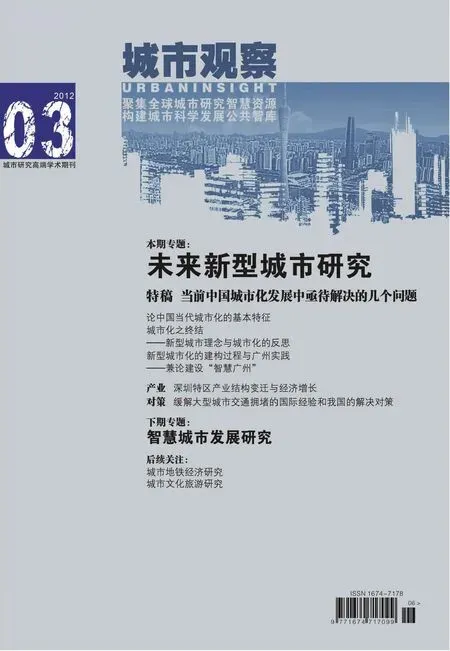基于3D視角的京津冀都市圈經濟空間分析
◎ 王潔玉 賀燦飛 黃志基
一、引言
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當前中國已經進入都市圈群體競爭的時代。都市圈是經濟發展的空間載體,是經濟活動和人口的主要集聚區,也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引擎。優化都市圈的經濟空間是國土規劃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但目前有關都市圈經濟空間的研究較少,并缺乏一個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本文引入世界銀行提出的“3D”分析框架,從一個嶄新的視角來研究都市圈的經濟空間格局,并以京津冀都市圈為例,探討“3D”框架在中國的適用性。
作為環渤海經濟區的核心,京津冀都市圈的發展對于推動整個經濟區以及中國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隨著《全國主體功能區劃》、《環首都經濟圈規劃》的實施,京津冀都市圈在國家經濟空間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近年來,京津冀都市圈的發展再次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本文基于“3D”視角,研究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空間格局,以期促進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二、理論框架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都市圈經濟發展不再依賴于比較優勢、廉價勞動力和資源,其經濟競爭力來源于專業化分工和產業集聚密度、與國家經濟中心和世界市場的距離及其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程度等。為了更準確地刻畫新時代的世界經濟地理格局,世界銀行2009年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1]在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框架下提出密度(Density)、距離(Distance)以及整合(Division)三個要素,從不同地理尺度刻畫世界經濟地理格局。該報告針對世界范圍的地理變遷提出“重塑世界經濟地理”,通過分析發達國家的早期經驗,為當代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政策提供有益的啟示。報告認為,高密度、短距離、低分割是經濟成功發展的基本條件,不斷增長的城市密度、人口的遷移和專業化生產成為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隨著一個國家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遠離經濟密集區導致生產率降低,于是人們為了從經濟密集區獲益,往往會向經濟密集區遷移,以縮短他們與經濟機會的距離,結果導致經濟密集區的經濟密度更高。同時,國家間為促進經濟更好地融合,實現經濟一體化,會縮減它們的經濟邊界、進入世界市場以獲取規模化和專業化收益。
促進都市圈內城市化水平,提高經濟集聚水平,縮小都市圈內經濟距離,減少都市圈經濟分割,促進城市專業化,實現經濟一體化,從而優化都市圈經濟空間,是國土規劃的重要目標。相對于非城市化區域,都市圈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高度聚集了各種生產要素,并在都市圈內部實現了合理的勞動地域分工,接近本國市場并與世界主要市場密切聯系,能夠吸引促進都市圈發展的資源,進而提升都市圈的規模經濟效益。所以世界銀行提出的“3D”框架抓住了經濟地理的核心要素,可以用來刻畫當代都市圈的經濟地理格局。
國內外有關“3D”框架整體的實證研究相對較少。Hector V.Conroy和Gabriel Demombynes(2008)[2]基于11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平均國民收入和消費數據,分析了地方特征(“3D”)和平均經濟福利(收入與消費)的關系,研究認為人口密度與貨幣福利有很強的正相關,長距離與低福利水平聯系在一起,少數民族比例較高的地區福利水平較低,進而證實了世界發展報告的觀點。Mark Robertsa和Chor-ching Goh(2011)[3]利用2000~2007年的數據,借用“3D”框架測試重慶市域范圍內勞動生產率的空間不均勻分布程度,發現距離與空間生產率分布有很強的相關性,特別是對于直轄市東南翼尤為顯著;而勞動生產率與分割尺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陳聞君(2009)[4]從“3D”視角對新疆城市化發展的困境與模式進行了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分別從“3D”組成要素,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提升了對各組成要素在經濟空間發展作用的認識。從經濟密度來看,其在國家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已成為一個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集聚程度的有效測度,也是協調區域發展和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5]。根據城市集聚經濟效應,城市經濟密度越高,生產率越高[6]。經濟密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經濟密度[7]、建設用地經濟密度[8,9]、人口經濟密度[10,11]或經濟密度的籠統性分析[12],選取的指標包括單位行政面積的就業人數[5]、城市單位建成區面積上的二三產業增加值[7]、單位面積城鄉建設用地上的二三產業增加值[8,9]、某地人口總數與經濟發展水平指標之比[10,11]等。從經濟距離來看,它是影響城市經濟活動空間分布與演化的關鍵因素。多數研究結合引力模型,利用經濟距離來劃分城市等級[13]或經濟圈范圍[14]。有關經濟整合的研究是近幾年的熱點,區域一體化發展、減少經濟分割,已經取得我國各界人士的認同。近年來,國家發改委已連續批準多項區域規劃,學術界也從不同方面進行了城市群整合問題的研究[15-17],主要集中于動力機制、整合模式等。
總體來看,“3D”框架為經濟空間研究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關于“3D”的已有研究缺乏系統性,主要是針對區域經濟空間某個方面的變化和發展,難以深入揭示區域經濟空間的差異。有鑒于此,本文試以“3D”框架為基礎重新刻畫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地理格局。
三、數據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京津冀都市圈是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石家莊、保定、秦皇島、廊坊、滄州、承德、張家口和唐山8座城市為腹地的區域①。本研究深入到京津冀都市圈的縣級層面,將市轄區統一作為整體單元統計,其中北京市市轄區包括東城、西城、崇文、宣武、海淀、朝陽、豐臺、石景山,天津市市轄區則包括核心六區,共計126個區縣單元。相關數據來源于《北京區域統計年鑒(2009)》、《天津統計年鑒(2009)》、《天津區縣年鑒(2009)》、《河北經濟年鑒(2009)》、《河北農村統計年鑒(2009)》等,重點參考了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
(二)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2008年京津冀都市圈126個區縣的經濟屬性數據,基于“3D”框架來研究其經濟空間格局。依據科學性、可比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均量指標與總量指標相結合的原則,剖析“3D”框架的經濟內涵,結合相關文獻選取的指標,提煉出適合京津冀都市圈經濟空間分析的評價指標體系(表1)。

表1 “3D”框架指標體系
經濟密度,即每單位土地上人口布局和經濟活動的強度,主要表現在人口、經濟產量、勞動就業的密集程度上。本文采用人口密度、單位土地面積GDP和單位土地面積從業人員數來衡量,分別由總人口、GDP和從業人口除以地區土地面積獲得,以評價都市圈經濟的集聚程度。
經濟距離,是指到達某一經濟密度區所耗費的成本,主要表現在與市場中心、交通中心的距離。本文采用到北京、天津的距離來衡量與市場中心的距離,到港口(天津港、秦皇島港、唐山港)的最小距離來衡量與交通中心的距離,以Google地圖中的最短駕車距離為依據。
經濟整合主要與社會政治地理相關,地方保護、制度壁壘、地理空間上的阻隔都會影響經濟整合的強度。本文選取外貿出口總額、實際使用外資額衡量都市圈外向開放程度,城市流強度衡量都市圈內部整合程度,其中城市流強度采用姜博等(2009)[18]提出的方法,基于三次產業的從業人員數來計算:

其中,Eij為i區縣j產業的外向功能量,Ni為i區縣的功能效率,Fi為i區縣的流強度,Q為從業人員數,GDPi為i區縣人均從業人員的地區生產總值。
研究過程中采用因子分析法來驗證“3D”框架指標體系的可行性,并利用主成分分析結果來刻畫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空間。“3D”框架綜合評價采用平均值進行分級,經濟密度、經濟整合、經濟距離得分大于平均值即認為符合對應項特征:若三項均符合,則經濟發展狀況最好,命名為“3D”地區;兩項符合,命名為“2D”地區;一項符合,命名為“1D”地區;三項均不符合,命名為“0D”地區。
四、研究結果
(一)“3D”框架指標體系的驗證及運用
基于SPSS17.0,對原始10個變量選取主成份分析法來提取公因子,根據特征值大于1和累積解釋方差(貢獻率)大于等于85%的原則,提取出3個公因子作為評價京津冀都市圈經濟空間的指標變量,累積貢獻率為92%,能反映原始變量的絕大部分信息。根據正交旋轉后的載荷矩陣(表2)進行因子命名解釋,發現三個公因子基本符合“3D”框架,由此也驗證了都市圈經濟空間分析的“3D”指標體系。

表2 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特征值及累積貢獻率
進一步采用因子分析結果來評價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空間。將初始因子載荷系數除以相應特征值的平方根,得到主成份系數,由此可以寫出前3個主成分的表達式:

用每一主成分中每個指標所對應系數乘上主成分所對應的貢獻率比重的總和,得到綜合得分模型。綜合得分模型中每個指標所對應的系數即每個指標的權重。

根據權重和正向標準化的數據,計算出126個區縣的經濟密度、經濟距離和經濟整合得分,以分析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空間格局。
(二)經濟密度評價結果
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密度整體較低,且各區縣得分不均衡,僅14%的區縣得分在平均值以上。經濟密度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天津市城六區、北京市城八區的得分遙遙領先,與周邊地區的經濟活動聯系松散,有所脫節,形成核心城市與腹地發展差距懸殊的局面。西部和北部經濟密度較低,東部和南部經濟密度較高,且高密度區主要沿北京—唐山、北京—保定—石家莊軸線分布,形成條帶狀高經濟密度廊道。由此可見,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活動以北京、天津為軸心向其兩側發展,城市間已形成松散的直線聯系,尚未形成網狀聯系。

圖1 京津冀都市圈經濟密度得分分布圖
(三)經濟距離評價結果
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距離得分較均衡,56%的區縣得分在平均值以上。經濟距離得分呈環狀遞減,北京、天津、廊坊的區縣得分最高,承德、張家口、石家莊的區縣得分最低。這也與近期研究得到的結果相同,京津冀都市圈區位水平等級以天津市、北京市為中心向外逐級遞減,且天津市區位水平略高于北京市[19]。

圖2 京津冀都市圈經濟距離得分分布圖
(四)經濟整合評價結果
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整合得分極不均衡,15%的區縣得分在平均值以上。北京市城八區的經濟整合得分遙遙領先,是第二位(天津市城六區)的7.9倍。在北京、天津、唐山、石家莊和廊坊,已有部分區縣獲得較高的經濟整合得分;在秦皇島、保定,僅有市轄區獲得較高的經濟整合得分;在張家口、承德、滄州,經濟整合得分均較低。
(五)綜合評價結果
通過平均值篩選后發現,京津冀都市圈126個區縣中“3D”地區14個,“2D”地區6個,“1D”地區54個,“0D”地區52個,大部分區縣為“1D”和“0D”地區,不能完全滿足經濟密度、經濟距離、經濟整合三個條件,經濟發展基礎薄弱且不均衡。京津冀都市圈的“2D”地區中,石家莊市轄區為密度、整合略好,滄州市轄區為密度、距離略好,其余4個隸屬于天津、唐山的區縣為距離、整合略好;“1D”地區中,張家口市轄區、承德市轄區為密度略好,其余52個區縣均為距離略好。

圖3 京津冀都市圈經濟整合得分分布圖
北京、天津、唐山的市轄區經濟發展狀況較好,但經濟活動擴散范圍相對較小,輻射能力全部布局在行政區劃范圍之內,對河北其他城市影響很小。在京津唐周邊出現一條“貧困帶”,這些區縣雖然經濟距離得分較高,區位因素良好,但經濟發展與京津唐存在巨大差距。2005年,亞洲開發銀行調研時也發現了這一現象,并提出了“環京津貧困帶”的概念②。大量經濟要素由腹地城市向核心城市聚集,而核心城市的經驗、經濟力量并未向腹地輻射,這種單向聚集造成核心城市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腹地則呈現相對衰退的趨勢,出現“貧困帶”現象。“貧困帶”外圍為“0D”地區,與經濟中心的距離較遠、聯系較少從而造成經濟發展狀況較差。

圖4 京津冀都市圈3D分布圖
五、京津冀都市圈的區域經濟空間差異
(一)經濟密度呈現“一體兩翼”格局
京津冀都市圈經濟密度的差異呈現出區域經濟發展多中心的空間結構,形成了以北京、天津、唐山、保定、石家莊為中心的“一體兩翼”高經濟密度格局,其中西翼較長、經濟密度較低;東翼較短、經濟密度較高。
京津冀都市圈內,北京、天津、唐山、保定、石家莊對周邊地區的輻射作用較明顯,已呈現出擴散的發展趨勢。同時,張家口、承德等城市還處于向心集聚的態勢,市區與周邊區縣的聯系較少,呈現出單一增長極的發展階段。北京、天津、廊坊、唐山、石家莊、保定已基本連接成片,形成明顯的點軸發展格局。從整體上看,京津冀都市圈正由單向集聚逐漸向雙向擴散過渡發展。在擴散效應的影響下,核心單元逐漸向外擴散,使周邊地區也發展起來,從而核心單元的經濟密度有所弱化,周邊地區的經濟密度有所增加,進而影響更大的區域。
(二)經濟距離呈現“環狀遞減”格局
考慮到北京、天津兩大市場中心以及沿海港口的巨大優勢,京津冀都市圈經濟距離的差異呈現出面向海岸帶,以天津市、北京市為中心向外環狀逐級遞減的格局。同時也從側面證明與交通可達性相比,市場中心可達性更重要。
(三)經濟整合呈現“高度集聚”格局
京津冀都市圈經濟整合整體水平較低,僅京津唐石獲得較高的經濟整合得分,差距懸殊。這主要來源于京津冀都市圈的行政壁壘、城鄉二元化以及經濟距離造成的市場區和非市場區的分割。京津冀三地分屬不同的行政等級,制度規制造成資源配置、要素流動不經濟,政府協商不對等。同時,區縣產業之間缺乏協作性和互補性,缺少與上級政府所在區縣的聯系,造成整個城市體系發展不連貫。中心城區和周邊區縣的經濟差距較大,也造成周邊區縣在對外開放度、社會投資、城市流強度等方面都處于劣勢。
(四)京津冀都市圈呈現“階梯式發展”格局
綜上分析,京津冀都市圈“雙核”格局明顯,并有“三足鼎立”的趨勢。從市域來看,京津冀都市圈的“3D”類型分布極不均衡,區域經濟差異明顯。北京、天津、唐山、廊坊屬于第一階梯。秦皇島、保定、滄州為第二階梯。石家莊、承德、張家口為第三階梯。

表3 京津冀都市圈市域3D類型
(1)第一階梯:與經濟中心和港口的距離最近,經濟活動的集聚密度最高,經濟整合狀況最好,是京津冀都市圈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
北京作為京津冀都市圈的首位城市,經濟水平整體最高。各區縣的經濟距離得分由東南向西北遞減,分布較均衡;經濟整合得分極不均衡,城八區遙遙領先,是第二位(順義區)的24倍,大興區、通州區、昌平區緊隨其后;經濟活動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八區,逐步擴散到周邊的順義區、通州區、大興區、昌平區,并影響到更遠的平谷區、房山區。門頭溝區毗鄰北京市城八區,但經濟密度較低,與其較低的經濟整合有關。北京市以中心城八區為首,開始延伸到東南方向的通州區、大興區、順義區,呈現出“中心集聚、東南擴散”的經濟格局。
天津是北方重要的門戶城市,毗鄰港口,各區縣的經濟距離得分均較高;經濟活動主要集聚于天津市城六區及其周邊的津南區、北辰區、東麗區、西青區,并逐漸擴散到其他各個區縣;經濟整合狀況為南部區縣顯著優于北部區縣。天津市以中心城六區為核心向四面八方擴散,傾向于濱海地區,呈現出“中心擴散、組團近海”的經濟格局。天津市近年來正在建設的“濱海新區”,擁有良好的區位因素,目前來看塘沽區的發展最好,其次為大港區,漢沽區稍弱,三區的資源整合仍需要進一步探討。
唐山是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深加工業基地,工業地位不容忽視。處于環京津、環渤海港口的核心,經濟距離得分較高。唐山市轄區的經濟密度最高,并輻射和帶動周邊區縣的發展。經濟整合得分較均衡,但普遍偏低。唐山的經濟格局以市轄區為中心,擴散到北部的遵化市、遷西縣。唐山市轄區東南部為采煤波及區和地震斷裂帶,西部有新京山鐵路的阻隔,相對來說更傾向于往北部擴散發展。
廊坊地處京津兩大城市之間,經濟距離得分較高。其轄區內的經濟活動受京津經濟輻射的影響很大,集聚在廊坊市轄區、霸州市及北部“飛地”,主要為轉化京津產業、輔助服務京津。廊坊市經濟整合較差,僅市轄區、北部的三河市略好。整體來看,廊坊市僅市轄區發展較為良好,其余區縣雖然距離京津很近,但經濟密度、經濟整合得分還很靠后,出現了“大樹底下不長草”的典型現象。
(2)第二階梯:承接第一階梯,帶動第三階梯的發展。與經濟中心和港口的距離較近,但經濟密度、經濟整合狀況一般,是京津冀都市圈經濟發展的過渡區域。
秦皇島是北方旅游中心和著名港口城市。處于海陸交通運輸的樞紐位置,地理區位良好,市轄區的經濟密度和經濟整合得分遙遙領先于周邊區縣。保定是北京南行的第一個大城市,曾為河北省的省會所在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但目前該市的政治和經濟功能被弱化,經濟整合較差。滄州擁有黃驊大港,文化旅游資源較豐富,也是西煤東運的主要途經地,主要產業為傳統化工,未來有望利用沿海港口優勢帶動內地經濟發展。
(3)第三階梯:與經濟中心和港口的距離較遠,經濟狀況為市轄區“一枝獨秀”,是京津冀都市圈經濟發展的外圍區域。
石家莊作為河北省的省會,是華北重要的商埠和交通樞紐,但距離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中心較遠,造成經濟發展缺乏規模效益。張家口和承德作為冀西北部生態環保型城市,旅游資源豐富,但經濟密度和外向度均較低,這也與其地形格局一致。
六、結論
隨著產業升級,區域經濟發展不再依賴比較優勢,而源于經濟分工與集聚的競爭優勢,經濟密度(Density)、經濟距離(Distance)以及經濟整合(Division)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框架來刻畫區域經濟空間。本文將此框架移植到一個都市圈內部研究區縣尺度的經濟地理格局,并以京津冀都市圈為例加以應用,對“3D”框架進行指標量化,采用因子分析法檢驗,并進一步評價京津冀都市圈的經濟密度、經濟距離、經濟整合及區域經濟差異,以實現“3D”框架的中國化運用。“3D”框架的可行性也可為今后城市群經濟空間評價提供借鑒和參考。日后可對指標體系進一步細化,增加動態對比,以豐富“3D”框架的運用。
2009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也提出了針對不同問題地區的措施建議。制度必須具有普適性并首先使用;基礎設施相關投資應當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使用,排在第二位;空間針對性干預措施盡量少用,放在最后一位。因此京津冀都市圈應以3D地區為范例,對2D地區推行適合的公共制度,對1D地區同時推行公共制度和基礎設施建設,對0D地區推行公共制度、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針對性的激勵措施。基于“3D”視角,京津冀都市圈只有遵循經濟地理變遷的三大特征,尋求適應于“3D”特征的城市發展政策,才能獲得進一步發展。推進城市化會增加經濟密度,生產要素向高密度區流動會縮短經濟距離,地區間減少分割能夠發揮規模經濟和專業化作用,這樣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
注釋: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研究報告.2005.
②亞洲開發銀行.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2005.
[1]世界銀行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7.
[2]Hector V.Conroy, Gabriel Demombynes.Density, Distance, and Divis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alysis with a Unified Local-Level Economic Welfare Map[J].http://nip-lac.org/uploads/Gabriel_Demombynes.pdf,2008:1-24.
[3]Mark Roberts, Chor-chingGoh.Density, distance and division: the case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China[J].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2011:1-16.
[4]陳聞君.3D概念對新疆城市化發展模式的政策啟示[J].開發研究,2009,(3):134-137.
[5]“中國經濟密度分布與政策研究”.課題組中國經濟密度格局已成型[J].調研世界,2011,1:12-15.
[6]陳良文,楊開忠.生產率、城市規模與經濟密度:對城市集聚經濟效應的實證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 2007,(02).
[7]馮科,吳次方,陸張維,貝涵璐.中國土地經濟密度分布的時空特征及規律——來自省際面板數據的分析[J].經濟地理,2008,(05).
[8]林堅,祖基翔等.中國區縣單元城鄉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空間分異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08,(03).
[9]曹廣忠,白曉.中國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區位差異及影響因素——基于27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20,(2).
[10]盧忠.中國人口經濟密度區域差異及分析[J].人口與經濟,1992,2:44-48.
[11]王曉明.廣東省人口經濟密度分市差異分析[J].南方人口,1993,2:20-24.
[12]何邕健,胡麗.基于經濟密度差異特征的區域空間結構研究——以江西省為例[J].規劃師, 2008,24(10):68-72.
[13]羅芳,馮立樂.基于潛力模型的南京都市圈城市等級劃分[J].華東經濟管理,2010,24(06):8-11.
[14]尚正永,白永平.贛州市1小時城市經濟圈劃分研究[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7,26(01):16-24.
[15]陳存友,湯建中.大都市區城市經濟整合發展研究——以長江三角洲為例[J].中國軟科學, 2003(6):120-124.
[16]王士君,高群,王丹.城市相互作用關系的一種新模式——近域城市整合研究[J].地理科學, 2001,21(6):558-563.
[17]王樹功,周永章.大城市群(圈)資源環境一體化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4,12(3):52-57.
[18]姜博,修春亮,趙映慧.“十五”時期環渤海城市群經濟聯系分析[J].地理科學,2009,29(3):347-352.
[19]陳潔,陸鋒.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區位與交通可達性評價[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8,24(2):53-56.
[20]周一星.城市地理學[M].商務印書館,19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