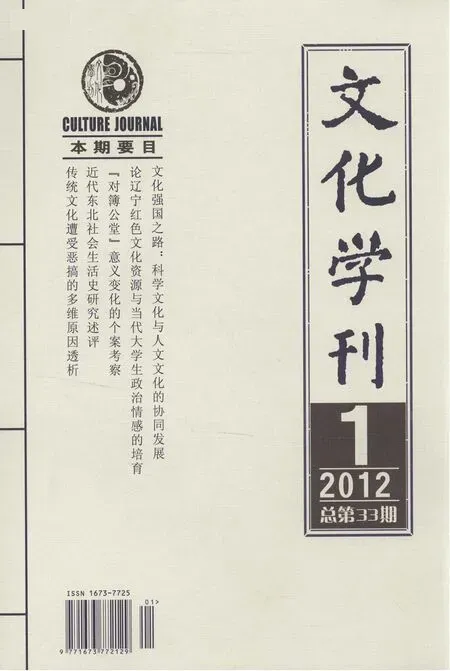“對簿公堂”意義變化的個案考察
冉啟斌 段文君
(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天津 300071)
漢語的歷史非常悠久,現代漢語的各個層面都是從古代傳承下來的。在漢語傳承過程中,詞義演變是經常的事。通常認為客觀事實的發展變化,詞義的相互影響,詞義的引申等等都可能導致詞義變化。然而漢語中有些詞的詞義變化并不與上述因素相關,而是由語言使用者的誤解誤用產生的。目前這方面研究很少,本文以“對簿公堂”的個案考察為例來了解詞語誤解誤用產生變化義的一些具體情況。
一、“對簿公堂”的本義
“對簿公堂”的本義很清楚,就是指在法庭上接受審問。
“簿”本指記事的文書、登記冊等,漢代以后也常常表示責問質詢某一事項的文書。《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吏簿責條侯(條侯即周勃的次子周亞夫)。”裴骃“集解”引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意思是說通過列有罪狀的文書來責問罪情。《史記·酷吏列傳》:“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集解”引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這些地方的“簿”都指列舉罪狀的文書。《漢語大詞典》將“簿”的這一義項釋為“指記錄審問材料或罪人供詞的文狀”,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實際的。
“對簿”較早的兩個用例見于《史記》。《史記·李將軍列傳》:“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史記·酷吏列傳》:“臨江王 (景帝的太子劉榮)征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此事又見《漢書·酷吏列傳》,顏師古注曰:“簿,謂文狀也。”即獄辭文書,“對簿”也就是答辯指控的事實,即接受審問。《現代漢語詞典》將“對簿”釋為“受審問”。 《漢語大詞典》釋義為:“受審。簿,獄辭的文書,猶今之起訴狀。受審時據狀核對事實,故稱對簿。”
“公堂”,古時可指君主的廳堂①如《詩經·豳風·七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朱熹集傳:“公堂,君之堂也。”,也常指官府的辦公場所。唐杜佑《通典》卷二十四“職官六·侍御史”:“上曰:‘吾聞斯人常以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以為準繩司乎?’”北宋王溥《唐會要》卷五十五“省號下·中書舍人”:“獨儒衡一日會食公堂,有青蠅入瓜上。”這兩處的“公堂”都指有關公務的處所。“公堂”后來也專指經常處理官司訴訟、案件審理的官府大堂。如 《醒世恒言·盧太學詩酒傲王侯》:“明日到公堂上去講,該得何罪?”《包公案》第一卷:“真贓未獲,巧言爭辯于公堂。”
“對簿”與“公堂”合起來的意義即指“在法庭接受審問”之義。“對簿公堂”作為一個整詞使用出現的時間較晚,在北京大學CCL語料庫中確切作為一個整詞使用是在1949年以后的現代漢語語料中。
二、“對簿公堂”的意義變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簿公堂”的意義發生了變化。在北京大學CCL語料庫中進行檢索,在現代漢語語料庫中有173個用例;經過逐一分析后發現,僅有三例使用了本義。這三例分別是:
(1)如果庭外和解不成,那就把羅大佑、“滾石”、南京音像出版社一起作為被告對簿公堂。(1994年報刊精選第五版)
(2)為了捍衛清白,原告正拭目以待準備“接招”,被告將對簿公堂。(1994年報刊精選第七版)
(3)《尤利西斯》1922 年首次出版之后,因被指控“色情淫穢、有傷風化”而兩次對簿公堂,直到1933年才得以公開與英美讀者見面。(《作家文摘》1994年)
其余170例中除去復現和需依語境定義的語料外,全部用例的意義都與其本義不同,現舉幾例:
(4)吳云凌牽了頭,接下去便滾雪球似的,呼啦啦站出來三百一十八戶農民,要同南極鄉政府對簿公堂。(《中國農民調查》)
(5)(國際)紐約世貿大樓開發商與保險公司就賠償額對簿公堂。(新華社2004年新聞稿)
(6)名翻譯家傅雷次子傅敏和安徽文藝出版社近日因傅雷譯作的出版糾紛對簿公堂。(《作家文摘》1996年)
(7)形形色色的暴利行為,廣大消費者要敢于向有關方面投訴,或依法對簿公堂。(《人民日報》1994年第4季度)
(8)賈老師說:“通過被捕的家屬,請律師對簿公堂。”(梁斌《紅旗譜》)
以上例句,是很難按照“對簿公堂”的本義來解釋的。“對簿公堂”的本義是“在法庭接受審問”,因此“對簿公堂”所指的對象是處于從屬地位的一個人或一群人,他們要在法庭上接受官吏法司的審訊,是被動的一方。總結例句(4)-(6),其基本格式是“A 和/同/與 B 對簿公堂”;例句(7)、(8)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卻也暗存著“相抗衡的兩方或雙方對簿公堂”的含義。(4)-(8)五個例句中“對簿公堂”一詞的指向都是兩個對象,而且這兩個對象間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利益糾葛,是處于同等地位卻又相對立的兩個方面。與此同時,用“受審問”這個本義去解釋例句中的“對簿公堂”是行不通的。
這種情況顯示出“對簿公堂”的意義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簿”不再是“核對案卷文狀”的意思,而將它理解為“打官司”的意思更加合理。
三、“對簿公堂”意義變化的原因
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詞義的變化是經常的。客觀事物的發展,語言要素的相互影響,詞義的引申,人類認識的發展等都會引起一個詞的詞義變化。引起“對簿公堂”意義的變化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一)語言使用者的錯誤理解
語言使用者錯誤理解的原因首先是 “望文生義”。
詞的意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們往往站在現在的立場上去理解詞的意思,而不是按照它本來的意思去理解,這是經常發生的現象。[1]
例如據我們調查,在“百度知道”上有人問“對簿公堂”的意義,有網友是這樣回答的:“‘對簿’指的是兩個人,一個人的話跟誰去對呢?”①見網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3797708.html?an=0&si=4&wtp=wk而更有甚者完全顛倒了 “對簿公堂”的本義和變化義的關系;寫道:“嚴格地說,對簿公堂是指雙方在公堂即法庭上對質,而不是單方受審。不過,如果按法律程序辦的話,審問的過程本身也會有很多對質,所以不太嚴格時也可用‘對簿公堂’表示被提審或接受審問。”②網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5602672.html?an=0&si=1在這里,語言使用者的理解角度均著眼于“對”字最主要的義項——“彼此相向、對面的、敵對的”,而非其“核對、比照”之義;這不失為是動詞“重新理解”③儲澤祥、王寅(2009)探討了動詞的“重新理解”,是把語言單位歷史上的X意義理解成當代的Y意義。從本質上看,“重新理解”是由于普通人(不包括專業人員)對某個語言形式歷史意義、用法的不了解或遺忘而造成的一種“普遍誤解”,是同一個語言形式在不同歷史時期使用結果不同的一個反映。的表現。
如此普遍的誤解誤用,除了“對”字主要義項的凸顯外,“公堂”對整個詞語的修飾限定作用對語言使用者的正確理解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擾。在單獨使用“對簿”一詞時,語言使用者會全面考慮到“對簿”的述賓結構關系,詞義理解不易發生偏差。而在“對簿”與“公堂”的組合使用時,“對簿”的詞義理解受到“公堂”的干擾與限制,有意無意地弱化了“簿”字的本義。冉啟斌探討“格殺勿論”的誤用義時,也指出望文生義的誤解現象在語言使用中是經常出現的,并列舉多例,如差強人意、望洋興嘆、長袖善舞等。[2]“對簿公堂”也屬于這一類現象。
語言使用者對“對簿公堂”的錯誤理解還受到格式相近詞語的負面影響。
與案件審理相關的詞語在普通話及方言中還有不少,其中三對六面、三曹對案、三頭對案等對“對簿公堂”錯誤義的產生有重要作用。“三對六面”是指 “謂會同當事雙方及中間人或見證人”(《漢語大詞典》)。 茅盾《子夜》:“回頭我自會請三先生來,大家三對六面講個明白。”“三曹對案”、“三頭對案”與“三對六面”意思相近,主要指“審問案件時的當場對質”。關涉同一領域的詞語之間常常會產生相互影響,加之這幾個詞語中的動詞成分都為“對”字,因此語言使用者很容易將這幾個詞語的詞義相互串聯,以彼“對”來解釋此“對”。這種格式相近的詞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語言使用者對“對簿公堂”的錯誤理解,產生了負面影響。
(二)傳媒、辭書的推進作用
在當代社會中“對簿公堂”的使用頻率很高,其誤用意義的推廣也有一定特殊性。在分析北大語料庫“對簿公堂”一詞的現代用例(共173個)時可以看到,126例出自報刊新聞稿,47例出自各文學期刊;其中不乏權威刊物。除去三個用例采用了本義,剩下的170個用例(含重復出現的用例)通通采用的是其“打官司”的變化義。搜索日常所接觸到的社會新聞,“對簿公堂”的誤解誤用更是比比皆是。如《人民日報》2011年8月12日第15版“德國公司為天然氣價格與俄氣對簿公堂”;2011年7月19日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 《竊聽丑聞:英國各界名人聯合“反攻”默多克集團》“還有人打算與默多克旗下的報業集團對簿公堂”。這些權威媒體的誤用更是大大推進了“對簿公堂”誤用意義的擴散和推廣。
對于這種現象,一些詞典已經將 “對簿公堂”的變化義收錄進來。從我們了解到的情況來看,比較早的辭書是常州市教育局編 《成語詞典》(1981)、劉松筠等 《中華成語大辭典》(1986)。其后馮世森等《簡明成語詞典》(2002)、李科第等《成語辭海》(2003)、李行健等《現代漢語規范詞典》(2004)、黃金貴等《新課標中學生實用成語詞典》(2004)、張林川等《學生成語學習詞典》(2005),都收錄了“對簿公堂”的變化義。例如《現代漢語規范詞典》的釋義是:“在公堂上根據訴狀核對事實。舊指在官府受審;今指原告和被告在法庭上對質打官司。”變化義進入多部辭書,無疑是“對簿公堂”變化義興盛擴大的又一個重要促進因素。
四、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了“對簿公堂”一詞的本義以及在當代漢語中的變化義,并對其意義變化的原因作了適當的分析。由于望文生義以及近似格式詞語的影響而使“對簿公堂”意義出現了誤解誤用,而傳媒、辭書對錯誤義的傳播推動,更加劇了其變化義的形成。
在當代漢語中“對簿公堂”一詞的變化義使用范圍很廣、頻度極高,變化義已經大大超過了其本義。根據我們了解,對于與古漢語有關的傳承詞,這種現象在當代漢語使用中并不少見。對這些廣泛出現的現象,采取怎樣的規范策略更加合適有效,應該引起我們更多的關注和探討。
[1]儲澤祥,王寅.動詞的“重新理解”及其造成的影響[J].古漢語研究,2009,(3).
[2]冉啟斌.“格殺勿論”誤用義的調查分析[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