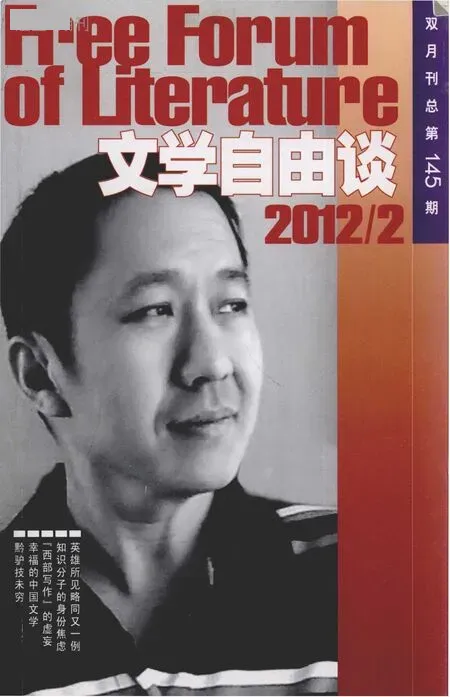“西部寫作”的虛妄
●文 嚴英秀
2011年底辭舊迎新之際,“甘肅文學(xué)論壇小說八駿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我有幸聽到了許多前輩老師的教誨,很是啟發(fā)心智。但也有一些言論,讓我萌生了有關(guān)思考。譬如有評論家說,對現(xiàn)在的甘肅小說真不知說什么好,因為這些作品全然不是多年前所熟悉的西部文學(xué)的狀貌,無法引發(fā)那種親切感新鮮感夾雜的閱讀期待。可以看出,這位評論家的話很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態(tài),因為不少人不約而同都談到了甘肅小說與“西部文學(xué)”的關(guān)系。而復(fù)旦大學(xué)的陳思和教授評論我的小說時,更是在文章里肯定地表示:“說實話,這些作品并非是我期待看到的西部文學(xué)的風(fēng)格”。
那么,大家期待看到的西部文學(xué)的風(fēng)格究竟應(yīng)該是什么樣的呢?甘肅的小說應(yīng)該保持怎樣的“西部”,才能贏來外界熱切而長久的關(guān)注呢?
雖然我非常清醒我的寫小說只是出于內(nèi)心的一種熱愛,一種情結(jié),我從來都不是有問題意識、堅持什么“主義”的作家,他人對我作品的褒貶也不太會左右我的情緒,但盡管如此,當上述評論家的意思變成問題擺到面前時,我得承認,作為一個“西部作家”,我的思緒有點悵惘,有點糾結(jié)和失落。因為我知道,那些意思雖表達得各個不同,或直接地表示質(zhì)疑,或含蓄地貶以褒出,但換句話說,都說的是:當甘肅的小說不再是色彩濃烈、原汁原味的“西部”,而是和“東部”、和中原、和中國廣大的別處的文學(xué)一個模樣,那么,你如何證明自己的存在是必要的?外界又如何界定、如何命名你的創(chuàng)作?你不寫大漠孤煙中踽踽獨行的神授藝人,不寫黃土溝壑下淚眼凝望著遠方的山妹子,不寫草原帳篷里的恩怨情仇,不寫西域駝峰上的紅塵往事,卻偏要跟到人家屁股后邊寫城市,寫現(xiàn)代人,你既然死活不明白全中國人民都會說、電視選秀節(jié)目上天天喊得山響的那句話“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別人為什么要對你偏遠小城市生活的作家的城市題材的作品感興趣呢?要看城市生活,人家不會去看“香港的情和愛”,不會去看“跑步走過中關(guān)村”,不會去看上海的“大城小愛”,不會去看“混在深圳”嗎?真是的!
在場的《文學(xué)報》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信息,研討會結(jié)束后,記者馬上發(fā)來了很具針對性的采訪題目:“在研討會上,也有評論家提到,西部寫作的地域特色可能在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城市氣質(zhì)。在八駿中,您是身份比較特殊的一位,比如西部作家的身份之外,您還是一位藏族作家。您是否會在寫作中試圖突出這一地域和民族的身份?您如何理解地域和民族在寫作中的意義。作為一位寫作者和評論家,您覺得當下年輕的西部作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他們可以向哪個方向進行突破?”
我歷來不是會做問答題的人,思索良久才淺嘗輒止、言不盡意地做了如下回答:“我生活在西部,我是一個藏族人,但作為作家,我迄今為止不曾在寫作中刻意突出過地域和民族的身份,從顯性的體例看,讀者或許不會從我的作品里識別出我是哪里人,我是哪個民族的人,更多的時候,我只是一個書寫當代城市生活、表現(xiàn)知識女性的情感命運的普通作家,和任何其他地方的作家并無二致。但這并不意味著,我低估或抹煞地域和民族在寫作中的意義,眾所周知,地域性寫作在中國出過很多名家,而且,還正在源源不斷地出著。必須承認,地域資源,肯定是寫作的一大寶藏。同時,就算不以地域生活為顯性的主題元素,任何作家的創(chuàng)作里,也都會毋庸置疑地留下自己植根故土的明顯胎記。而民族,更有著非凡的意義,她不光是一種記憶,一種滋養(yǎng),更是一種血統(tǒng),一種底色,一種支撐,一種信仰。我相信我的創(chuàng)作正在踐行著母族文化和故鄉(xiāng)熱土給我的饋贈。
從文學(xué)史的眼光看,從中國文學(xué)的全局觀照,‘西部作家’這樣一種提法曾經(jīng)是有意義、也有意味的,但時光走到今天,我認為已經(jīng)不存在這樣一個整齊劃一的‘西部作家’的群體。生活在西部的作家同樣面臨的是普遍的中國性境遇,沒有誰因為‘西部’而可以置身事外,逍遙在千年的牧歌想象中,沒有誰不被裹挾進強大而盲目的現(xiàn)代化洪流中,從根本上說,并不存在一個一成不變的‘西部’,‘西部’本身已面目模糊。因此,西部作家寫作時遇到的問題和別處的作家一樣,是千頭萬緒,難以一言以蔽之。每個作家在每個階段遇到的問題也會不一樣。若非要做群體性的區(qū)別的話,可以說,西部作家更強烈地感受著山川河流痛失往日面貌的滋味,我們的問題、我們需要突破的地方也許都在這里,即如何用手中之筆有力地表達我們失鄉(xiāng)、尋鄉(xiāng)的精神歷程。”
后來,我從報紙上看到八駿中最年輕的弋舟對“西部寫作地域特色”問題的回答,觀點基本一致,但他顯然更高屋建瓴:“這只是特定階段內(nèi)的產(chǎn)物,這個‘西部’和‘特色’,只是特定時段里的特定語境。如果我們承認時光在流傳,世界在改變,那么,我們就應(yīng)該承認‘西部特色’也將是一個日新月異的所指。據(jù)說我國城市人口已經(jīng)首次超過了農(nóng)村人口,這便是今日我們面對的格局,文學(xué)描述的圖景隨之轉(zhuǎn)變,也是可以理解的了。當然,文學(xué)絕不會是日新月異的事情,那些亙古與恒常的準則,永遠會作用在我們的審美中。在這個意義上,我?guī)缀鯖]有將自己的寫作落實在某個‘地域’的窠臼中。我個人覺得,生活在中國的西北,生活在中國的內(nèi)陸,對于一個中國人而言,有利于其對于這個國度更本質(zhì)地認識。作用在自己的寫作中,這樣的認識,意義就堪稱重大了——更本質(zhì)地把握我們的國家,更本質(zhì)地把握中國人的境遇,由此,便可以放眼整個人類的世態(tài)炎涼與愛恨情仇了。”
看來,在西部寫作,是怎么也繞不過“西部”的,你如果“西部”了,那且好,名正而言順;如果你不愿意或者還未來得及“西部”,至少你得面對以上的提問,做出自圓其說但終歸顯得有點心虛的回答,好像自己多么對不起西部似的——我是深諳個中滋味的,因為如記者所說,我除了“西部作家的身份之外,還是一個藏族作家”。我在極其短暫的寫作生涯中,不計其數(shù)地深度體驗過這種對來自外界的期待、界定、命名的愧欠感。我曾一遍又一遍地捫心自問:為什么,我的筆離西部題材這么近,我離藏族題材這么近,但這么多年,只是很近,卻從未進入?一條魚,想要對它所寄身的河流完成一種審視,一種表述,真的是那么難以企及嗎?
我相信這是個極其恰切的比喻。是的,是魚和河流。迄今為止,不是別的。不會是鳥和林子,鳥的食有時在別處,鳥常常飛得很遠,并且常常從高處俯瞰它棲身的樹林。也許只有作為魚,才會如此地明白鳥看似隨心所欲的姿態(tài)其實是多么珍貴。
講一次小小的“西部”經(jīng)歷吧。幾年前的一個暑假,我們一行人集體組織去九寨溝游玩。剛上旅游車,導(dǎo)游就自我介紹說她是中專畢業(yè)的藏族女孩“卓瑪”,說“藏族人只要會說話就會唱歌,只要會走路就會跳舞”,然后音色平平地演唱了“康巴漢子”,然后口若懸河、錯誤百出地講解美麗的九寨風(fēng)光,講解生活在九寨的藏族人神秘的天葬,浪漫的婚俗,講解我們此行需要入鄉(xiāng)隨俗的種種事項,說得全車人個個眼眸熠熠生彩,充滿神往——確乎,相比我們生活的工業(yè)城市蘭州,遠方又是多么荒蠻多么風(fēng)情的“西部”啊!
接下來,經(jīng)過有效探察,我已然斷定所謂“卓瑪”并非我同族,而只是一個導(dǎo)游業(yè)務(wù)還不甚過關(guān)的漢族打工妹。這沒什么奇怪,不過是旅游公司的營銷策略中一個小小的手段罷了,兩下并無礙。車越來越近地駛?cè)肓瞬貐^(qū)腹地,卓瑪高聲談笑的聲音像車窗外連綿的綠草地上一掠而過的油菜花一樣明艷,使得我的長期在嚴重污染的天空下案牘勞形匆匆奔波的同伴們越來越袒露出了“原生態(tài)”的興奮,若卓瑪不是卓瑪,而是阿芳或珍珍,快樂總是要打點折扣的吧?——然而,我們卻遭遇了一個真正的“卓瑪”。
在甘川交界的一片有稀落幾家人煙的曠野上,我們的旅游車突然卡殼在馬路正中,司機車上車下地鼓搗了好久后,卓瑪宣布故障可能還不會很快解除,她抱歉地說大家可以下車活動活動,拍個照什么的解解悶,四處風(fēng)光甚好,“不過,你們記著不要隨便和這兒的居民打交道”,她說,“藏民很壞的!”一言既出,車廂內(nèi)突然一片異樣的肅靜。這句話既不符合說話者自己的“卓瑪”身份,又嚴重消解了之前她一路道來的關(guān)于藏民族淳樸善良、熱情好客的講解。愕然中,有些人不安地扭頭打量我——我是此行中惟一的藏族人。卓瑪意識到自己脫口而出的失誤,她愣怔了一下,又很含糊地補充了一句:“我是說這里的藏民壞。”
雖然對“這里的藏民壞”有了一定的思想準備,但事情還是顯得更糟。急著要方便的一群人匆匆奔到前方刷著大紅色“廁所”字樣的土墻下時,一個穿著簡易藏裝的婦女擋到了面前,“廁所,收費!三塊錢!”她用生硬的漢語喊。什么?三塊?見我們不解,她很不耐煩地重復(fù)說:“三塊,一個人三塊,男的女的都三塊!”這太過分了,怎么能這么乘人之危!人群同仇敵愾地上去講理,城里的洗手間最高也就五角錢,這兒沒有水不供應(yīng)草紙,不過一面土墻遮個羞而已,竟收三塊,也忒黑了吧!也有好脾氣的人以戲鬧的口氣說,原價三塊,但這么多人一起上,就打個折一人一塊吧?藏族婦女冷冷地瞅著我們,絲毫未被人多勢眾所威懾,她堅持說:“廁所,三塊!”絕無薄利多銷的意思。最后,有些人嘟嚕著“不跟這些刁民一般見識”拿出了三塊錢,有些人罵著“少數(shù)民族窮了就要搶人”憤然離去,還有一些男人離開人群繞到遠些的空地上以圖就地解決,婦女望著他們的背影一聲口哨,呼地四處冒出來十幾個半大的小孩,抓起地上的土圪拉向那些“撒野”的過客沖去。
我在一切復(fù)歸安靜后無可遏制地走到了那個婦女面前,我用藏語告訴她,不能這樣,這樣太野蠻太無恥。我說我也是藏人,藏人不該是這樣的,從來都不是這樣的,但今天你們的行為太給我們民族丟臉!我還說,你怎么能唆使孩子們做土匪路霸,他們這個樣子長大了如何做人?那個婦女聽見我說藏語,先是露出了驚喜的表情,像是陰冷的冬日天空亮出了一抹陽光,然后她咯咯地笑彎了腰,說“你的口音,哈哈!你的口音!你是青海的,拉薩的,甘南的?你到底是哪里人嘛?”嘲笑完我的方言,她開始安靜地聽著我的聲討,她的臉上慢慢浮現(xiàn)出悲憤的神情,鄙夷的神情,她說,你想讓藏人是什么樣子?你知道現(xiàn)在藏人的生活是什么樣子?我們的牛肉羊肉被人家拿走了,牛皮羊皮被人家拿走了,人家給我們最低的錢,一轉(zhuǎn)身卻拿我們的東西發(fā)家致富,全世界去坑人!那些人今天這個來劃圈征地建廠子,明天那個來開礦挖山砍木頭,十年里,我被逼著拆遷了三次家!他們淘了金子挖了寶貝拍屁股走了,我們的草場干了,青稞爛了,河水臟污成牛喝了都要死!現(xiàn)在,我們的牛羊沒處去,我們的人都被包工頭包下挖冬蟲夏草去了。你看看,草原這幾年變成什么樣子了!日子過成這樣子了,守個廁所要他們?nèi)龎K錢,我犯什么法了?
一時間,我被她的話擊中。她眼中突然迸濺的淚水使我啞口無言。我呆立半晌,慢慢轉(zhuǎn)身,她在背后不依不饒地喊:“丫頭,你嫌我給你丟人了,我還嫌你丟人呢!你吃上了公家飯當上了城里人,就以為自己是文明人了,就不知道自己是瞎子了!你說這些孩子長大怎么做人,再怎么做人也不會比你們那些城里人更壞吧?他們殺羚羊販藏獒,他們把我們的朋友馬和狗剁成肉燉成湯,他們見什么吃什么,聽說,他們現(xiàn)在要吃人肉大補呢!你就好好跟著他們學(xué)吧!”
我在她凜冽的罵聲中慢慢走回到我的同伴中,走回到同樣凜冽的目光的包圍中。車修好了,大家歡呼雀躍,說“趕緊離開這鬼地方”,就在那一刻,我遽然喪失了一種似是而非的相伴,疼痛橫空而出,那么尖銳,那么多,它一下子把我和人群隔離開來,我是那么地孑然一身啊。車窗外,那一片被無數(shù)的歌謠贊美吟唱過的藍天白云,依然如美輪美奐的畫卷,靜默地綻放著天荒地老的孤獨。
接下來的行程,導(dǎo)游卓瑪眼神飄忽卻依然興致盎然,九寨風(fēng)光美不勝收,其間她組織大家付費一百元到“古老的土司寨”觀賞了藏族風(fēng)情表演。青稞酒,酥油茶,哈達飛揚,歌舞如海,尖叫像密集的鴿哨,這才是“原始狂野神秘”,才是“能歌善舞、熱情善良”,這才是“真正”的藏族特色啊,我的同伴們受了傷害的心又開始煥發(fā)出矜持的熱情。而我,觀賞著旅游產(chǎn)業(yè)精心打造的“原生態(tài)”,心底又一次隱隱作痛回想前日的情景。是的,這同一片寥廓的天與地,它們都是我的母土,而那立在高原曠野上飛淚訴告的胡亂草率的婦人,她和眼前這些被商業(yè)文化包裝的鮮艷精致的孩子們,都是我遺失在時間中的親人。可是啊,走了這么久,家園和人都已千瘡百孔,都已經(jīng)凋了容顏變了聲音,當我們?nèi)绱讼嘤觯覀內(nèi)绾蜗嗾J?
后來,相似的情景,在廣袤的西部不只一次地遭遇過。在自小從民歌里認識的吐魯番,葡萄架下除了美麗的姑娘,更是大宰外地客的商農(nóng)。本應(yīng)在自家院里享受清涼和天倫的老人被安置在驕陽下的大路邊,身邊立著漢字的牌子“和維族百歲老人合影5元”;在內(nèi)蒙古,一片又一片裸露的沙地橫在藍天下,像一道道觸目驚心的傷口,呈現(xiàn)著今日草原之殤;在我的家鄉(xiāng)甘肅南部,藏族留守兒童們每逢集日就和鄰近漢族村子的孩子們一樣,放下功課去城里做買賣,他們的雞蛋要比普通的雞蛋賣得很高,因為那是城里人需要的“土雞蛋”,但實際上村里幾年前就沒有叫土雞的那種雞了。孩子們賣了雞蛋然后買各種黑心作坊加工的不安全不衛(wèi)生食品,還買地攤上幾塊錢一張的亂七八糟的影像碟片,反正,外出打工的阿爸阿媽們互相攀比早就為家里置辦了VCD,DVD,反正爺爺奶奶管不了他們……
就是這樣——當然,我并不是說我沒有看到富強進步,看到團結(jié)和諧,然而,當我總是看到另一些無法忘記的生活的碎片時,它們以尖銳的觸角弄疼了我,卻又讓我無力表述。我無力表述的總是越來越多。我多么希望它們只是“西部風(fēng)格”,而非“中國特色”。
常常想要在閱讀中尋找答案。知道有“西部文學(xué)”這么一個曾經(jīng)輝煌的存在,知道它至今還吸引著“東部”的目光,也認識一些依然活躍的“西部作家”,以及更多的“西部少數(shù)民族作家”,所以我試圖在別人的文字里看到我所置身的西部和我的民族,在今天的情狀。但我每每失望。總是浮泛而虛弱的呈現(xiàn),總是停留在一個類型化的抒情時代,大家千人一面地在作品中鋪排、呈現(xiàn)“西部”和民族文化中的一些表象的成分,這些成分在許多時候僅僅是一些地域風(fēng)情性的標簽和符號,總是用這些缺少精神支撐的地理和文化標簽、符號制造出來的神秘的宏大,荒涼的崇高,虛飄的神性。我知道,在眼下,有關(guān)少數(shù)民族,有關(guān)藏族,有關(guān)青藏,題材本身就是一種極富價值的資源,有許多人在“東部”陌生化的期待視野下進行著這樣取巧的寫作——在潛在的功利性美學(xué)目的、懶惰的思維、固定的套路下的寫作,那種放棄了難度的匱乏現(xiàn)實感情和現(xiàn)實能力的再現(xiàn)型的寫作。而我,我所有的,也不過是雖豐富直觀但零散表面的膚淺的感受和認知,當我無力從今天的城市生活中抽身而出,“藏族”于我越來越只是一種深厚的母族情懷和永恒的故鄉(xiāng)記憶,我無法從根本的理性的意義上去把握那片土地的過往、現(xiàn)在和未來,無法達到從經(jīng)驗的分散性上升到理論的統(tǒng)一性、思想的高度性。我也只能是浮光掠影,得其貌而失其神,如鏡中花瓶中水,更如水中之魚,載浮載沉于與生俱來的慣性中,久而已不知水的冷暖,更無法在一定的距離外完成對水整體的審視。
這就是我為什么到現(xiàn)在不敢貿(mào)然去碰去寫藏族題材,非不為也,是力不逮也。我不能僅僅給自己筆下的人物貼上扎西、卓瑪?shù)臉撕灒瑑H僅給作品置入草原、牧場或半農(nóng)半牧的背景,然后寫一個似是而非的因為高地因為苦難因為信仰所以崇高所以純粹所以神性的“西部”故事,不,我不能容忍如此地“利用”自己天然的民族身份,和“東部”的“看”。當然,寫母族題材毋庸置疑是我的一個心結(jié),我祈愿會在對的時間與此邂逅。福克納的故鄉(xiāng),是一枚郵票大小的地方,因為他了然于胸,所以開掘出了一個深遠廣大的世界。我深信我的故鄉(xiāng),那些亙古的藍天白云,藍天白云下那些寬闊的草原,以及從草原一路往西往東的更廣大的西部,那些有多么悠揚就有多么憂傷的牧歌,那些在綿延不絕的天災(zāi)人禍中痛失往日面貌的山川河流,有一天一定會從我的夢中走到我的心中,流到我的筆尖,結(jié)晶成一顆疼痛炫目的珍珠。
曾在北戴河認識一個陜西作家,因為我又“西部”又“藏族”的身份,他對我非常熱情。他曾去西藏旅游兩周,回來后寫成關(guān)于藏人生活的長篇小說一部,據(jù)他自己介紹說相當不錯。當他了解了我的創(chuàng)作情況后,他吃驚地問:“你為什么不寫西藏?不寫你們藏族人自己的故事?”這樣的問題,我之前之后許多次地面對,在我的族人內(nèi)部,它更表現(xiàn)為一種有力的質(zhì)詢和不滿。我曾那么地躊躇于這個問題。但在認識了這個興高采烈的西部作家后,對此問題的回答我開始有了一句狠話:對于今天的我,寫,是一種迎合;不寫,才是堅守。
陳思和教授說我城市題材的小說并非是他期待看到的西部文學(xué)的風(fēng)格后,又肯定了我的小說值得一說的價值,因為“從發(fā)展眼光看,現(xiàn)代化的都市建設(shè)在西部迅速崛起,現(xiàn)代生活方式及其感情矛盾,也將是西部人所面對的挑戰(zhàn)”。這個句子使用的將來時態(tài),使我覺得多么地富有意味!如果我把將來時態(tài)改成完成時態(tài),改成正在進行時態(tài),把陳教授的“將是”改為“已是”、“早就是”,他是否會覺得非常荒謬,如同我面對“將是”所感覺到的無奈?我所生活的城市蘭州,在東部人的眼里,真的是落后到如此地滯后于時代的發(fā)展,以至于“現(xiàn)代生活方式及其感情矛盾”,都還是將要面對的未知數(shù)?生活在當今時代的東部人,尤其是那些滿含悲憫進而充滿期待的學(xué)問家們,莫非他們真的還在相信蘭州人“坐著羊皮筏子過河、騎著駱駝上班”?相信尕妹妹和阿哥是隔著高山望著平川漫著“花兒”定終身?
這里我自然不想做甘肅、蘭州和許多的東部的GDP的數(shù)據(jù)比較,不用比較也知道這其中的巨大差距;我也不想自辯說我的話里沒有一個西部小城人由自卑而生的敏感情緒,西部對東部了解的總是很多,而東部對西部了解的總是太少,總是太淺,這恰似過去的許多年里,中國人對西方總是知道太多,而西方人對中國則知道得很少——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弱對強的全力關(guān)注和強對弱的余光掃描總是不成比例的。問題的關(guān)鍵不在這里,而在于:事實上就連我的西北邊陲城市也早就被裹挾進飛速運轉(zhuǎn)的擴張性的大都市建設(shè)中,像火輪停不下步子,“現(xiàn)代生活方式及其感情矛盾”,早已是西部人所面對的日常,當“西部”本身已面目模糊,漸行漸遠時,我們的文學(xué)該如何的“西部”?我們是表現(xiàn)這古老的西部大地和民族文化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陣痛、變異和生長,在持守和嬗變中再創(chuàng)造出真正的反映母族大地的現(xiàn)代訴求的新的西部傳統(tǒng),還是永遠地開掘取之不盡的“西部”資源,讓自己的文字成為類似于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風(fēng)俗旅游中那種滿足了“東部”人的優(yōu)越感和獵奇欲的民俗表演?為什么我們在抵制“東方主義”的同時,不能自覺地警惕“西部主義”?
蘭州有一個寫散文的女作家王琰,雖然她尚不知名,但我認為她是為數(shù)不多的優(yōu)秀的值得尊敬的“西部作家”之一。她的文字綿密又空靈地記述了老蘭州城曾有的風(fēng)貌,和甘肅大地上太多值得記錄的古老的人和事。她的西部,不是那些宗教作家筆下崇高神秘得不可言說的神性西部,不是那些浪漫作家描畫的黃沙彌天中刀光劍影、快意恩仇的原始西部,也不是底層敘事的淚水中苦難無邊的悲劇西部,更不是主旋律的歌舞升平中大發(fā)展大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西部,她的西部,是黃河兩岸的人們針頭線腦、一湯一水的真實的日子,是水車悠悠下喝一碗灰豆子的踏實,是隴東窯洞里一窗剪紙的詩意,也是驚濤駭浪中羊皮筏子無處著陸的苦情,涼州故道上葡萄美酒的蒼涼,更是高原的風(fēng)刀霜劍中高唱“阿克班瑪”的不屈。王琰寫出了一個帶著體溫的“西部”。然而——她站在現(xiàn)時態(tài)的蘭州的街頭,卻已找不到她筆下的故鄉(xiāng)。當承載著幾代人記憶的許多物事已然送進了博物館,當四處叫囂著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聰慧的作家,她知道她的西部,終成了“天地遺痕”。
就是這樣。還能怎樣呢?多年前,甘肅有過一個叫張子選的詩人,他寫祁連山,寫阿克蘇,寫阿拉善以西。后來,他去北漂了。他曾說過一句話,在西部,要靠夢想活著。我不知道這話在今天是否適用,因為,今天的西部,其實到處充斥著物質(zhì),和工業(yè)垃圾,可供擱置夢想、擱置藝術(shù)想象的空間并不富余。也許,在今天,在西部活著,和在廣大的別處活著一樣,夢想不多不少,能支撐你在大地上的重量就夠了。這正如,今天,在西部寫作,其實真的不是為了擎起什么旗幟,也不是為了某種宣言,某種說明,它只是一種存在。一種告別了過去,但還不知要通向怎樣的未來的,正在進行著的現(xiàn)時態(tài)的寫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