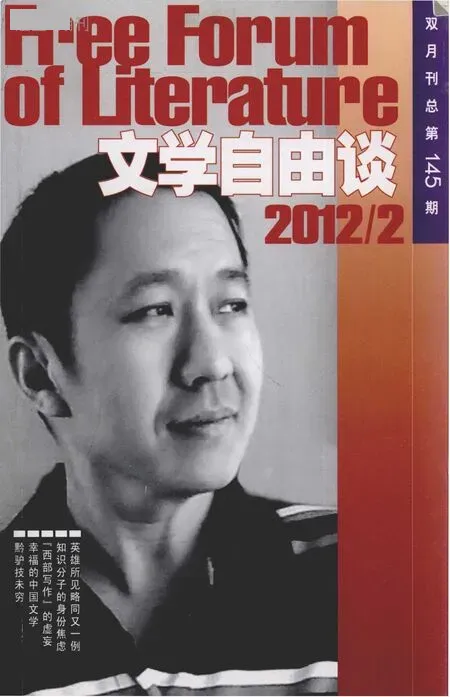我看《十四家》
●文 羅強烈
《十四家》首先讓我刮目相看的,是其文風。所謂敘述,我認為也可以說就是用語言指陳事實的過程。名與實之間的聯系,歷來渠道纏繞,有簡切者,也有繁復者。用美國作家來打比喻,福克納的名實之間就很繁復,甚至語義再生語義;而海明威卻很簡切,語義僅僅指陳事實,然后,讓事實本身呈現意義,《老人與海》便是明證。海明威的文風,當然受到其記者生涯影響;巧的是《十四家》作者,據說也是一位記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曾倡導過“新新聞主義”寫作,其中包括文風,也包括文體。二十多年過去了,《十四家》正是我當初倡導“新新聞主義”寫作時的心儀之作。
我很欣賞作者的寫作追求,包括文風,更包括敘事。用幾乎沒有修飾的語言,把基本的事實陳述出來,就像覺悟之后的塞尚一樣,山和樹都是本來面目,連風和光這些容易討好人的修飾都去掉了。無論是《十四家》作者,還是塞尚,這樣做當然有這樣做的力量。
我們看看翟益偉家的一個生活小故事:翟益偉到深圳打工,母親和三個孩子留守貴州老家;一次,翟益偉托人帶回三百元錢,給一家老小買糧吃;老大翟莎卻想給自己買件像樣的新衣裳,老二翟蘭知道這是口糧錢,見說服不了姐姐,便把錢一把奪過來跑了,翟莎急得拿起菜刀去追趕妹妹;翟蘭跑了一陣回來,弟弟告訴她翟莎上山了,翟蘭以為姐姐是到母親的墳上去哭訴,她上山一看,姐姐吃了農藥趴在那里……最后,翟莎是救過來了,三百元錢卻交了醫藥費。
這個故事的力量,就源于生活的面目沒有被語言遮蓋,而呈現出本身的深沉和多義:十五歲的妹妹知道這三百元錢是口糧錢,十六歲的姐姐能不知道?相濡以沫的姐妹,何以要用菜刀相逼?十六歲的少女想穿件好衣裳,難道沒有充分的理由?她喝農藥尋死,難道不是這種理由最驚人的陳述?那么,最后那三百元錢既沒買上口糧,也沒買成衣裳,而是交了醫藥費,這當然是悲劇,但它卻是一個不只一種意義指向的悲劇。
《十四家》是一部紀實文學,寫了中國西部的十四個家庭,而且是在與東部的對照中來寫這十四個家庭的。從作者的總體追求上看,他寫十四個家庭的基本人生,是想通過這種基本人生寫出人生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意義。人可以穿得花枝招展,但那是衣裳;人可以吃得腦滿腸肥,但那是脂肪;人可以擦得光鮮水靈,但那是皮膚……只有《十四家》這種在柴米油鹽的人生基本形式里的基本生活,才是骨頭,是生活的骨頭,是人生的骨頭!能夠如此對生活和人生入骨三分,是《十四家》最打動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