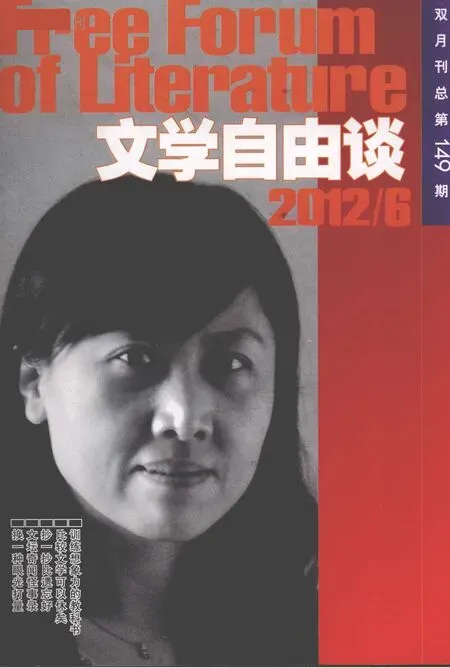關于“ 我”的話題
●文 毛志成
我這里說的“我”,不是指我毛志成本人,而是泛指世上一切由認識他人上升到認識自己的意識品位。這種意識,也可稱之為“我意識”。必須承認,中國無論各式各樣的社會現象、社會行為,還是文學的理性思考、語言表述,真正落實到“我”、深入到“我”,并且從“我”中開發出優質能量,這樣的事并不多。但時而大呼“無我”、時而直呼“唯我”的事卻不乏其例,此起彼伏。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難建設好一個高品位的“我”。
在漫長的蒙昧歷史、等級社會中,對“我”具有很深認識的人往往極少。而有時,“我”又常常是極少數人的專利、特權。總之,“我”的質量和品位都是頗低的。例如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種種不平等的社會中,地位卑下的人至多只是習慣于使用“我們”一詞,而很少使用“我”。至于“我們”,又大多是“小民”、“奴才”的自稱。而敢于宣稱“我”的人,非但必須有某種特權,而且也常常易之為另外的名詞。如皇帝自稱“孤”、“寡人”、“朕”;皇后自稱“本宮”,官吏在平民或下屬面前自稱“本大人”、“本老爺”等等。不難看出,那時的社會從來沒有純粹的“我”。
在中國的古代典籍中,最早涉及“我”(大多時候使用“吾”)的詞語畢竟是有的。這里先舉出三則:一,老子說:“吾之所以有大患也,在于我有身。及我無身,我何患之有!”;二,孔子強調“吾日三省吾身”;三,《詩經》中的《碩鼠》里開篇便說“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結尾又說“吾將去汝,逝彼樂土!”綜上三則可以看出老子很超脫,連“我”的形體(身)都想掙脫,然而雖然高妙但卻虛玄。孔子每天進行三次自我檢查,雖高尚但有刻意之嫌。反倒是《詩經》的《碩鼠》中,一個由奴隸變成的農民有了“我黍”(即屬于我的糧食)的概念,而且發誓離開搶奪我糧食的人,這樣的“我”更真實。但他追求的“樂土”無非是另一種統治者恩賜的“仁政”而已,“我”與真正的自由仍有天壤之別。
我們真要感謝當年歐洲的文藝復興,它所宣揚的人性解放就本質上說,首要的一條就是發現了“我”,承認了“我”,強調了“我”。歐洲文藝復興的文學名著,大都是圍繞著“人本主義”(而非“神本主義”、“權本主義”)而展現的,這其中就必然包括對“我”的特殊看重。以兩部很轟動的名著《十日談》、《唐吉訶德》為例,前者揭露的是欺人的教士,后者嘲諷的是自欺的騎士,這都有自我解放(包括生理解放和心理解放)的意味。這一點,中國的“失我“習慣(包括文學習慣和行為習慣中的“失我”),就顯得太頑固。即使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之首的《紅樓夢》中,最具叛逆性的賈寶玉,對一大群漂亮丫頭的憐愛看起來很有思想解放之意了,其實那樣的“我”也是角色式、主子式的“我”,與天然、本原式的“我”仍有很大的差異。也就是說,假如賈寶玉不是“怡紅公子”而是小廝一名,也不會有“我”了。
但是將“我”推向極端化、無序化成不成呢?也不成。西方曾有人提倡“自然主義”,將人的生理現象視為最大的美;有人宣揚“無政府主義”,甚而把任何的服從都視為對自由的扼殺。這樣真能使“我”游向幸福彼岸么?后來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功勞很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之所以高明,之所以與后來中國極左式的“階級斗爭”大大不同,就在于馬克思追求的是人類解放而不局限于“無產階級解放”。并且強調: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其實,全人類的解放說到根兒上,就是解放世界上所有的“我”。
當年中國曾把對階級的認識推向了絕對化、極端化,好像階級意識、階級立場、階級觀點、階級感情(包括階級仇恨)是人的生存基礎。如此一來,“我”也便徹底不存在了。在愚昧或虛假的社會中,人非但絕不可能走向“無我”、“忘我”的理想世界,恰恰相反,只能使“我”直線地跌入愚化、野化、惡化、偽化,包括等級壓迫的加劇化。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最典型的例子至少有四:
一,“群眾運動”的頻繁,而且那樣的群體式舉動又大都有從上、從眾之意。無論是從上還是從眾,都是對“我”的壓制或撲滅。
二,即使在號稱“階級友愛”、“階級感情”、“階級兄弟”的群體內部,尊卑、貴賤之分也未真正抹平過。一個廠里的書記、廠長何曾把普通工人看在眼里?一個村里的大隊書記、大隊長何曾把貧下中農當成平等的人?擴大一點說,官和民盡管可以握手,可以交談,但恩賜和感恩的心理也往往是雙方的習慣。也就是說,雙方的“我”都像角色而不是人本身。
三,另一種在認識上的誤區是:將任何的獨立人格、獨立意志、獨立思維都視為集體主義精神的敵人,或把任何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強都可以貼上“一切聽從組織安排”的標簽予以寬容或縱容,這都是對“我”的否定。
四,在上述的盲動現象越來越引起社會的冷漠,在后來的“經濟掛帥”、“物質第一”之風盛行時,反彈出的必然是自私自利的流行化,個人主義的神圣化。于是,“以自我為中心”也就成為一時的精神導向。這是“我”的真正醒悟么?當然也不是。
當前中國某些文學作品中的“我”,似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過分強調“自我”,如自我表現、自我展示、自我體驗、自我抒發或自寵、自炫、自炒等等。如果太“自我”了,是真實的、達標的、高品位的“我”么?也絕對不是。真正的“我”,有一點自私屬性是正常的,也是應當理解和尊重的。但是將“我”推向絕對自私化、極端自私化,非但是反文明的,即使對于文學本身來說,也是一種墮化,因為任何有價值的文學作品都是寫給別人看的,給社會提供價值的。
對“我”的真正醒悟,奴隸式的人永遠做不到,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也永遠做不到,只有真正的主人才能做到。什么是真正的主人?根本的品格是:只做自己的主人,不必去做別人的主人。也就是說,既不做別人的奴隸也不當別人的上帝。無論是意志、思想還是行為、情感,都應具有足備的獨立性和益世性。
不必諱言,所有的文學作品只要是文學作品而非一般性的或單純性的文字,都是有意無意地表述“我”或塑造“我”。特別是作品中的主要正面人物、正面行為,大都有“我”的影子。無論是中國的屈原、李白、魯迅、沈從文,還是外國的雨果、狄更斯、托爾斯泰以及寫長詩《列寧》的馬雅可夫斯基,主觀上或客觀上都有“寫我”的因素。反倒是統統無“我”的御用文人或極左文字,無非廢紙一堆。但是瘋狂式的或病態式的“寫我”,無論是對“我”的過分膨脹還是對小家子氣十足的“我”百般自戀,也都近于垃圾。
任何的正常之“我”、正確之“我”、正義之“我”,都必須首先是人,既不是神仙也不是鬼怪。但人是有品級的,“我”也是有品級的。什么是較高的品級?不是指符號的品級如官銜、財銜、學銜、名銜多么高,而是指人本身在德智上的真正趨高。
中國離真正發現“我”、形成“我”、健全“我”仍有不小的距離,必須努力向更高的境界邁進才成!
中國古今文學的寫人,先是專寫“他人”而很少甚而絕不寫“我”;今天卻熱衷于專寫“我”而不太理會“他人”,故而難以出現在世界上有極大撼動力的作品。古代、前代專寫他人如《西游記》專寫神仙鬼怪,《三國演義》專寫文武杰才,各種傳奇、話本專寫德才超眾之人,幾十年前又專寫“階級的人”(包括窮則必革命和富則必反動的人),“文革”時期又提倡去寫帶有“三突出”、“高大全”意味的人,總之寫的都是“他人”。想在那里找一點“我”的痕跡太難了,弄不好還會招來“反動”、“思想有問題”的禍殃。殊不知沒有真實的“我”,豈會有活生生的“人”?
今天又將專寫“我”視為文學時尚的主要標志,所謂人生也無非是“我”個人的人生,似乎與民生、眾生無關。好像無論是“我”的哀吟抽泣還是“我”的醉話、瘋話,包括“我”的吹牛、罵街、撒潑,都成了時尚文學或新潮文學。其實從哲學的角度來講,識我與識人、立我與立人、利我與利人都是辯證統一的,失去一方都不能成立。世上統統失去了“我”固然任何的“人”都會變成虛假的影子,但不觸摸“人”、不走近“人”、不尊重“人”也只能使“我”成為孤魂游尸。
當然,任何美好的道德理念和真正的大智之舉都必須首先落實到“我”,否則什么好事也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一經將任何的無德、發昏之事都賦予合理性,也只能導致“人我互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