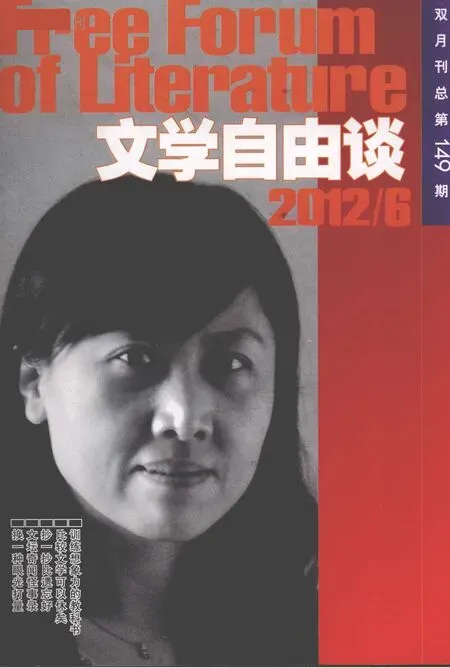金鈴子·馬占祥
(兩 章)
●文 嚴英秀
●文 嚴英秀
金鈴子:我正在過分地愛
金鈴子在魯院第一次隆重的師生見面會上,做自我介紹時,用極具特色的川味普通話念了那句著名的話:“美,是困難的。”然后,她說,詩也是困難的,雖然我已經寫了二十年了。
然而,從別人的眼睛看過去,詩歌于金鈴子卻是并不困難的,甚至,那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她天生一副詩人相。也或者,是二十年的詩歌生涯打造出了她今天的容貌?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但她的漂亮絕不等同于一般世俗女子的嬌艷和嫵媚,那是專屬于一個女詩人的美。那種美有著猙獰的力度。金鈴子有一頭濃密的黑發,有時候,她把它們編成許多的小辮子,使自己充滿異族女人的風情。更多的時候,它們在她的肩頭洶涌澎湃著,劍拔弩張著。那是一頭桀驁不馴的鬈毛,綠鬢似云、青絲如瀑之類柔媚的詞語無力形容這樣的頭發。它更容易讓人想起曠野之草,想起刮過曠野之草的野火,想起野火中飛馳而過的駿馬那高揚的鬃毛。
四個多月的時間也長也短,我算不上是金鈴子走得很近的同學。魯院時光的彌足珍貴未能改變我素來的疏懶,而鮮艷的金鈴子其實也是沉靜而踏實,她每日緊閉房門讀書,寫詩,還為一份刊物編著詩。她按時作息,從來都準時出現在課堂和食堂上,而且,她常常在課堂向老師認真提問,常常在課后還和同學熱烈討論。她實在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好學生,這使我們從未感受到“隔壁住著一個詩人”的刺激和驚悚。好長一段時間,我們只是在過道微笑牽手,或者在教室門口高大的鳳尾竹下互相欣賞換季的衣衫。但這樣的疏淡并不影響我們之間發生了通透的了解。她曾在我午夜夢酣時打來房間電話,說,親愛的,我睡不著,因為讀了你的小說。她激動地發問:你為什么,要寫這樣的愛情?你真的相信,世間有這樣的愛情?她的語氣,似是咄咄逼人的質詢,我卻聽出了小心而熱切的求證。但恍惚間,我難以給她鏗鏘的回答。自此后,我們聊過一些深入的話題,關于故鄉,成長,關于女性,婚戀,家庭等等。她有兒子正讀高中,她對老公,有一個孩子般親昵的愛稱。當然,聊得更多的還是關于詩歌。我們也說起那些有關詩壇的飛短流長,種種的相互攻訐,那些以詩歌的名義進行的不堪和卑劣,以及做一個美麗端正的女詩人的不易。金鈴子說,讓詩壇見鬼去吧,我只關心詩歌。金鈴子說,當有一天,我離去,我將留下對這個世界響亮的嘲諷。
我將留下對這個世界響亮的嘲諷。后來我一遍遍玩味著這句話,我是多么欣賞她的快意恩仇。但對于我,這個比耳光更響亮的嘲諷,比嘲諷更徹底的棄絕,還要怎樣地讓時間一步一步抵達?南行途中,我們不約而同在同一家店里買下了同一個款式的連衣裙,但顏色是不同的,她選了向外綻放的大紅,我選了兀自干凈的暗綠——這簡直像一種隱喻。
因為喜歡,我認真研讀了金鈴子的詩。和她的人一樣,她的詩是那種具備了鮮明的精神氣質的詩。讀這些詩,你知道她為什么而寫,是怎樣強烈堅定的熱愛之情在震擊著她的心靈,是怎樣苦痛而炫目的理想之光在照耀著她的詩筆。她愛著,恨著,她不可壓抑地追求著,無與倫比地孤獨著,這些元素決定了金鈴子的詩是內心有力量的詩。那首長達一百余行的《青衣》開篇沒有設置絲毫文字的銜接,沒有蘊蓄任何情緒的鋪墊,自由的激情如同噴薄的地下火橫空出世:“這奇異的世界不能久留。我們去死/這見慣的青春不能久留。我們去死/這些詩篇不能久留。我們去死/這平常,平常不過的愛情不能久留。我們去死。”就這樣,素常的詩歌詞匯在她筆下有了黃金般的質地,暴力般的沖擊力。金鈴子寫過一首自白式的詩《我寫詩,我只寫詩》:“我寫詩,我只寫詩/這世界總讓我激動得顫抖,讓我伸出一百只手/抱住一朵桃花的表情/抑或一株清明草的歌唱/你叫我怎么辦呢,這消滅不了的快樂……/我總能找到,胡言亂語的理由/我是這個季節吞噬的又一個人。另一個人/再一個人……/我多想將這個春天固定下來。”其實,在生命中的某一瞬間,每一個人都是詩人,當我們處在一種特別美好的情境中,當天地萬物都讓人深深感動時,“你多美呀,請停留一下”,便是最真實自然的心靈的呼喊。金鈴子把這種太多人都經歷過而又遺失的詩歌沖動固定下來了,把那些喚醒過我們的美好場景固定下來了,把人類對純粹世界對美好自然的渴望和熱愛固定下來了,把一切不復再來的時光固定下來了。所以,當她說,“我寫詩,我只寫詩”,“你叫我怎么辦呢,這消滅不了的快樂”,你又怎能拒絕她的詩,她的快樂?
金鈴子喜歡在詩歌中用“親愛的”“我愛”這樣的語詞,這使她的大多作品都披上了愛情詩的外衣。其實它們之所指是廣闊而深邃的,當詩人深情地喃喃,那么在她靈魂深處應聲而出的那個“親愛的”,“我愛”,可能是她愛過的一個人,可能是她愛著的許多人,也可能,就是金鈴子自己,更可能,就是詩歌本身,“親愛的,我就是你向世界宣戰的理由/是你所有愛過的花朵中最痛的那朵”。所以,你難以從金鈴子的詩里窺視到那些所謂“女性詩歌”欲蓋彌彰、欲露又遮的低暗風景。她訴說的是關于我們,我們每個人的“山川。草原。黑鳥/無數迷路的夜晚”,和“街道愈來愈荒涼”,是“陽光與露珠在城市游走/這里需要田野、糧食、花朵、音樂”,是我們共同的手“埋掉的那棵梧桐/它的痛和殤,它強烈感情的微弱共鳴”,是“我看見一切都迅速離去,我看見/人們相遇,相愛,絕望和死亡/留下一望無際的貧瘠”之后再誕生的“嶄新的悲愁,嶄新的快樂”,所以,她說“我的苦難不多,卻疼痛了每一個地方……/今夜,我只與死于心碎的人們在一起”,所以,她說:——“我一度是你的,也永遠是你的”。
金鈴子說:詩歌的力量與語詞無關,只與氣質有關。這是她作為一個詩人的自覺,警誡自己不要追求外在的辭藻形式,而應追求內在的精神氣質和力量。但實際上,離開了語詞的氣質是不存在的,任何氣質都是通過語詞來實現的,語言抵達的地方才是思想抵達的地方,所以,金鈴子獨一無二的語詞世界正是她區別于另外一些詩人的重要標志。她的詩歌語言從不云里霧里的繞,從不模棱兩可,可有可無,似是而非,她直接,素樸,但又決絕,險峻。那樣的語言,你一讀就會被它抓住,被它擊中,讓你一下子深陷其中,跌到現場感的蠱惑中,不由自主地被一種真正的純詩所噴發的巨大的能量淹沒。金鈴子,其實她深諳語詞之于氣質的舉足輕重,她說:“我這樣厭倦了詞語/它們讓我左右為難/十分棘手。有的詞語/仿佛莊嚴的雪,堆在心邊/我真害怕,稍不留神,就悄悄化掉/有的詞語,藏滿火焰/恰似鐵的枝條上,花朵等待燃燒/我不敢去碰它們,擔心一碰/花蕾中的火星,就會畢畢剝剝地炸裂,留下淚水的灰燼/有的詞語,渾身是刺,如同眼中的/釘子,奪眶而出,那么的快速/那么的驚心,好像/尖銳的往事,一下子就將我釘穿……/有的詞語,就是明明白白的石頭,既硬/又重,對于我的愛情,它就是/泰山壓頂……”
請看這些讓金鈴子坐臥難寧的語詞成詩后的形貌,她寫愛情,“九月的風,它們經過那桂花/花香,一碰即碎。你無法聽見花的憂傷/我很想模仿一些姿勢/從頭發、手臂、嘴唇、眼睛,長出容光的葉子/并開花/只為你,親愛的/有東西叫這花死得,又慢又苦/你叫它季節,我叫它愛情”;她寫失眠,“黑夜這只野獸太大,我一個人背不動/我還動用了繁星,動用了月亮/黑夜這只野獸太大/它的奸險是1米多長的獠牙,它的貪婪/是具有5噸容量的胃/它的兇狠一旦亮出來,1000畝廣場也難以裝下/黑夜這只野獸太大,比白晝的長壽湖/還闊,比沉痛的歌樂山/還重。我的悲哀,僅僅是它身上的一根汗毛/我的幸福,被它一腳踩碎……”她寫天氣:“雷雨當前,我應該準備好自己的天空/重新整理骨頭里的閃電/理順頭腦中的狂風……”她有時也迷惘:“我不知道為什么/我視力有限,卻縱情于遠觀……”她愈來愈堅定:“我必須低下頭顱/用想象不到的勇氣/成為一個壞人/一個罪人/一個,一看到懸崖絕壁/就跳下去的人。”
魯院園子里,有兩棵很大的桑樹。二月底我們初來時,它們只是默立在蒼黃的天底下,滄桑的枝干上看不出一點蠢蠢欲動的熱情。三四月份,白海棠、紅櫻桃們把園子開成畫一樣了,它卻也只是沉靜地撐起一樹簡單的綠。然而,六月就不同了,到了六月,桑樹脫穎而出,成就了萬眾矚目的豐碩和華麗。數不清的桑葚一嘟嚕一嘟嚕掛在枝葉間,先是澀澀的紅,繼而是濃濃的紫,最后成了誘惑的黑。于是,樹下出現了許多的手,許多的嘴。大家從桑樹上摘下桑葚,連最愛干凈的女生們也沒有拿回去洗,而是直接放進嘴里。許多年沒有這樣了吧,桑葚的甜美和甘醇,是陽光的味道,童年的味道,純天然無污染的舊時光的味道。
七月忽至,歸期已近,而桑葚卻像是永遠也吃不完似的,熟透的果子噼里啪啦砸在草地上,砸在青磚地上,將汁液迸濺的抹不去的傷感彌散開來,空氣中發酵著一場巨大的離別。于是,漸漸地,僅剩的日子里,很多人不再到桑樹下徜徉了。
詩人金鈴子是那個越到后面越燦爛的“桑葚分子”,她穿著各式花裙子在樹下拍照,聊天,她朗誦自己的詩“我見過的愛情很多,可是,沒有那一個像你和我”,她揮著手霸氣地宣布“我們都是瓜娃子”,她旁若無人地唱李白的《將進酒》和《詩經》里的許多篇章,所有我們平時只能用來讀誦的古詩詞,她都斬釘截鐵地唱出來。她的歌嗓并不優美,但卻有著和那些永遠的詩歌們相匹配的酣暢淋漓。她不停地吃桑葚,就好像再不需要吃別的食物了似的。她開始在桑樹下大聲地哭泣。
她說,我知道我在過分地愛,我要的就是這樣的愛。我正在愛和更愛之間墮落。
馬占祥:我的訴說高不過一座山
寧夏和甘肅比鄰而居,據說以前是一家子。我去過寧夏的許多地方,但認識寧夏詩人馬占祥卻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我見馬占祥時,他已譽滿京城文學館路上一處幽靜的小院了。據說馬占祥坐汽車趕火車,風塵千里,車馬勞頓,終于到了那座著名的魯迅塑像下,他卸下行李,感慨萬千地說道:“唉,北京真是太偏僻了,離我們寧夏這么遠!”就像眼下一些偉大的作品被慷慨的評論家提前送進文學史一樣,馬占祥這話一經在小院子里大面積鋪開,面臨的便是毋庸置疑地被經典化,而他個人隨即也迅速地被名人化。沒辦法,出名要趁早,現如今,這是硬道理。
但馬占祥卻是一個安靜沉穩的小伙子。一身機關干部的打扮和中規中矩的小平頭,使他和另一些從頭到腳洋溢著詩人符碼的人區別開來。把他和別人區別開來的還有吃飯。吃飯時,他遠遠地一個人坐在清真席上。他是人群中惟一的回族。后來,大家熟了,不十分拘禮了,便也端著飯盆坐到他那一桌。但無論是笑語喧嘩三五成群,還是形單影只向隅而坐,馬占祥都是那么安穩,他篤定而自信。從他的背影,讀出的不是孤獨,而是孤獨的力量。
使馬占祥激動起來,使馬占祥名副其實像說出北京太偏僻這種狂話的詩人馬占祥的,是酒。馬占祥愛喝酒,據說常常喝,據說喝完了常常激動。我有幸見證過一兩次他的激動,紅著臉,從座位上搖搖晃晃地站起,他說,大家安靜一下,我給你們唱個寧夏花兒。說完他低下頭,捏緊拳頭,像是在下一個很大的決心。然后他猛抬頭,用極悲愴的表情喊出:
早知道黃河的水干了,
修他媽的鐵橋者干啥呢?
早知道尕妹妹的心變了,
看她媽的臉色者干啥呢?
他說是寧夏花兒,其實這是甘青寧黃河兩岸廣為流傳的民謠,我多次聽到過不同版本的演唱。但這一次,在遙遠“偏僻”的北京,在喧囂萬丈的都市之夜,聽著詩人馬占祥在來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調的人群中用極西北的味道吼出我諳熟的蒼涼,我內心還是被震動了。一時間,千年旱塬上苦情的黃河風卷著他的聲音呼呼地從我身后刮過。
后來,我讀了馬占祥的詩集《半個城》。半個城就是馬占祥生活在寧夏的小縣城同心的別名。馬占祥生在寧夏,長在寧夏,他無可選擇地熱愛寧夏。半個城,雖然是“這座不顯眼的小城,在傳說中失去了半個城”之后剩下的另一半,但它“依舊養育著莊稼河流大地和人民”,所以在詩歌里,它是完整的,是被放大了的。那就是馬占祥用赤誠的文字建構的詩歌寧夏的形象:西部的,干旱的,回族的;苦難的,堅韌的,壯美的。這是地理學層面的寧夏,更是精神意義的寧夏。馬占祥深情歌詠了寧夏廣袤的大地上那些被前人悉數寫過的壯懷激烈之地:六盤山,賀蘭山,西夏陵,騰格里,西海固。他有理由在這些名詞里自豪沉醉,做出登高望遠凝眸歷史的姿態,因為他確實寫出了那種裹挾天地的浩然長風,那種蒼莽渾黃的西部氣息。但他沒有這樣,不僅僅是憑吊昔日之榮光,而是撫慰今日之疼痛。他用詩集中占近三分之二的詩篇,細微精湛地展現了那些卑微、沉默、堅忍的山山水水,一村一壑。他詳盡描述了所有滿含希望又收獲淚水的農事,那些過早成熟的山芋苗,沒能高過手指的糜子……寧夏南部龜裂的山川大地,就這樣柔軟地豐潤地走進了馬占祥的詩歌。
海德格爾說過,歸鄉是詩人的天職。幸運的是,馬占祥不需要尋找,不需要歸去,他從來都在那里,他生命和詩歌的根都深深地扎在那里——半個城,這是具體實在可感知的地理學的故鄉,更是一個他聊以安妥自己靈魂的精神家園。他在《小城之一——同心》里寫道:“城南是一條河。它如一雙手般/將小城同心托起。而旁邊一塊闊大的墳地里/有我的爺爺。三個奶奶。兩位兄長。已無法數清的鄉親以及/剛剛大去的李阿訇。城北一大片蕎麥長勢良好。一大片玉米/迎風挺立。我的父輩在小城同心生活過,我在小城同心/生活過,我的后代也會一樣。在小城同心滿足而安然。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不止這些,在馬占祥厚實悲憫的詩歌里,可以肯定的還有更多的人和事,那些苦難而親愛的地名共同構建了他的寧夏“干旱的地理”:“小城西吉如此狹長。像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從清晨到/傍晚。它依次發召喚聲。誦經聲以及祈禱聲/長長的聲音布滿了整座小城。它安詳平和卻包含了/更多……那里還有些堅韌的人。身穿長袍。將頭叩向大地。心中燃著/火焰。仿佛傳說中的部落……”;在就連“向日葵都放棄了春天”的山城固原,“在山與山的間隙。總有秦腔抑或花兒飄起/那是怎樣的聲音啊/我該炸裂幾次才能干凈地收聽”;“窯山,這大地上的一粒暗痣。內心蘊藏著/煤炭般的黑焰火。在五十載不遇的大旱之年/只讓絨毛般的芨芨草淡淡地綠了一下子”;“十萬山巒洶涌著聚集張家塬,抬起或深埋了/無數村落。那一刻:鷂鷹收攏了雙翅陡然沖向擁有/三棵老槐的山灣”;“我可以肯定堡子山是寂寞的。一個撐天的高大身影在/小城涇源/撐起云朵。鳥鳴。山風。留下陽光。水聲。它經歷了/更多的目光的/質詢。因此它可以見證:一個漂泊的人在小城涇源/聽到水聲……”
就是這樣,干旱缺水、荒涼貧瘠的寧夏高原,賜予馬占祥的卻是一個雨水豐沛、蔥蘢自足的詩歌世界。故鄉成就了馬占祥,一生“在塬上尋找糧食和水”的父老鄉親,給了馬占祥一雙以悲劇的重量輕盈飛翔的翅膀。他沉重卻不蕪雜,澄澈而又深邃,他隨意拙樸又深情蒼涼的詩句使一個叫“半個城”的地方巋然屹立于中國當代詩歌的版圖中。
馬占祥在詩集后記中說道,寫詩二十年,從初次提筆的頑童時期已到兩鬢漸白,詩風由抒情轉為寫實。的確,馬占祥的詩看上去非常樸實,因為他以極寫實的手法描述鄉土世界,但實際上,他的寫實既有抒情的傳統的根基,又具備一種內在的現代特質。他用詞簡約,語言克制,摒棄了可有可無的辭藻和修辭,詩句短小精悍,富有張力,尤其在意象選擇和轉換上,自然輕巧,不著痕跡,但又有深入廣闊的內容開掘,表現出了一種特別的現代意味。他常常從突兀而起的日常場景和思緒的承接轉換,飛躍上升到一個人在完全的寂靜和孤獨中所感受到的對生命、空間的觸摸和徹悟,這樣的詩不見虛弱浮泛的吟唱,內在的支撐使詩句每一個字都瘦骨如銅,錚錚作響。馬占祥生活在“回民的黃土高原”,這使他的詩歌創作必然地籠罩在宗教的光環下。但他袒露在詩歌里的,除了信仰者的虔誠,還有作為思想者才能達到的審視高度,這種內蘊的勇氣和精神使我非常贊賞《參加楊輝爺爺的葬禮》這首詩:“六月酷熱,那個被楊輝稱作爺爺的人走了……/他在81年中一直達觀而/平民地活著。在最后仍保持著低調的/作風。我仔細地再次端詳了這個老人/胡須花白。臉色平靜。仿佛一塊平靜的/石頭。阿訇在他身邊用《古蘭經》的章節/成全他。其實這個老人已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他沒有虧欠什么……”
我同樣贊賞的還有《寧夏以南:寫給高原的詩》,在這首詩里,詩人在“一再提及黃土高原,寧南山區,一座山,一條河和眾多莊稼”,提及“山坡羊,苦菜花,陽光,蜜蜂”,提及“戴蓋頭的姐姐皸裂的臉頰”后,卻低聲地喟嘆,“我的訴說高不過一座山”。與這句話相對應的是另一首《我將要到山上去》中的“我不能不到山上去,站在高處,看我生活其中的小城的渺小”。這兩首詩兩句話多么難得,它們交相輝映,寫出了詩人難能可貴的兩個方面:在山川河流,在自然萬物,在沉默勞作的人們面前,永遠保持著敬畏謙卑的態度,永遠清醒地告誡自己,“我的訴說高不過一座山”。與這樣的態度和胸襟相匹配的是,“我不能不到山上去,站在高處,看我生活其中的小城的渺小”的眼界和立場。作為詩人,馬占祥做到了謙卑地低下去,投身于渺小和苦難,從塵埃里唱出了神性的歌吟,與此同時,他又警醒著,掙脫羈絆,完成著對自身對生活的審視:站在高處,俯視渺小。正因為有了這兩樣最可寶貴的秉性,他正在成長為一個越來越優秀的詩人。
今夏,蘭州多雨,黃河水漲潮,幾度淹沒了四十里風情河堤。每日出門憂慮于一場場突降的狼狽時,心中總會驀地想起馬占祥。想起馬占祥在北京的飯桌上,猛地揚起手機,無比歡喜地喊:寧夏的短信,那邊下雨了!寧夏下雨了!他臉上的笑,他眼里的亮,像極了一個孩子在宣布:明天就過年了!——但這樣的歡喜也是孤絕的,并沒有太多的響應和共鳴。人們沉浸在自己的話題中:關于人類明天的走向,關于現代人今天的靈魂,關于后現代時期文學的處境。太多凌空高蹈的深刻思想,使許多人的臉上妝扮著恰如其分的憂患,誰又分得出心去關注一片遙遠天空下的一場小小的雨呢?誰又愿意從滔滔的熱鬧中抽身而出,安靜地聆聽馬占祥訴說正在夜降喜雨的那個小城呢?那里,是他祖輩生活的地方,那里,自古以來,十年九旱,十種九不收,那里,年均降水量只有二百毫米,蒸發量卻是兩千三百毫米,那里,清亮的水源總是離村莊太遠,一位回族婦女行走在下溝上塬崎嶇不平的挑水路上,桶里的水每灑一滴,她就“哎喲”一聲……
那么,現在,寧夏也下雨嗎?半個城,它在下雨嗎?我的城市里這不期而至的連綿不絕的惱人的雨,會不會是詩人馬占祥身后那些苦焦的千溝萬壑久盼的甘霖?那么,那些旱塬上的莊稼,那些堅挺在村口如同戰士般的矮樹,那些在崖畔上開出皺褶的花朵的馬蓮草,不會再遭遇一瘦再瘦的命運吧?
太多的人說,詩歌是無力的。我不是不知道這個,在今天,詩歌的光芒微弱到不足以照亮一條手機短信撒播的短暫黑暗。但我仍相信,一首純粹的高尚的詩歌,就是一場好雨。相信那個婦女濺灑出去的每一聲疼痛的“哎喲”,都讓馬占祥用雙手掬起,捧進了他的詩歌——那是生活對一個詩人所能賜予的最好的禮物:上天的雨水。
2012年秋于蘭州
黃河之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