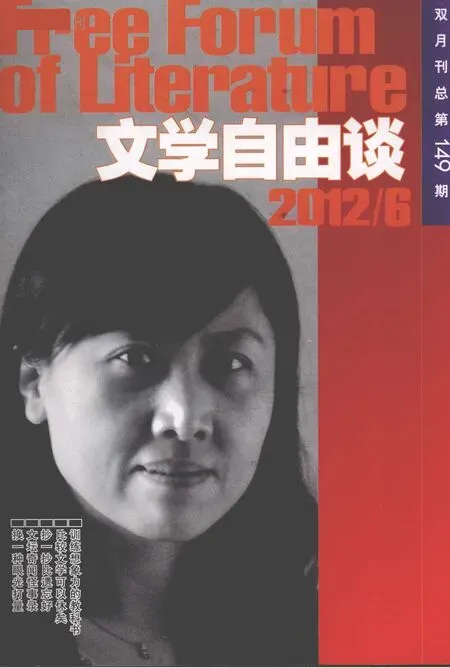耐看的傾斜與平衡
●文 任芙康
女作家中,與一些面相寫滿內(nèi)容的人比,彭名燕是很單純的一位。她的灑脫,她的快樂,甚至她的稚氣,皆自然本色,而無常見的加工。
沒有任何預(yù)熱,靜悄悄地,她又出了新書,實(shí)在令人欽佩。我的欽佩不摻水分,因?yàn)闅J佩彭同志二十多年了。“永葆革命青春”這句口號,原本大而化之,卻被她實(shí)踐得卓有成效。歲月的刀刃好像不起作用,她將已有的七十年人生旅程,舒緩出少有的從容。八幾年的時(shí)候,我為彭名燕的小說寫過評論。北京電影制片廠家屬宿舍,筒子樓里,有一間掛布簾的房間,就是她的家。她的先生畢鑒昌,擅長一石雙鳥地鼓勵(lì)別人,便在屋里高聲誦讀我的文章。老畢是老紅軍的兒子,老紅軍居住在我老家四川達(dá)州的干休所里。老畢又是電影《青年魯班》的主角,主角叫李三輩,與之相對應(yīng)的現(xiàn)實(shí)人物,也姓李,就是后來人所共知的一位領(lǐng)導(dǎo)人。
十來年前,吃過彭名燕一頓飯。碩大的圓桌,聚攏一幫慷慨男女,話題不離“文學(xué)”二字,酷似正規(guī)的學(xué)術(shù)研討。又記得飄進(jìn)一朵花絮,是中途遲到的一位先生,向眾人展示一對貼身姑娘:“我的——學(xué)生。”兩位弟子神色活泛,顯然是師母不在現(xiàn)場,便有了師生同樂的自在。
文壇已然如此飄逸、夢幻,端的是順應(yīng)時(shí)勢的改變,亦可歸類為古典浪漫的回潮。有時(shí)看看周圍,一些先前出道并獲聲名的寫家,早已心猿意馬,棄文而去。有的與文物販子擠眉弄眼,保護(hù)民間文化去了;有的看首長臉色說東道西,醉心參政議政去了。而他們嘴上偶爾蹦出文學(xué)的字眼,無非長袖善舞的飾物而已。然而事情也怪,愈是此類貨色,愈能唬人,愈易搖身現(xiàn)形為文化泡沫中的大師。
相形之下,從我認(rèn)識彭名燕,她就一直在寫小說。量高、質(zhì)優(yōu),就這兩條,凸顯她的過人之處。一位作家,光耀的程度,取決其寫作的狀態(tài)。如果都能像彭名燕,為文散淡,再加精神不老,自然就錦上添花了。她的新書,名字讓人詫異:《傾斜至深處》。讀完才曉得,光怪陸離,當(dāng)代內(nèi)容;酸甜苦辣,域外家常。此種題材,因故事的稀罕、離奇,多年來吃香、受寵。但讀來讀去,車載斗量的成品,多屬滄桑的“漂泊”。而《傾斜至深處》,登堂入室,全是“定居”的故事。定居讓人踏實(shí),已跨上質(zhì)變的臺階,標(biāo)志人生駐留,抵達(dá)一處相對消停的驛站。
自國門開啟,遠(yuǎn)行的學(xué)子,次第畢業(yè),擇業(yè),安家。恍惚間,又有不少土生土長的熟人,成了非黃種女孩的公公、婆婆,或是非黃種男孩的丈人、丈母娘。接下來,一帆風(fēng)順的訊息便難得再有,如四季光陰,春的暖,夏的熱,秋的爽,冬的寒,時(shí)隱又時(shí)現(xiàn)。說來很正常,閱歷不同,背景不同,習(xí)俗不同,新鮮勁兒過去,舌頭跟牙齒就得打架。然后要么絕裂,要么妥協(xié)。但世間通用的文明,往往可以規(guī)范彼此的底線;人性內(nèi)在的溫度,往往可以融化相互的尷尬。
這一切,由彭名燕投影到小說中,人物的打造,細(xì)節(jié)的鋪陳,思想的激蕩,立意的高遠(yuǎn),無不套路新奇,表現(xiàn)出文學(xué)疆域的新開拓。這部小說常給人錯(cuò)覺,以為捧讀的書頁中,所載凡俗與高雅,簡陋與奢華,概屬真人實(shí)事,并非虛構(gòu)之物。這樣也好,你若有同樣的困惑、苦悶,盡可在閱讀中受到啟迪,得到釋放;你若有同樣的喜悅、感動,盡可在閱讀中找到印照,得到放大。其實(shí),即或你無緣書中境遇,依舊可以分享作者心得,從而展擴(kuò)認(rèn)知廣度。《傾斜至深處》顏色、味道濃淡相宜,而形狀乃工筆兼寫意,與彭名燕的經(jīng)歷、氣質(zhì)頗為配套,實(shí)可謂相得益彰。
傾斜與平衡,本是不可或缺的人生功課。姑且以女人為例,索性就說寫作的女人罷。她們的生活應(yīng)當(dāng)平衡,她們的精神則需傾斜。光有平衡,缺少傾斜,她就寫不動了;光有傾斜,而無平衡,她就寫不穩(wěn)了。瞧這位彭名燕,舉重若輕地,過風(fēng)姿綽約的日子,寫氣韻獨(dú)特的小說,將傾斜與平衡的演進(jìn),營造出耐看的景致,明晃晃耀人眼目。難以仿效的高妙,亦令友朋喜悅不已,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