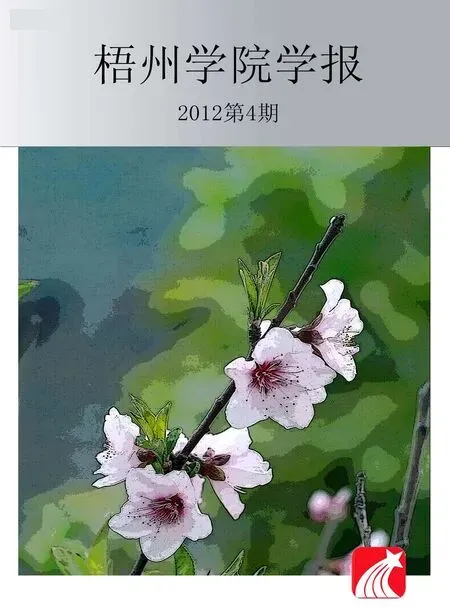中國生態家園的詩意建構
——從“大同社會”、“至德之世”到“世外桃源”的藍圖設計
宋堅
(欽州學院中文與傳媒學院,廣西 欽州 535000)
中國生態家園的詩意建構
——從“大同社會”、“至德之世”到“世外桃源”的藍圖設計
宋堅
(欽州學院中文與傳媒學院,廣西 欽州 535000)
和諧生態家園的詩意建構,是中國理想社會形態的表現形式。“大同社會”代表了儒家的人文綠色的生態社會理想;“至德之世”則代表了中國道家和諧的生態理想形態;“世外桃源”則上承儒家的“大同社會”人人平等的理想,下接道家的“小國寡民”的淳樸民風,其仙境一般的美妙世界,成為人人向往的生態樂園。三種理想社會形態都共同凝聚了古代智者的思想精華,同時又因其濃郁的烏托邦色彩而具有超越性質。盡管內容與形式上相互區別,但其價值指歸是一致的,它們都蘊含了豐富的生態審美思想。
社會理想;儒家;“大同社會”;莊子;“至德之世”;陶淵明
中國人歷來向往“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努力構建人與萬物相親共融、人與人和諧共處的合理生存情景,設計了人人平等、人間太平的大同社會,由此構成的以儒道為代表的生態文明社會的理想模式深入人心,影響久遠。儒道兩家代表都以詩意的筆墨和濃厚的人文關懷精神,描繪了人人向往的理想生態藍圖,從而給人們提供了“詩意棲居”的人間樂園。
一、“大同社會”:人與人睦鄰友好的人文生態藍圖
“大同社會”代表了儒家的社會生態理想。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傳統的主流思想。他強調的是“自強不息”的積極入世思想,以匡正時弊、拯救天下為己任,通過人格修養與內心的提煉,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實現,從而建立一個太平盛世,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儒家經典《禮記·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儒家設計的一種十分理想的人文生態社會模式。在這樣的社會里,執政者大公無私,昭行大道于天下,任用賢能,政治清明;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人人講誠信和睦,相親相愛,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大家過著其樂融融的生活。由此社會太平,人人自得其樂。歷史上出現的“成康之世”,“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唐朝“貞觀之治”迎來的太平盛世,社會上出現了“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太平景象,正是“大同社會”的真實展現。
其實中國很早就有“大同社會”的萌芽。《詩經·碩鼠》曾提出了“樂土”、“樂國”、“樂郊”的美好社會形態,在那里,沒有剝削和壓迫,人人平等,其樂融融,是早期“大同社會”的雛形。在面對禮崩樂壞、諸侯紛爭的現實社會,孔子遵循西周禮樂時代的太平盛世,設計了符合儒家理想的“大同社會”的和諧藍圖,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文明社會的概括總結。在這樣一個社會里,人人和睦,互敬互愛,自由祥和,美滿友好。“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指太平盛世中圣人之治的社會風氣,人人尊崇大道,以天下為公,無絲毫私心雜念;“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大同社會的政治理想,社會有評價人才的良性機制,做到任人唯賢,唯才是舉。人與人的平等關系及誠信程度是生態文明社會最重要的指標。在社會道德上,大同社會沒有欺詐和盜竊,人人都為他人著想,人與人之間和睦融洽,大家團結友愛,童叟無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更是一種胸懷天下的博愛精神,人人思想高尚,所以信任和睦成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大家都沒有利益爭端,而是盡其所能地為社會和他人作貢獻;大家共同享用勞動成果,同甘共苦,榮辱與共,承擔風雨。由此社會太平,路不拾遺,生活過得十分富足,精神祥和安寧,身心舒泰安逸。
大同社會的生態藍圖是幾千年來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正是秉承了以人為本的生態理念;孫中山的“天下為公”正是以創建“大同社會”為己任。近代思想家康有為在他的《大同書》里描繪了一幅大同社會的理想圖景,這是一個至公、至平、至仁、至治的極樂世界。它“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1]108康有為的《大同書》既是對古代“大同社會”的重新闡釋,又帶有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的社會改良的特點。而孫中山以“天下為公”的精神創造的“三民主義”則帶有比大同社會更加理想的色彩,他想以財產均分、機會均等的原則來實現他的民主、民生和民權思想,從而還政于民,讓人民共同享受國家的財富,分享大家共同創造的勞動成果。由此可見,從孔子到孫中山,大同世界一直是中國幾千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奮斗的崇高目標。大同世界的理念既符合生態人文思想,又符合人際倫理原則;既符合社會大道,又符合人類的生存之道。它從根本上解決了生態社會中的一對基本矛盾: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說:“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解決了這對矛盾,其他的社會生態關系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二、“至德之世”:人與萬物相親共融的和諧情景再現
“至德之世”代表了中國道家的和諧生態社會理想。莊子提出的“至德之世”的社會背景是比較復雜的,但與儒家提出的“大同社會”大致一樣,都是在春秋戰國“禮崩樂壞”所導致的天下價值體系的混亂情形下,士人知識分子不得不努力尋求的救世方案。那時的人們普遍為物驅使、殉身名利。“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齊物論》)人在為物所役、為欲所累中遠離了生命的本真,陷入了荒誕的生存。由于對“此在”的絕望和孤獨,莊子便有了超越現實的向往和逍遙于塵世之外的愿望,從而追求生命的自由和詩意的生存方式。莊子提出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生態藍圖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的:“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馬蹄》)
這是一幅人與萬物共生共榮的和諧生態景象:在“至德之世”,人與禽獸生活在一起,彼此相安無事,互不傷害,其樂融融;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性情敦厚,無知無欲,性真德全,生活雖然十分簡單,但卻過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生活;那時的人民少私寡欲,按照自然的規律而動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從容自在,日子過得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快樂知足;那時的人類性靈淳樸,清靜無為,“鄰國相忘,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來往。”(《胠篋》)人與萬物和諧相處,各得其所,悠哉游哉。
莊子的“至德之世”是一個詩意充盈的原始時代。那時的人民淳真素樸,人與自然相親共融,與萬物和諧相處,生活輕松自在,無思無慮,樂在其中:“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山木》)
這是自然而詩意的國度,人民過著樸素的生活,悠然自得,無知無欲。大家只懂勞作而不收藏財產,慷慨助人而不求回報,粗狂豪放而不拘小節,活著的時候逍遙快樂,死了之后安然入葬。莊子認為,只有在原始時代的“至德之世”,人們離形去知,無欲無為,才能找回這種詩性智慧,才能回歸本源的生活。莊子以詩性智慧指出了人類生存的理想之境,那就是:人與萬物相親共融,與自然冥合為一,做到本然處世,詩意而居,逍遙于世,快意人生,從而實現生命的本真意義,獲得生存的快樂。
為此,莊子設計的“至德之世”的生態藍圖,首先要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歌德曾經說過:在中國,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2]。泰勒說得好:“當人還作為自然物生活在自然中的時候,他既無快樂也無痛苦,因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而當人走出自然,發現了自然的時候,快樂和痛苦便一起來了。而且人離開自然越遠,人的快樂和痛苦越激烈。因為離開了自然的人注定是孤獨的、寂寞的。人為了解脫這種痛苦,并獲得真正的快樂,就必須回返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3]大自然所具有的天然之美、造化之功,使人們越來越鐘情于山水林泉。莊子說:“山林與,皋垠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莊子·知北游》)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我與天地精神共來往的人生觀,啟迪著無數的士人返樸歸真,回歸自然,找回自我,追求自由詩意的生活方式。他們為了追求性靈之真,往往留連于山林皋壤之中尋找人生的樂趣。于是就有了陶淵明的“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本然覺醒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怡然自樂。所以,莊子所設計的“至德之世”始終都離不開人對自然的審美觀照,體現了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古風在《境界探微》一書中也說:“所以中國藝術家的興趣點和藝術表現的核心點,都在自然景物方面。他們將‘回歸自然’作為主要的藝術修養方式,在山水中澄凈靈魂,在花鳥中滋潤了文思,在風月中攬掬靈感。”[4]
“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馬蹄》)
在“至德之世”,人們任真自得,率性而為,行于其所當行,止于其所當止,一切都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時時像嬰兒那樣,餓了就吃撐肚皮兒,飽了就四處嬉戲游蕩,由此保全了人的純真性靈。這說明了,人一旦拆除自設的障蔽,擺脫外物對人性的摧殘,回歸本真的性情,便能逍遙于天地之間,無羈無絆,享受人生無窮的樂趣。
莊子所設計的“至德之世”,指向了人人稱頌的“堯舜之世”——那是一個民風淳樸、童叟無欺的時代。那時的人們:“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莊子·讓王》)
人與自然相親共融,不用奸、不使詐,通過自己的勞動豐衣足食,快樂地度過春夏秋冬,逍遙于天地之間而悠然自得,整天過著無拘無束的日子。那時: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馬蹄)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繕性》)
這體現了莊子“至德之世”的生態理想,即生態整體觀。按照莊子的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生態整體觀,人與萬物是相互平等的關系;人只是自然的一分子,他應該與自然萬物共生共榮,和諧發展,維護生態種群的完整性和平衡性,讓生態種群都能自由生長,共同創造萬物群生、欣欣向榮的和諧生態景象。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莊子·天地》)
至德之世,人人平等,君主賢明,民眾自由。人人性情敦厚,和睦相處;不尚賢使能,不用詐,無機心,無貪欲,知足常樂,無憂無慮,樂陶天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素樸而民性得矣。”(《馬蹄》)可見當時的社會是多么和諧。
但是,曾幾何時,隨著歷史的進化,暴力和殘殺代替了祥和柔德,瘋狂的掠奪使人類的生態家園慘遭破壞,“至德之世”已不復存在。在對遺失已久的生態家園的眷念和回顧中,莊子將“至德之世”置放于人類的“上古社會”,即“史前人類”時期,并加以詩意的描繪: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莊子·盜跖》)
在傳說中的伏羲、神農時代,人與自然萬物生活在一起。人們安然而居,適時而起,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整天和麋鹿生活在一起;他們自耕自足,日子過得逍遙自在,人皆沒有相害之心,這是人類道德極盛、生活過得極其安逸的“至德之世”。“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莊子·胠篋》)
傳說堯舜以前,中國曾有12個上古帝王,他們治下的時代正所謂圣人治下的“至德之世”,也稱“至治之世”。那時的人民毫無機心,一任自然;他們結繩記事,粗茶淡飯,但卻過著“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的生活,日子過得其樂融融;鄰國之間雞犬相聞,一派生機,但大家互不往來,也不侵害對方,彼此相安無事,共享天下太平。這是莊子按照傳說中上古社會的“原型”設計出來的理想生態社會,這樣的社會既符合人的自然天性,又符合宇宙大道。時至今日,當人們看到當下殘破不堪的“地球村”時,不由得懷念起上古時期淳樸清明的時代,懷念人類曾經擁有的和諧美好的生態家園。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遂,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烏鵲之巢可攀緣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莊子·馬蹄》
這是莊子對“至德之世”的詩意概括。在人類的道與德都完美無缺的至德之世,民德高尚,社會開放,人性自由,政治開明,無拘無束。自然界百草豐茂,樹木掩映,鳥獸遍野,它們都與人和諧相處并自由自在地生長。那時有山也不開辟道路,有河流也不架設橋梁,很好地保持了山川原有的生態風貌;人可以牽著禽獸四處游走,卻不受到傷害;人可以攀爬到樹上偷看鳥巢,而鳥卻不驚飛;人與萬物相親和諧,融洽無間;人人平等,沒有區別和對立;這是一個多么優美和諧的生態社會。這樣的“至德之世”是一種對遠古社會狀況的理想化模擬,是一種用高深的德性影響而形成的社會模式,它真實地表達了莊子對人類原有的恬靜美好的生態家園的深深眷念。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對莊子描繪的“至德之世”充滿了神奇的向往,因為這是人類可以“詩意棲居”的理想生態家園。
三、“世外桃源”:人人向往的人間生態樂園
生活于塵世中的人們,總想超越俗塵凡境,向往人間仙境,而這個仙境必定是一個山清水秀、景色優美、落英繽紛、幽谷飄香的地方。“仙境是一個可以慰藉靈魂、凈化心靈、超越現實苦難的夢幻世界,仙人則被賦予無窮的生命,他們飄忽天際,餐霞飲露,不必樵蘇于山,不必耕耘于野,既沒有情場之樂,也沒有宦海之險,他們不必爭利于市,也不必爭名于朝,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升天入海,在無窮無盡且閑散優雅的歲月中云游四方。”[5]可是在這世俗社會中,去哪兒尋找這樣的“化外之境”呢?東晉詩人陶淵明在《桃花源記并詩》中,以奇特的手法和詩意的筆墨,描繪了一個人人向往的人間仙境——“世外桃源”:那里遠離塵囂,奇隱幽閉,是武陵打魚人誤入桃花溪,忽逢桃花林,因迷戀于“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美景而流連忘返,結果偶入桃花源,進入了武陵的桃源仙洞。只見那里“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詩人給我們展現的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田園山水畫卷,是遠離了世俗紛擾的恬靜村落。那里的景色著實迷人,只見:青山隱隱,仙霧繚繞;花樹婆娑,流水潺潺;落英繽紛,宛若仙境;這里的人際關系極為融洽,人與自然親密無間,老人少兒皆怡然自樂,共享人間太平、無憂無慮的生活。“其中往來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髻,并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這里的人自耕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十分平靜簡樸的生活。這里民風淳樸,熱情好客,見到武陵打魚人,由“大驚”,到殷勤款待客人,為之殺雞、置酒,好飯好菜招待;此事一經傳開,村中的人紛紛趕來看望漁人并問寒問暖,氣氛熱鬧非凡,完全是一派淳樸未開的民情風俗的真實展現。“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既然偶遇桃花源,處處美景都留給武陵漁人深刻的印象,所以在離開之際,他到處留下標記,盼望以后再重返桃花源。但既然是“桃源仙境”,人間哪能再見?所以后來“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世外桃源,人間難覓,這本是意料中事,但這其中包含了作者對世俗人事多么深刻的反諷,同時也真切地表達了詩人對人類理想的生態家園的詩意向往。
這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究竟在哪里?臨別前桃源人的一句叮囑:“不足為外人道也”,這大大地增加了“桃源仙境”的神秘性。陶淵明在《桃花源詩》開篇寫道:“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亦復湮,來徑遂蕪廢。”由于秦皇、漢武這些所謂的“英雄豪杰”擾亂天下,破壞了自然的和諧,使得天下大亂。商山四皓隱姓埋名,社會賢者紛紛隱居深山。因為他們的隱居之處與世隔絕,遂成了奇隱幽閉之處。“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閉。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桃花源隱蔽于世500多年了,只因武陵人誤入桃花源,才讓它第一次向外界敞開其神仙般的境界。這里的社會風尚與世迥異,民風如此淳樸,人們過著神仙般的日子,怎忍心讓外界來玷污了這塊人間凈土?還是回復原來幽蔽狀態為好。請那些云游四方的好奇之士,不要再去尋找這片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了。其實,《桃花源記》對此已作詳細說明:“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絕。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呢?《桃花源詩》寫道:“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余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怡然有余樂,于何勞智慧?”這里的人們自耕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樂陶天然,無憂無慮,少兒老人隨意嬉戲,不用每天勞智傷神,卻有享有不盡的快樂。一直以來,桃源仙境都是世人向往的夢中樂土。據《晉書·隱逸傳》記載,劉子驥是晉代的隱逸仙人,《桃花源記》記述了他尋找“桃花源”的經過,卻始終未能找到。學者陳寅恪先生曾考證說“桃花源”在北方的弘農;后來有人說在武陵桃源縣(今湖南的常德);被當代人傳得沸沸揚揚的“世外桃源”是在廬山的康王谷,等等,不一而足。筆者以為,這種按圖索驥式的揣測臆想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陶氏的“世外桃源”是通過想象而創作出來的理想生態模式,它既是對抗黑暗現實的武器,也是陶淵明追求內心和諧的生態樂園,同時還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它上承儒家的“大同社會”理想,下接道家“小國寡民”的淳樸民風。在文化意義上,它成了黑暗濁世中人們回歸自然、返樸歸真,實現詩意生存的精神指歸。
平靜祥和的“世外桃源”引起了古往今來很多詩人的向往。東晉以后,無數的文人墨客競相歌詠桃花源。孟浩然的《游精思題觀主山房》:“誤入桃源里,初憐竹逕深。方知仙子宅,未有世人尋。舞鶴過閑砌,飛猿嘯密林。漸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孟浩然曾隱居于澗南圓的一座道觀,這里有若遠離人煙的桃花源,竹林桃花相互掩映,密林深處飛猿啼嘯,婷婷仙鶴飛舞于臺階之前,宛然是世人神往的“世外桃源”。包融的《桃源行》以“桃源”為題寫道:“武陵川徑入幽遐,中有雞犬秦人家,家傍流水多桃花。桃花兩邊種來久,流水一道何時有?垂條落蕊暗春風,夾岸芳菲至山口。歲歲年年能寂寥,林下青苔日為厚。時有仙鳥來銜花,曾無世人此攜手。可憐不知若為名,君任從此多所更。古驛荒橋平路盡,崩湍怪石小溪行,相見維舟登覽處,紅堤綠岸宛然成。多君此去從仙隱,令人晚節悔營營。”詩中所寫到的“桃花流水,暗香襲人,仙鳥銜花,紅堤綠岸”的優美景色,令人神往,抒發了詩人隱居仙境的愿望。盧照鄰的《過東山谷口》曰:“桃源迷處處,桂樹可淹留。跡異人間俗,禽同海上鷗。古苔依井被,新乳傍崖流。野老堪成鶴,山神或化鳩。泉鳴碧澗底,花落紫巖幽。日暮餐龜殼,開寒御鹿裘。不辨秦將漢,寧知春與秋。多謝青溪客,去去赤松游。”這首詩抒發的情感和上面幾首“桃源詩”是一致的。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美妙的“桃源仙境”,“桃花源里可耕田”就曾經表達了一個領袖的社會理想。中國士人在險惡的生存環境中,都自覺地把山水田園作為他們的快樂之源。是陶淵明的詩意創造,為他們提供了可以“詩意棲居”的安身立命之所,使他們從狹窄的生存空間轉向清新廣袤的田野山村,并投身于空靈曠遠的自然山水,從中獲得身心的解放,恢復性靈的自由。學者吳洪森說得好:“老莊哲學到了黑暗的晉代社會,通過陶淵明的再創造,使中國文化具有了源遠流長的田園精神。由于中國有了田園精神,使得中國統治者將天下讀書人全部網羅的野心永遠都只能是癡心妄想。可以說,田園精神兩千年來是中國文化人的宗教,是知識分子對抗黑暗現實的安身立命之所。”[6]由此可見,陶淵明創造的桃源文化對中國人的精神靈魂的重新鑄造和積極建構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作為一個詩人,陶淵明無力改變時局的混亂,但卻在詩文中創造了一個人類可以詩意棲居的理想生態家園。
四、三種理想社會形態之比較
從“大同社會”、“至德之世”到“世外桃源”的藍圖設計,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圣賢的生態理想和人文情懷。相比之下,我們發現它們之間有許多共同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三種社會形態的設計集中體現了中國智者思維的宏大設想,并為后人提供了為之奮斗的理想模式
“大同社會”的理想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提出的,它要建構一個和諧美好的人文生態社會。所以,儒家的生態美學思想就集中地體現在“大同社會”的建構中,它要恢復周朝禮儀和仁愛思想,建立一個人人平等、互敬互愛、社會太平、民胞物與的和諧生態世界。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治世”和“盛世”,都是以“大同社會”作為“藍本”去實踐和操作的。如“成康之時”,執政者效仿堯舜,移風易俗,勤政愛民,天下為公,致使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成為大同社會的雛形。晚清時的康有為按照大同社會的模形,在《大同書》中構想了一個至公、至平、至仁、至治的極樂世界——“大同社會”。它“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7]71,表達了人類的美好理想。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以儒家的“大同社會”的理想,提出了“天下為公”的思想。大同理想作為終極價值目標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社會理想和思想信仰,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治亂興衰的晴雨表。在自然生態社會的藍圖設計中,莊子的“至德之世”和陶淵明的“世外桃源”成為后人神往的理想生態模式。許多士人悠游林下,寄情山水,以“桃源仙境”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以“至德之世”作為理想的自然居所。象魏晉時代的阮籍、嵇康和包敬言等提出的“無君論”,嵇康就此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態理想;修仙隱逸之士葛洪提出了心目中的“自由樂土”是:“曼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山無溪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兼并,士眾不聚,則不相攻伐。”(《抱樸子·諳鮑篇》)當今人們按照“世外桃源”的原型設計和構建的風景名勝區——武陵桃花源風景區:那里風光旖旎,流水潺潺,還坐落著秦人時避難的“秦人村”,游人游覽至此,仿佛夢回1000多年前的武陵桃源洞,那里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處處皆宛若仙境;還有人人趨之若鶩的廬山“康王谷”……這一個個如神話般降落人間的仙境,正是按照先賢的詩意創造而設計出來的理想王國,經過人民世世代代的不斷努力,終究會有一天把夢想變成現實。
(二)從其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思想基礎來看,它們都是社會離亂后創造的理想產物
儒家的“大同社會”和道家的“至德之世”都是產生在禮崩樂壞、生靈涂炭的春秋時代。當時的儒、道、墨等各家都紛紛推出自己的救世方案。儒家以克己復禮為己任,企盼挽狂瀾于既倒,救萬民于水火,他們奔走呼號,游說諸侯采納自己的政治主張,從而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抱負。孔子從古代典籍中整理出合理的成分,構建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共同理想。道家則主張返樸歸真、回歸自然,恢復人類淳樸的本真和性靈,建立與自然萬物相親共融的和諧關系。為此莊子提出了“至德之世”的社會理想,為人們逃離苦難、重返自然提供了安然于居的生態家園。陶淵明處在異常動蕩的魏晉時代,當時統治者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達到了殘酷的程度。據史書記載:“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8]。繁重的徭役,逼得百姓“至有殘形剪發,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9],正可謂“民疲田蕪,事役頻苦,童耋奪養,老稚服戎”[10]。在此情況下,人民不堪忍受,紛紛逃離隱匿。為此,陶淵明創造了人人平等、安居樂業的桃源仙境——“世外桃源”,既為亂世中的人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避難所,又給后世開辟了一個既符合人性、又符合自然的生態家園。
(三)具有濃郁的烏托邦色彩
從《禮記·禮運》的“大同社會”、莊子的“至德之世”到陶淵明的“世外桃源”,都是古代圣賢設計出來的理想生態藍圖,這種生態文明形態,也許只有在遠古社會人類混沌未開的時代才有可能出現,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烏托邦是人類擺脫苦難現實、實現自我超越的理想途徑,是在嚴峻的社會現實中精神上無家可歸的浪子家園。烏托邦思想不僅是對未來的憧憬,而且是對現實的批判,同時也是對過去的反思,它是連接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必不可少的橋梁”[11]。由此可見,烏托邦理想帶有某種復古情緒,是對現實不可實現的最大超越和對未來理想的積極展望。
除了具有這些相同之處,它們之間也有相異之處。
(一)代表了各家的學說和思想中不同的社會理想和思想觀點
“大同社會”代表了儒家的思想觀點,它要表達的是人文生態理想,即建立一個人文生態倫理社會,從根本上解決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它致力于建構人人平等、處處祥和的太平盛世,最終實現儒家的救世理想。莊子的“至德之世”則代表了道家的思想觀點,他要建立的是自然生態社會,讓人們過著恬淡素樸的生活,達到“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陶淵明的“世外桃源”則綜合了老子的“小國寡民”、莊子的“至德之世”和孔子的“大同社會”,同時也夾雜著雜家的社會理想,成為各種社會形態中最理想的完美綜合體。它表達了陶淵明逃離濁世、享受幽寧的理想愿望,“桃源仙境”也由此而成為古往今來眾人追求的理想生存之境。
(二)表現的內容不盡相同
儒家的“大同社會”是非常符合現實社會的理想要求的。由于社會上唯才是舉,使得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各得其所,而且人人都講究誠信,睦鄰友好;“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為公,體現了民胞物與、泛愛萬物的博大精神,表達了原始的公平與正義的思想。“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體現了整個社會的尊老愛幼的良好風氣。由于人民的良好愿望和創造成果都獲得尊重,公平與正義都獲得充分的保障,自由與權力都獲得實現,所以這個社會充滿了生機與活力,人們對未來充滿了期待,人與人之間都講誠信友愛,互相尊重,和諧相處,相互幫助,迎來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盛世。這就是人人向往和追求的大同理想,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幸福安康,安居樂業,社會秩序井然有序,大家各安其分,各守其業,融洽無間,體現了古代生態文明社會的理想模式。莊子的“至德之世”則體現了道家的生態美學思想,“道法自然”是其思想核心。在道德健全的時代,人心淳樸,詩性圓滿,“其生可樂,其死可藏”(《山木》)。人與自然生死相依。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讓王》),日子過得樂陶天然。莊子要求人們回歸自然,返樸歸真,否定非本真的生存方式,用生態審美的方式來領悟自然的和諧之美,感受詩意人生的祥和快樂。“故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圣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知北游》)道家的“無為”思想并不是要求人們無所作為,消極對待,而是要求人們不要人為地去破壞自然,造成人與自然的對立,破壞萬物和諧的關系。“與人和者,謂之人籟;與地和者,謂之地籟;與天和者,謂之天籟。”(《齊物論》)這正是道家以詩意的筆墨勾畫出來的生態審美思想和“與天同樂”的生態和諧境界。陶淵明的“世外桃源”則高度融和了儒道兩家的社會理想,又加入了自己個人的獨特創造和想象,代表了古往今來的生態審美理想的最高理想和最完美的形式,所以獲得了越來越多人的共同青睞。
盡管如此,這三種理想的生態社會形態在價值指歸上是一致的,它們都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審美思想,它要處理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相互關系,而且要最終建構“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觀念。它們都是中華民族生存智慧的高度概括和總結。同時,它們都將為今后建構和諧美好的生態社會提供理論支撐和智力支持,更為將來共同開創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人與萬物相親共融的良好局面提供極其富有價值意義的深刻啟示。
[1] 康有為.大同書[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 德·愛克曼.歌德談話錄[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112.
[3] 閻國忠.人與自然的統一[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2001(3).
[4] 古風.意境探微[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266.
[5] 劉潔.唐詩題材類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333.
[6] 吳洪森.面對摩羅的困惑[M]//摩羅.不死的火焰·序.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
[7] 康有為.大同書[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8] 晉書·劉毅傳·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92.
[9] 晉書·范寧傳·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76.
[10] 宋書·武帝紀·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33.
[11] 張叉.中外文學中的理想社會—論陶淵明和華茲華斯的生態文明建構[J].當代文壇,2006(6).
Poetic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homeland——A Blueprint from the“DatongSociety”,“FullyMoralWorld”to the“Arcadia”
Song Jia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Qinzhou University,Qinzhou 535000,China)
Poetic construction ofa harmonious eco-homeland isa presentation of ideal social pattern of China.“Datong Society”reflects the Confucian ideal of eco-society of green and humanity while“Fully MoralWorld”represents the Taoist ideal of harmonious eco-society.“Arcadia”,on the other hand,blends Confucian notion of equality in a“Datong Society”with Taoist simplicity of folk customs in a“Small Country and Population”,whichmakes a fascinating paradise as amazing as a fairyland.All the three social patterns contain the wisdom of ancient thinker and are rich in Utopian flavors,because of which they imply a transcendental nature.Although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forms,their value orientations are the same,with some ecological and aesthetical ideas beneath them.
social idea;Confucianism;“Datong Society”;Zhuang-zi;“Fully MoralWorld”;Tao Yuanming
C912
A
1673-8535(2012)04-0075-08
宋堅(1963-),男,廣西欽州人,欽州學院中文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生態文藝與詩學理論。
(責任編輯:高堅)
2012-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