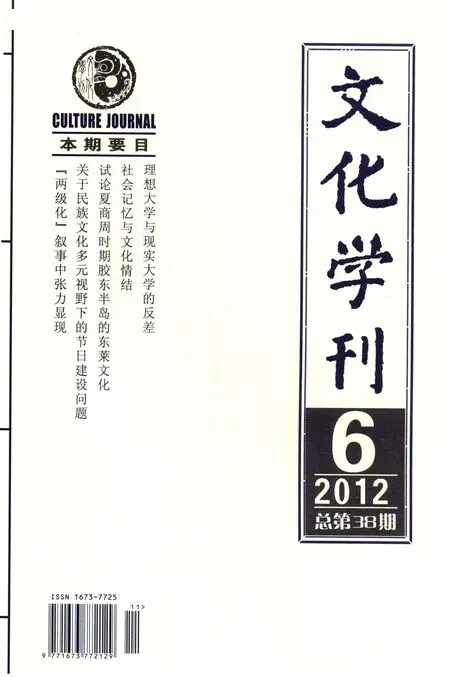中外迷文化研究比較分析
劉乃仲 張飛宇
(大連理工大學(xué)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遼寧 大連 116000)
一、引言
“迷”是英文“fans”的中文釋義,國(guó)內(nèi)也有學(xué)者將其翻譯成“粉絲”。迷文化研究最初興起于20世紀(jì)90年代的英美學(xué)界,形成了一個(gè)新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并在大眾文化、媒介文化和社會(huì)學(xué)等領(lǐng)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中國(guó)的迷文化悄然興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了我國(guó)文化產(chǎn)業(yè)、媒介工業(yè)、娛樂(lè)經(jīng)濟(jì)等各項(xiàng)事業(yè)的繁榮,所以,無(wú)論是業(yè)界還是學(xué)界都應(yīng)該對(duì)迷文化有正確的認(rèn)識(shí)和深入的研究,這其中的理論價(jià)值和現(xiàn)實(shí)意義不言而喻,而當(dāng)前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迷文化的研究還在發(fā)展初期,研究領(lǐng)域和視角涵蓋雖廣,但是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關(guān)照和分析,缺少系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研究。
西方迷文化研究經(jīng)歷幾十年的發(fā)展已經(jīng)成熟,對(duì)我國(guó)有借鑒意義。本文通過(guò)對(duì)中外迷文化研究在研究領(lǐng)域、研究?jī)?nèi)容、研究方法、學(xué)者態(tài)度、發(fā)展程度等方面的比較,意在發(fā)現(xiàn)我國(guó)在迷文化研究中的缺失與不足,從而促進(jìn)研究得以深入發(fā)展。
二、樣本選取與梳理
(一)樣本選取
陶東風(fēng)主編的《粉絲文化讀本》一書(shū)精選翻譯了國(guó)外迷文化研究經(jīng)典的代表性著作,是國(guó)內(nèi)迷文化研究領(lǐng)域比較全面的引入西方成果的著述,本文參考其中共23篇文章和選段,結(jié)合SSCI中以“fan cultrue”為關(guān)鍵詞搜索出的百余篇學(xué)術(shù)論文,總結(jié)出國(guó)外迷文化研究的主要領(lǐng)域、內(nèi)容及研究方法。
同時(shí),在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期刊網(wǎng)絡(luò)出版總庫(kù)以“粉絲文化”、“迷文化”等為關(guān)鍵詞搜索,搜索出有關(guān)迷和迷文化研究的論文總計(jì)50篇,在中國(guó)優(yōu)秀博碩士學(xué)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中,搜索出博士學(xué)位論文2篇,碩士學(xué)位論文18篇,大致梳理并總結(jié)出中國(guó)迷文化研究的現(xiàn)狀,并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比國(guó)外迷文化研究,提出中國(guó)迷和迷文化研究存在的問(wèn)題以及由此帶來(lái)的啟示。
(二)樣本梳理
通過(guò)分析所收集的資料,梳理出國(guó)內(nèi)外迷文化研究領(lǐng)域及研究?jī)?nèi)容如下。
理論基礎(chǔ)研究。米歇爾·德賽都的日常生活實(shí)踐理論,將積極的受眾閱讀視作文化拼貼,在拼貼過(guò)程中,受眾先將文本分解后重新組合,從中找出理解自己生活經(jīng)驗(yàn)的部分;詹金斯用德賽都的理論,將迷定義為通俗文化的“盜獵者”與“游牧民”,他們通過(guò)挪用文本形成一種參與性文化;約翰·費(fèi)斯克認(rèn)為,迷文化就是工業(yè)化社會(huì)中大眾文化的一種強(qiáng)化形式,迷是一些“過(guò)度的讀者”。
國(guó)內(nèi)的理論研究主要是對(duì)西方迷研究理論基礎(chǔ)上的中國(guó)本土化研究。如:董雪飛的《日常生活實(shí)踐與大眾文化的政治:約翰·費(fèi)斯克大眾文化理論的啟迪與反思》;楊玲的《西方消費(fèi)理論視野中的粉絲文化研究》;鄧惟佳的 《試析西方迷文化研究的三次浪潮和新的發(fā)展方向》等等。
受眾研究。威爾·布魯克對(duì)《星球大戰(zhàn)》迷進(jìn)行了研究,他從一個(gè)“兼具迷身份的學(xué)者”的角度,提出了迷社群衰落的可能性,由于沒(méi)有新的主文本的出現(xiàn),這個(gè)特定的迷群最后可能只會(huì)剩下一些骨灰級(jí)的鐵桿,因懷舊而繼續(xù)做迷,這是研究者中鮮有人提及的話(huà)題。
劉麗榮的碩士學(xué)位論文 《粉絲受眾研究》,將粉絲作為特殊受眾,提出了粉絲群體存在的缺陷以及改進(jìn)的措施;國(guó)內(nèi)受眾研究領(lǐng)域如胡瑛的 《媒介重度使用者粉絲的受眾特性分析》分析了粉絲狂歡背后的動(dòng)力,打破了粉絲受眾主動(dòng)與被動(dòng)二元對(duì)立的思維空間,超越了簡(jiǎn)單的主動(dòng)性與被動(dòng)性研究。
媒介研究。詹金斯在《昆汀·塔倫蒂諾的星球大戰(zhàn)》一文中對(duì)《星球大戰(zhàn)》迷所創(chuàng)作的迷電影進(jìn)行了實(shí)證分析與理論探討,并將其看做是當(dāng)代媒介革命的先導(dǎo)。提出“迷是所有新媒介技術(shù)的最早使用者和推廣者之一”。
消費(fèi)研究。將迷看作是與媒介生產(chǎn)者相對(duì)應(yīng)的媒介文本的消費(fèi)者。詹金斯指出迷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yàn)?“他們構(gòu)成了消費(fèi)者中特別活躍和善于表現(xiàn)的一個(gè)社群”。費(fèi)斯克在他的 《粉都的文化經(jīng)濟(jì)》中提出迷能夠創(chuàng)造“自己的生產(chǎn)和流通體系”,形成一種類(lèi)似于主流文化經(jīng)濟(jì)的“影子文化經(jīng)濟(jì)”。
中國(guó)的學(xué)者在消費(fèi)研究領(lǐng)域?qū)γ缘年P(guān)注大多是表面的分析和介紹,缺少全面深入的具體研究。郁青的《粉絲文化對(duì)娛樂(lè)明星消費(fèi)市場(chǎng)的影響研究》總結(jié)了粉絲文化對(duì)娛樂(lè)明星消費(fèi)和經(jīng)營(yíng)所帶來(lái)的新模式和新趨勢(shì),認(rèn)為粉絲文化推動(dòng)了明星制的廣泛運(yùn)用,并且產(chǎn)生了新的消費(fèi)市場(chǎng)——娛樂(lè)明星周邊市場(chǎng),還促使“粉絲”提高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意識(shí),促進(jìn)了娛樂(lè)明星消費(fèi)市場(chǎng)和文化產(chǎn)業(yè)的快速發(fā)展。
社會(huì)學(xué)研究。蓋利·P.T.芬與理查德·吉利亞諾蒂的 《是蘇格蘭球迷,不是英格蘭混混——蘇格蘭人、蘇格蘭性和蘇格蘭足球》運(yùn)用實(shí)證研究與理論分析相結(jié)合的方法,探討了足球運(yùn)動(dòng)、球迷與民族身份之間的關(guān)系。認(rèn)為雖然足球運(yùn)動(dòng)承擔(dān)了表達(dá)蘇格蘭身份的重任,一個(gè)依靠與英格蘭的二元對(duì)立而建構(gòu)起來(lái)的蘇格蘭身份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現(xiàn)。一個(gè)更積極的、更具包容性的蘇格蘭身份有待建立。[1]
馬竹音 《粉絲消費(fèi)行為的社會(huì)學(xué)分析》中,以百度貼吧迷群體的消費(fèi)行為作為個(gè)案,將其置于社會(huì)學(xué)的大背景中,認(rèn)為粉絲消費(fèi)并非是過(guò)度的、非理性的,而是有節(jié)制的,粉絲對(duì)于偶像文本的符號(hào)性消費(fèi)使其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受眾”,他們有了主動(dòng)消費(fèi)的意識(shí)和能力,也有了更多的社會(huì)意義。
傳播學(xué)研究。聶晶磊和王秋艷的《從大眾傳播視角談一種文化現(xiàn)象》探討了粉絲文化的成因及粉絲的行為特點(diǎn),并運(yùn)用大眾傳播學(xué)的議程設(shè)置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使用與滿(mǎn)足理論、二級(jí)傳播理論對(duì)粉絲行為進(jìn)行分析,認(rèn)為大眾傳播促進(jìn)粉絲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
心理學(xué)研究。國(guó)外學(xué)者運(yùn)用三種精神分析學(xué)理論分析迷的心理和行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論、克萊因的內(nèi)攝與投射理論、溫尼科特的過(guò)渡性客體理論。
女性主義研究。萊儂·白利的《她們自己的賽博空間:網(wǎng)絡(luò)女性粉都》一書(shū)用民族志的方法描述了迷群中的女性對(duì)網(wǎng)絡(luò)空間的使用方式,借用哈貝馬斯和多位女性主義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個(gè)性別與社會(huì)空間的西方譜系。[2]
從比較中可以看出,國(guó)外迷文化研究涉及領(lǐng)域眾多,這也是迷文化研究跨學(xué)科性質(zhì)的印證。從研究方法上看,早期迷文化研究以思辨性的理論分析為主,但隨著迷文化研究的深入,學(xué)者們多采用個(gè)案分析的實(shí)證研究方法結(jié)合理論分析。民族志研究也是學(xué)者們較多使用的方法。
此外,很多學(xué)者在做研究時(shí)自己本人就是所研究對(duì)象迷群中的一員,即所謂“兼具迷身份的學(xué)者”。比如詹金斯本人是著名科幻電視連續(xù)劇《星際迷航》的鐵桿迷,所以他是以這樣一個(gè)“兼具迷身份的學(xué)者”的雙重身份進(jìn)入他的研究的,并且以參與者的方式進(jìn)入這個(gè)群體中進(jìn)行觀察。像這樣具有雙重身份的研究者還有很多,他們是學(xué)者同時(shí)又是迷,對(duì)迷文化有很深的了解,更易進(jìn)入迷群內(nèi)部深入研究。
三、比較分析
縱觀國(guó)內(nèi)外迷文化研究現(xiàn)狀,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在研究領(lǐng)域、內(nèi)容、方法、學(xué)者態(tài)度以及發(fā)展階段等方面都存在諸多不同之處,從中也能看出我國(guó)迷文化研究的問(wèn)題和不足。
從研究領(lǐng)域上看,國(guó)內(nèi)外研究學(xué)者都從理論基礎(chǔ)、受眾研究、消費(fèi)研究和社會(huì)學(xué)研究方面對(duì)迷文化展開(kāi)探討,其中理論研究方面我國(guó)的研究是在西方理論基礎(chǔ)上所做的中國(guó)本土化研究;在傳播學(xué)研究領(lǐng)域我國(guó)學(xué)者運(yùn)用傳播學(xué)理論對(duì)迷文化現(xiàn)象進(jìn)行了闡釋?zhuān)鴩?guó)外并沒(méi)有相關(guān)研究成果;對(duì)于國(guó)外學(xué)者研究較多的女性主義視角、心理學(xué)中的精神分析視角以及媒介研究領(lǐng)域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幾乎從未涉獵;此外,對(duì)于迷和迷文化現(xiàn)象的闡釋性研究也得到了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廣泛關(guān)注。
從研究?jī)?nèi)容上看,國(guó)外迷和迷文化研究不僅突出了迷實(shí)踐行為的能動(dòng)性,而且研究了迷的實(shí)踐行為如何反映社會(huì)資本、文化資本和經(jīng)濟(jì)資本及在此基礎(chǔ)上研究迷的動(dòng)機(jī)問(wèn)題;我國(guó)的迷和迷文化研究雖然數(shù)量眾多,也不乏站在客觀角度審視迷現(xiàn)象的研究成果,但是停留在表層的研究并沒(méi)有觸及迷和迷文化的核心和本質(zhì),僅僅針對(duì)迷和迷群體本身的研究也無(wú)法發(fā)現(xiàn)其背后深層的社會(huì)根源。
從研究方法上看,國(guó)外學(xué)者在進(jìn)行迷和迷文化研究時(shí)采用的研究方法頗多,如民族志、理論分析、田野調(diào)查、個(gè)案研究等,同時(shí)國(guó)外學(xué)者很多人本身也是迷群體中的一份子,甚至是鐵桿粉絲;中國(guó)研究者們多運(yùn)用理論分析方法,新近的研究個(gè)別采用個(gè)案研究的方法,其中也有部分研究者借鑒國(guó)外經(jīng)驗(yàn),以一個(gè)“兼具迷身份的學(xué)者”的身份進(jìn)行觀察研究,如鄧惟佳的博士學(xué)位論文《能動(dòng)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作者作為美劇迷的一員深入迷群體內(nèi)部獲得第一手資料,對(duì)國(guó)內(nèi)迷研究領(lǐng)域來(lái)說(shuō)是一次有益的嘗試。
從學(xué)者對(duì)迷所持態(tài)度上看,國(guó)外學(xué)者對(duì)于迷和迷文化的態(tài)度客觀中立,雖然早期出現(xiàn)過(guò)偏激的理論,但經(jīng)過(guò)幾十年的發(fā)展,在完整的研究框架和研究理論下,學(xué)界都能客觀看待迷和迷文化現(xiàn)象;在中國(guó),情形并不如此,學(xué)者們?cè)诿τ诮?gòu)迷文化研究理論框架時(shí),將迷群體置于一個(gè)“他者”的位置,雖然像研究初期所出現(xiàn)的明顯偏激觀點(diǎn)已經(jīng)并不多見(jiàn),但是在字里行間卻表現(xiàn)出精英知識(shí)分子在面對(duì)迷群體時(shí)的智力優(yōu)越感,尤其是2007年被媒體炒的沸沸揚(yáng)揚(yáng)的楊麗娟事件以后,迷和迷群體更是被學(xué)者和大眾貼上了瘋狂、偏執(zhí)、非理性等道德批判的標(biāo)簽,這些刻板成見(jiàn)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xué)者對(duì)迷和迷群體客觀真實(shí)的評(píng)價(jià)。
從發(fā)展程度上看,國(guó)外迷文化研究經(jīng)歷了三次發(fā)展浪潮,如今已經(jīng)進(jìn)入成熟期;中國(guó)的迷和迷文化研究才剛剛起步,還處于摸索前進(jìn)階段。從所查文獻(xiàn)中可以看出,國(guó)內(nèi)研究最多的還是對(duì)迷現(xiàn)象的闡釋。
四、總結(jié)與啟示
基于對(duì)中外迷文化研究的比較分析,得出以下結(jié)論:
我國(guó)迷文化研究應(yīng)涉及媒介研究、女性主義研究和精神分析視角的研究。媒介技術(shù)尤其是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發(fā)展促使迷群體的發(fā)展壯大,同時(shí)迷和迷群體的文化實(shí)踐活動(dòng)又會(huì)促進(jìn)文化產(chǎn)業(yè)、媒介工業(yè)以及娛樂(lè)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迷與媒介、迷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成為一個(gè)重要關(guān)注領(lǐng)域。女性占迷群體中的大部分,國(guó)內(nèi)學(xué)者應(yīng)該多關(guān)注女性視角的迷研究。此外筆者認(rèn)為,有關(guān)迷和迷群消費(fèi)的研究應(yīng)該是迷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gè)領(lǐng)域,消費(fèi)活動(dòng)才是迷實(shí)踐活動(dòng)的本質(zhì),迷群體的消費(fèi)特性才應(yīng)該是迷和迷文化研究的根本。
迷文化研究應(yīng)該聯(lián)系中國(guó)國(guó)情,探索中國(guó)迷文化發(fā)展的深層原因。我們?cè)诮梃b國(guó)外研究成果的同時(shí),更應(yīng)該將中國(guó)迷文化發(fā)展置于中國(guó)當(dāng)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的大背景下進(jìn)行研究。社會(huì)學(xué)者朱力認(rèn)為:中國(guó)從計(jì)劃經(jīng)濟(jì)到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社會(huì)控制機(jī)制的轉(zhuǎn)型,導(dǎo)致了中國(guó)社會(huì)在社會(huì)組織、社會(huì)流動(dòng)、信息傳遞和核心價(jià)值等方面一系列劇變,微觀上表現(xiàn)為社會(huì)成員的行為與規(guī)范發(fā)生沖突,造成意識(shí)形態(tài)的真空、價(jià)值觀念的迷亂。[3]而迷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是否可以看做是中國(guó)民間對(duì)這種 “真空”和“迷亂”的回應(yīng)與自救?
迷文化研究應(yīng)采用深入實(shí)際的調(diào)查研究方法。單純的理論分析和思辨性探討不能建立迷文化研究框架,要想真正對(duì)迷文化有深入的認(rèn)識(shí),須深入迷群內(nèi)部對(duì)迷群體及個(gè)體進(jìn)行具體研究。同時(shí),研究者是否是“兼具迷身份的學(xué)者”,是否對(duì)迷文化有深度的卷入對(duì)研究成果有著深刻的影響。
對(duì)迷和迷群體少一些批判,多一些冷靜思考;少一些利用,多一些引導(dǎo)。對(duì)于迷研究學(xué)者來(lái)說(shuō),一味地批判、否定不是真正的科學(xué)研究,對(duì)于我國(guó)迷文化發(fā)展來(lái)說(shuō),冷靜的思考和客觀的評(píng)價(jià)才是當(dāng)前研究者應(yīng)該有的研究態(tài)度。對(duì)于媒體來(lái)說(shuō),迷和迷群體不應(yīng)該被當(dāng)做獲得經(jīng)濟(jì)利益的炒作對(duì)象。處于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的中國(guó),媒體承擔(dān)著道德塑造與規(guī)范的作用,具有社會(huì)倫理道德培養(yǎng)的功能,媒體切不可為了追逐經(jīng)濟(jì)利益而喪失媒體的良心。
隨著傳播科技的飛速發(fā)展,中國(guó)的迷文化越來(lái)越蓬勃,而中國(guó)的迷文化研究也即將迎來(lái)新的浪潮。由于西方娛樂(lè)產(chǎn)業(yè)興起較早,所以其迷文化研究起步也比較早,對(duì)比來(lái)看中國(guó)的迷文化研究就存在諸多問(wèn)題和不足,這是我國(guó)迷文化發(fā)展的必經(jīng)之路。當(dāng)前在我國(guó)新媒體領(lǐng)域,“粉絲”已經(jīng)成了企業(yè)的搖錢(qián)樹(shù),甚至超越經(jīng)濟(jì),成了社會(huì)輿情的觀察點(diǎn),這個(gè)舶來(lái)品在中國(guó)以讓人瞠目的方式風(fēng)行,其沖擊力不可小覷,而學(xué)術(shù)界也必將掀起迷文化研究的風(fēng)潮。
[1][2]陶東風(fēng).粉絲文化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275.429.
[3]朱力.變遷之痛:轉(zhuǎn)型期的社會(huì)失范研究[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6.29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