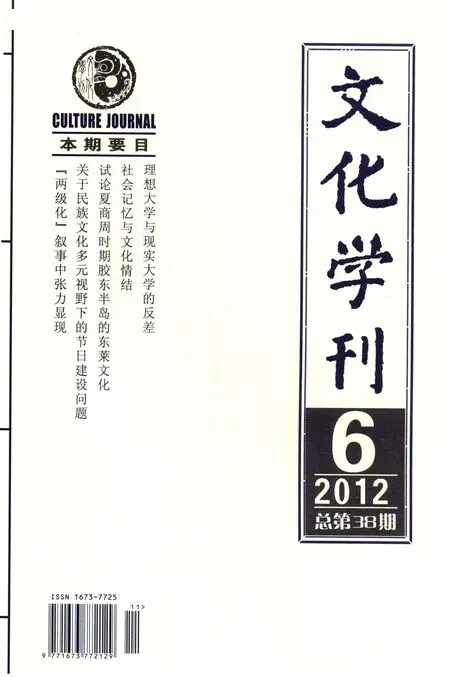關(guān)于《新青年》編撰的幾個(gè)史料問題——也談主撰的 “引領(lǐng)”兼與張寶明教授商榷
王玉春
(大連理工大學(xué)人文與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部,遼寧 大連 116024)
《新青年》作為“民初乃至整個(gè)20世紀(jì)中國影響最大的思想文化雜志”,它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思想史乃至新聞傳播史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近年來學(xué)術(shù)界也從文學(xué)史、思想史、傳播史等不同視角對(duì)《新青年》雜志做了大量的充分的研究。其中張寶明教授的《“主撰”對(duì)<新青年>文化方向的引領(lǐng)》(以下稱《引領(lǐng)》)一文,通過大量的史料與分析詳細(xì)地闡明了作為主撰的陳獨(dú)秀在《新青年》的創(chuàng)刊、轉(zhuǎn)折與發(fā)展的精神歷程中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杠桿作用,可謂是目前學(xué)術(shù)界從編輯社會(huì)學(xué)角度對(duì) 《新青年》研究的重要學(xué)術(shù)成果。不過,該文在具體論述過程中有幾處提法與事實(shí)有所出入,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作者對(duì)《新青年》編撰問題的相關(guān)看法與判斷。因關(guān)乎到“五四”文學(xué)史與文化史的史實(shí)問題,特此指出并談幾點(diǎn)粗淺的看法,敬請(qǐng)張教授以及各位專家批評(píng)指正。
一、《新青年》的編輯思路
《引領(lǐng)》一文在論述陳獨(dú)秀對(duì)刊物的“引領(lǐng)”時(shí)認(rèn)為:在《新青年》“由一人主撰到輪流編輯、由個(gè)人領(lǐng)唱到多重唱、由一人導(dǎo)航到齊頭并進(jìn)的短暫過程中”,在“諸如思想爭(zhēng)鳴、文化選擇、貞節(jié)問題等等討論都可以讓輪流主持者各領(lǐng)風(fēng)騷、獨(dú)占鰲頭”的“放”得最開的時(shí)段,陳獨(dú)秀“對(duì)其情有獨(dú)鐘的定位卻一刻也沒有讓步過、退縮過”。為證明這一觀點(diǎn),作者在下文寫道:
割舍不斷的政治情懷既使陳獨(dú)秀一直保持著與時(shí)俱進(jìn)的鮮明特征,也同時(shí)埋下了群體分裂的隱憂。在《新青年》作者讀者兩不旺的“青年”期,他為了拉住主力胡適,不僅在創(chuàng)刊號(hào)上以“批評(píng)時(shí)政,非其旨也”相標(biāo)榜,更是“爽快”地答應(yīng)了“二十年不談?wù)巍钡募s定。然而,待到《新青年》雜志門庭若市,主撰站穩(wěn)了腳跟時(shí),他便試水似地開始了 《國內(nèi)大事記》、《國外大事記》等具有敏感政治色彩欄目的嘗試、開設(shè)。1918年7月陳獨(dú)秀發(fā)表的《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即是主編食言的信號(hào),而11月15日“關(guān)于歐戰(zhàn)的演說三篇”的專欄則更是主撰言不由衷的暴露。
這段文字描述存在以下幾點(diǎn)歧義:
第一,作者認(rèn)為陳獨(dú)秀“為了拉住主力胡適”而“在創(chuàng)刊號(hào)上以‘批評(píng)時(shí)政,非其旨也’相標(biāo)榜”,這無疑是不符合歷史事實(shí)的。1915年9月15日,陳獨(dú)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時(shí),胡適尚在美國留學(xué),兩人之間還互不相通。同年10月6日,作為老鄉(xiāng)的汪孟鄒將《青年雜志》的創(chuàng)刊號(hào)寄給在美國的胡適,并附信介紹陳獨(dú)秀和雜志的情況以及對(duì)其約稿:“今日郵呈群益出版青年雜志一冊(cè),乃煉友人皖城陳獨(dú)秀君主撰,與秋桐亦是深交,曾為文載于《甲寅》者也。擬請(qǐng)吾兄于校課之暇,擔(dān)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wù)希拔冗為之,是所感幸。”《引領(lǐng)》一文也承認(rèn)“從這封信的內(nèi)容看,此時(shí)的陳獨(dú)秀與胡適還不曾直接通信,甚至沒有接觸。”實(shí)際上,陳胡二人于1916年始有書信交往,直至胡適的 “八事”、《文學(xué)改良芻議》在《新青年》的第2卷先后發(fā)表,方才引起巨大反響。兩人之間可以說是互相成就了彼此,因此,說陳獨(dú)秀發(fā)表在創(chuàng)刊號(hào)的文字是為了“拉住主力胡適”,顯然是不符合實(shí)際情況的。
第二,該文寫道“待到《新青年》雜志門庭若市,主撰站穩(wěn)了腳跟時(shí),他便試水似地開始了《國內(nèi)大事記》、《國外大事記》等具有敏感政治色彩欄目的嘗試、開設(shè)”。這里出現(xiàn)了明顯的史料錯(cuò)誤,因?yàn)椤秶鴥?nèi)大事記》和《國外大事記》這兩個(gè)欄目是自《新青年》創(chuàng)刊起就有的。兩欄刊載的文章數(shù)目情況詳見下表:
因此,這兩個(gè)欄目并非是待到雜志“門庭若市”、主撰“站穩(wěn)了腳跟”才“開設(shè)”的。恰恰相反,這兩欄是直到第4卷時(shí)才被“取消”的。更確切地說,應(yīng)該是被“轉(zhuǎn)移”了,因?yàn)榫驮谶@一年底陳獨(dú)秀創(chuàng)辦了《每周評(píng)論》,而《國內(nèi)大事記》和《國外大事記》則是該刊固定的兩個(gè)專欄。更有意味的是,第4卷正是《新青年》開始實(shí)行集體輪流編輯的時(shí)候,對(duì)“具有敏感政治色彩”的欄目的調(diào)整,恰恰從一個(gè)側(cè)面說明了同人群體合力對(duì)雜志編輯思路的影響與調(diào)整。

?
第三,該文寫到“1918年7月陳獨(dú)秀發(fā)表的《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即是主編食言的信號(hào)”。按照這種說法,所謂的“主編食言的信號(hào)”,其實(shí)早在1917年7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5號(hào),陳獨(dú)秀在回答讀者來信時(shí)便已發(fā)出。面對(duì)讀者顧克剛責(zé)問雜志為什么談?wù)螁栴}時(shí),陳獨(dú)秀頗為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評(píng)時(shí)政,青年修養(yǎng),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guān)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其后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一文中他又再次強(qiáng)調(diào):“政治問題,往往關(guān)于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應(yīng)該裝聾作啞呢?”更何況,“我現(xiàn)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guān)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yuǎn)紛擾,國亡種滅而后已!國人其速醒!”雖然創(chuàng)刊號(hào)上陳獨(dú)秀在回答讀者來信時(shí)表示“批評(píng)時(shí)政,非其旨也”,重申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dǎo)青年之修養(yǎng)”為目的刊物定位。但隨著時(shí)局的變化,特別是1919年以后歐戰(zhàn)結(jié)束、巴黎和會(huì)召開以及由此催生出的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這一連串事件的發(fā)生,身為國人又豈能置身事外。正如陳獨(dú)秀所說“在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談?wù)我擦T,不談也罷,誰都逃離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跡絕對(duì)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huì)尋著你的。”之后的胡適也有過類似的表達(dá):“以前我們是不談?wù)蔚模Y(jié)果政治逼人來談”。主撰對(duì)刊物編輯思路變化所作的解釋,正說明了主撰的編輯思路并非是從一開始就設(shè)計(jì)好的,而是隨著時(shí)事的變化“在運(yùn)動(dòng)中逐漸成型”的。因此,將主撰對(duì)辦刊思路的探索過程簡(jiǎn)化為“一刻也沒有讓步過、退縮過”的引領(lǐng),顯然是不準(zhǔn)確的。
二、《新青年》的編輯過程
《引領(lǐng)》一文雖然在篇首提及《新青年》同人共同唱和的實(shí)績(jī),但是,其整篇的論述卻過于強(qiáng)調(diào)主撰個(gè)人引領(lǐng)的作用,而低估了同人群體的“共同唱和”。在具體論述中,諸如“‘欲摘故縱’、‘先放后收’的辦刊套路”、“嚴(yán)防死守,把關(guān)嚴(yán)厲”、“不占優(yōu)勢(shì)誓不罷休”、“多少帶有‘指點(diǎn)江山’的頤指氣使味道”……之類的語句比比皆是,連“讀者論壇”也成了“陳獨(dú)秀為自己坐穩(wěn)主撰位置而精心設(shè)置的一個(gè)暗哨”,不免予人以主撰一人獨(dú)斷之感。
陳獨(dú)秀任意敢為的性格的確容易造成霸道的印象,加之其“必不容反對(duì)者有討論的余地”的激烈言辭更是歷來為人所詬病,這也使得不少研究者容易被“語言”所遮蔽而草率得出結(jié)論。有學(xué)者認(rèn)為,以陳獨(dú)秀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之所以有這樣的言論態(tài)度,一是因?yàn)檫@些人物的思想中都含有“尼采層”;二是為了通過激烈的言辭以破除舊說;三是由于當(dāng)時(shí)國家“烈火焚居,及于眉睫”的危亡處境而“急不擇言”。①此觀點(diǎn)可參見賴光臨在《中國近代報(bào)人與報(bào)業(yè)》中的詳細(xì)論述。賴光臨.《中國近代報(bào)人與報(bào)業(yè)》[M].臺(tái)灣:臺(tái)灣商務(wù)印書館,1987.陳平原先生就將這種作風(fēng)概括為“學(xué)問家與輿論家”的“相得益彰”。對(duì)此胡適在后來的回憶中也不得不承認(rèn)“當(dāng)時(shí)若沒有陳獨(dú)秀‘必不容反對(duì)者有討論之余地’的精神,文學(xué)革命的運(yùn)動(dòng)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可見,這些激烈的言辭作為特定歷史時(shí)期的產(chǎn)物,已經(jīng)深深地打上了時(shí)代的烙印,對(duì)此研究者不能光聽其如何“說”,更要看其如何“做”,否則很容易產(chǎn)生誤讀。
事實(shí)上,作為主撰的陳獨(dú)秀之所以能引領(lǐng)著《新青年》使之成為“民初乃至整個(gè)20世紀(jì)中國影響最大的思想文化雜志”(陳平原語),恰恰得益于其在“硬性”(剛性)的牽動(dòng)和“軟性”(柔性)的包容之間存在著一個(gè)“伸縮自如的緩沖地帶”。其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第一,打破省界意識(shí)的作者群體。強(qiáng)大的作者隊(duì)伍是辦刊成功的重要因素。《新青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批第一流知識(shí)精英的精誠合作。在吸納人才方面,陳獨(dú)秀前期利用《甲寅》的作者群,后期又發(fā)揮北大學(xué)府的人才優(yōu)勢(shì),充分彰顯了“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民主辦刊風(fēng)格;第二,輪流編輯實(shí)現(xiàn)互補(bǔ)。從1918年開始,《新青年》編輯部改組,由陳獨(dú)秀個(gè)人主編轉(zhuǎn)變?yōu)榧w輪流編輯,從而避免了個(gè)人主編的單一和封閉。對(duì)此學(xué)界已有了很多相關(guān)研究成果,這里就不再展開詳細(xì)論述。
除了以上兩點(diǎn),還有一個(gè)重要的方面,即《新青年》品牌欄目“通信”欄的多元開放姿態(tài)。通信欄作為《新青年》“最具創(chuàng)意的欄目設(shè)計(jì)”(陳平原語),它的開辟與繁榮,成為報(bào)刊編輯史上極為成功的典范。通信欄的意義不僅是作為出入歷史的“資料庫”,它的價(jià)值還在于其為眾多聲音的共存提供了話語空間,“許多重要的問題和思想都在這里得到認(rèn)真的討論和發(fā)展”,《新青年》“通信”欄成為“中國雜志上第一個(gè)真正自由的公眾論壇”。《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文學(xué)論爭(zhēng)集》中第1編“初期的響應(yīng)與爭(zhēng)辯”和第2編“從王敬軒到林琴南”中收錄的40多篇文章中便有約一半的文章選自《新青年》的“通信”欄。②參見趙家壁主編、鄭振鐸編選:《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文學(xué)論爭(zhēng)集》[M].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盡管這樣的論壇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不平等性,但絕非《引領(lǐng)》一文所說的“社外的讀者兼作者不過是任由主撰拿捏的棋子”,“這些讀者兼作者的‘論者’成為主撰在調(diào)兵遣將時(shí)招之即來、揮之能去的兵勇”。“通信”欄是《新青年》主撰及編輯部同人合力經(jīng)營的品牌欄目,所謂“眾人拾柴火焰高”,同人的參與一方面,保證了通信欄的正常運(yùn)行,使欄目一直能夠保持回信與來信同步刊發(fā)甚至一信多復(fù)的狀態(tài);另一方面,編輯部同人之間不同的編輯理念又形成互補(bǔ),既容納了感性、偏激的言論,又于眾聲喧嘩中展露了思想的鋒芒,從而營造了多重對(duì)話的言論空間,使之成為《新青年》“最生動(dòng)最豐富的部分之一”[10]。
三、《新青年》同人的分裂
關(guān)于《新青年》同人的分裂,《引領(lǐng)》一文歸因?yàn)椤耙I(lǐng)與既成思路的緊張”,認(rèn)為陳獨(dú)秀“割舍不斷的政治情懷”埋下了“群體分裂的隱憂”:
……胡適等人一再責(zé)怪 “政治色彩過于鮮明”,甚至“聯(lián)合抵抗”,幾乎造成了分裂在即的局面,于是乎才有了《每周評(píng)論》的創(chuàng)刊。正如后來胡適所說:“在某種意識(shí)上說,這張小報(bào)的發(fā)行原是尊重我只談文化不談?wù)蔚闹鲝垺!?/p>
事實(shí)上,《每周評(píng)論》的創(chuàng)辦既非因?yàn)椤缎虑嗄辍吠恕胺至言诩础钡木置妫鼰o關(guān)乎胡適“只談文化不談?wù)蔚闹鲝垺薄?/p>
首先,《每周評(píng)論》創(chuàng)刊于1918年12月22日,適時(shí)《新青年》同人尚未達(dá)到“分裂在即”的局面。直至1920年1月,陳獨(dú)秀離開北京到了上海,《新青年》的編輯陣容發(fā)生了變化,李漢俊、李達(dá)、陳望道等社會(huì)主義者加入其中,《新青年》同人分化為“北京同人”與“上海同人”,這時(shí)才是真正“分裂在即”。而且“政治色彩過于鮮明”也不是胡適等人對(duì)陳獨(dú)秀的“指責(zé)”,而是陳獨(dú)秀的原話。1920年12月16日,陳獨(dú)秀在給胡適和高一涵的信中首先提到“《新青年》色彩過于鮮明”,他說:“《新青年》編輯部事有陳望道君可負(fù)責(zé),發(fā)行部事有蘇新甫君可負(fù)責(zé)。《新青年》色彩過于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胡適馬上回信到:“但此是已成之事實(shí),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 ”[11]因此,“《新青年》色彩過于鮮明”是胡適在回信中“引用”的陳獨(dú)秀的原話,而很多研究者在論述中都將其作為胡適等人首先提出的對(duì)陳獨(dú)秀的批評(píng),顯然是對(duì)史料理解的誤差,在此一并指出。
其次,《每周評(píng)論》不是為了胡適“只談文化不談?wù)蔚闹鲝垺倍鴦?chuàng)。對(duì)于當(dāng)事人胡適事后的種種解釋,學(xué)者在引用時(shí)是需要斟酌的。舒衡哲先生在對(duì)五四“記憶”如何延續(xù)的探討中,就提示了學(xué)者處理有關(guān)問題時(shí)應(yīng)有這樣的“自覺”。①參見舒衡哲著,李國英等譯.《中國的啟蒙運(yùn)動(dòng)--知識(shí)分子與五四遺產(chǎn)》[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此外,羅志田的《歷史記憶與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一文也涉及到這一問題,參見羅志田著:《近代中國史學(xué)十論》[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3.陳平原先生也指出“《新青年》同人‘自我建構(gòu)’的能力很強(qiáng),其‘五四敘事’異彩紛呈,令人嘆為觀止。對(duì)于此等由當(dāng)事人提供的“證詞”,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12]。1918年底《每周評(píng)論》創(chuàng)刊時(shí),胡適尚在安徽奔母喪,未聞其事。并且,《每周評(píng)論》創(chuàng)刊后,《新青年》也沒有轉(zhuǎn)而“不談?wù)巍薄?/p>
再次,胡適本人亦未能做到“不談?wù)巍薄:m在留美歸國之際就以 “講學(xué)復(fù)議政”自任,其后在《新青年》第5卷第4號(hào)開辟了《什么話?》欄目,在首期欄目中,其所搜集的“或可使人肉麻,或可使人嘆氣,或可使人冷笑,或可使人大笑”的報(bào)刊資料中,就有不少涉及政治的地方。如其輯錄的一則關(guān)于時(shí)任大總統(tǒng)徐世昌的言論:徐世昌就總統(tǒng)職宣言書中,有句云,“惟是事變紛紜,趨于極軌,我國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決時(shí)局,促進(jìn)治平耳。而昌之所慮,不在弭亂之近功而在經(jīng)邦之本計(jì);不僅囿于國家自身之計(jì)畫;而必具有將來世界之眼光。”[13]其中所暗含的針砭之意,較之陳獨(dú)秀通過國內(nèi)外大事記兩欄來曲曲折折地評(píng)論時(shí)政,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及至《努力周報(bào)》創(chuàng)刊,就更加鮮明地“代表自由主義知識(shí)分子站到議政、干預(yù)政治的前臺(tái)”。正如他自言:“我們本來不愿意談實(shí)際的政治,但實(shí)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shí)一刻不來妨害我們。 ”(《爭(zhēng)自由的宣言》)
可見,《新青年》同人產(chǎn)生分歧的關(guān)鍵不在于“是否”談?wù)危谟凇霸鯓印闭務(wù)巍_m時(shí)知識(shí)分子“談”政治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直接干預(yù)政治:或以個(gè)人身份加入政府成為職業(yè)官僚,或聯(lián)合組黨;二是間接干預(yù)政治:以知識(shí)精英的身份留在民間社會(huì),與政治系統(tǒng)保持一定的距離,通過大眾傳媒工具批評(píng)時(shí)政。從五四同人后期的分化來看,陳獨(dú)秀所代表的廣場(chǎng)型知識(shí)分子選擇了前者,創(chuàng)建了中國共產(chǎn)黨,并將《新青年》作為黨的公開機(jī)關(guān)刊物。而以胡適為代表的書齋型知識(shí)分子則選擇了后者,以邊緣知識(shí)分子的身份對(duì)政治發(fā)言,追求“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fù)責(zé)任的言論來發(fā)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jié)果”[14]的獨(dú)立精神。知識(shí)分子在價(jià)值追求與角色認(rèn)同上的重大差異,無疑成為同人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導(dǎo)致同人分裂的還有同人間性格的差異以及人事的紛爭(zhēng)等諸多復(fù)雜因素。
《新青年》同人分裂的原因如此頭緒紛亂、問題駁雜,恰恰說明了歷史的復(fù)雜性,它是由種種主客觀因素綜合在一起而最終造成的。由最初發(fā)行量?jī)H一千份的無名小刊,發(fā)展成為 “民初乃至整個(gè)20世紀(jì)中國影響最大的思想文化雜志”,《新青年》的輝煌得益于天時(shí)、地利、人和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樣,它的結(jié)束也是方方面面的共同結(jié)果,諸多因素糾結(jié)在一起才最終導(dǎo)致了同人的分裂。這一方面說明了歷史發(fā)展的復(fù)雜性,另一方面也證明了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性。從現(xiàn)代文學(xué)社團(tuán)的發(fā)展來看,從“新青年”到“少年中國”到“創(chuàng)造社”再到“語絲社”,同人的分裂與分化幾乎成為文人團(tuán)體不可逆轉(zhuǎn)的宿命。這其中處于引領(lǐng)地位的主撰固然有不容推卸的責(zé)任,但絕非張寶明教授所說的,有一個(gè)“剛?cè)岵?jì)的‘動(dòng)感地帶’”就可以避免得了的。將一個(gè)包含著諸多矛盾的復(fù)雜歷史歸因?yàn)閭€(gè)人的失誤,既對(duì)歷史人物有失公允,也有違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在抹煞歷史的豐富性的同時(shí),也遮蔽了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性。
[1][7]陳平原.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xué)——《新青年》研究(上)[J]. 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02,(3):116-155.
[2]張寶明.“主撰”對(duì)《新青年》文化方向的引領(lǐng)[J].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08,(2):90-99.
[3]耿云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7冊(cè))[M].合肥:黃山書社,1994.260-261.
[4]陳獨(dú)秀.答顧克剛[J].新青年,1917,(5):6.
[5]陳獨(dú)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J].新青年,1918,(1):1-5.
[6]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冊(cè))[M].臺(tái)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4.358.
[8]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運(yùn)動(dòng)回憶錄(上)[M].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79.157.
[9][美]周策縱.五四運(yùn)動(dòng):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革命[M].周子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93.
[10]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五四時(shí)期期刊介紹(第1集)[M].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9.39.
[11]任建樹等.陳獨(dú)秀著作選(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23-224.
[12]陳平原.《觸摸歷史與走進(jìn)五四》自序[J].博覽群書,2003,(6):77-78.
[13]什么話? [J].新青年.1918,(4):435.
[14]引言[J].獨(dú)立評(píng)論.19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