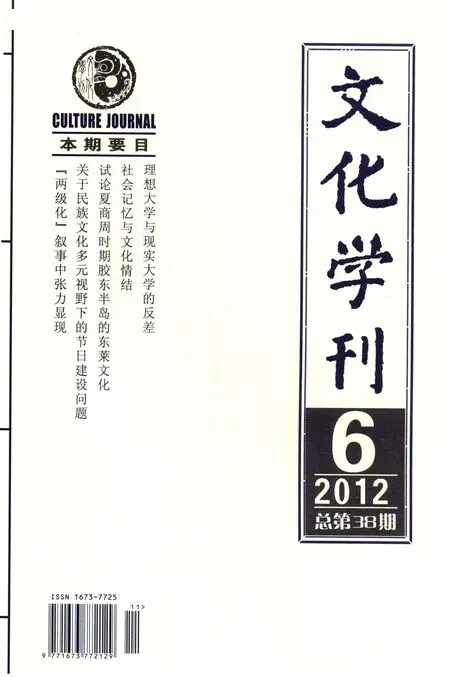評《唐宋社會變革論綱》
祁志浩
(作者系云南大學人文學院助理研究員)
“唐宋變革”論是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長期備受矚目的重大課題之一。其成說既久,流變有加,影響不可謂不深。但回顧和總結一個世紀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正如李華瑞教授在《“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一文中所說:“中國學界認識唐宋之際社會變動甚早,更不乏真知灼見,但始終沒有從范式的角度特別關注唐宋的社會變革,即便有也是從五個社會形態理論出發把宋代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階段加以認識”。《唐宋社會變革論綱》(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以下簡稱《論綱》)則恰是針對學術界的此種不足,試圖從理論范式的角度給唐宋變革以全新的解釋,可謂是一部極富張力的佳作。
一
林文勛教授長期關注“唐宋變革”這一論題,《論綱》是其十年間對該問題所思、所想的集中迸發。研究歷史,林文勛教授注重實現“在縱向上溝通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在橫向上溝通經濟史和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等的聯系”。《論綱》正是很好地體現了這一觀點。
該書篇章緊湊、邏輯清晰、語言練達、觀點精到。全書除“引論”與“結論”外,凡四篇,共計29萬字。細讀之下,不難發現其呈“總-分-總”格式布局,且對史學研究的慣用要素皆有顧及與圈點,思路、行文合乎書之思想性要義,處處皆現作者匠心。
“引論”中,作者緊緊圍繞“商品經濟”這一代表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動力源”展開論說,指出“凡是中國社會商品經濟大發展的時期,都是社會大變革的時期”,故而應將商品經濟史研究上升到歷史哲學的高度,既要 “對商品經濟的力量給予充分肯定”,又要 “用商品經濟的歷史觀看待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第一篇“總論”,作者上承“引論”的核心論點,細數學界關于“唐宋變革”論認識的種種,認為“唐宋社會的變革是商品經濟沖擊下原有社會要素和社會關系的重新組合”,應“以商品經濟的歷史觀研究唐宋史”,“必須全面研究商品經濟與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的關系,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視點,開辟一些新的研究路徑”。更進一步,作者強調尤其應重視商品經濟對唐宋社會變革的根本性影響,最顯著者,即是“富民社會”的形成;第二篇題為 “商品經濟與經濟關系及階級關系的變革”,作者分別細致考察了唐宋時期土地私有產權確立與商品經濟之互動關系、財富力量崛起給予社會變革的影響、富民階層興起的歷史意義、商品經濟與兩宋農民戰爭之關聯,認為“唐宋社會變革就是商品經濟發展引起的財富力量崛起對社會的全面沖擊和瓦解”,“富民階層的崛起,是唐宋社會在商品經濟發展推動下財富分化不斷加劇的結果”,并進而指出“所謂唐宋變革,就是從漢唐的‘豪民社會’轉變為‘富民社會’”。同時,在林文勛教授看來,富民階層的出現對唐宋社會經濟關系、階級關系、生產關系、價值觀念等均帶來了不小的影響,這既為后文深入論述作了鋪墊,又與全書的謀篇布局基調甚為協適,暗含著一致性,增強了論說力;第三篇題為“商品經濟與國家政策的調整及制度變革”。作者選取了唐宋時期的國家財政、專賣制度及民族政策進行分析,意在言明商品經濟與賦稅結構調整、賦稅征收的市場化趨勢、直接專賣向間接專賣的轉變(入中法的實施)、民族政策創新等方面存在著歷史的必然性,尤其是闡釋的如“商品經濟的發展,促成了唐宋專賣制度的大變革”、“隨著市場的擴大,周邊各少數民族卷入了宋王朝的市場體系,對宋王朝形成強烈的經濟依附關系”等論斷頗具啟示性;第四篇題為“商品經濟與思想價值觀念的變革”,雖僅兩個小節,所論卻是殊途同歸,無出本書主旨左右。通過林文勛教授的研究,我們看到了宋代義利之辨的經濟動因以及保富論背后所劍指的重大歷史進步性。同時他還強調,義利之辨“并不是脫離現實社會的而局限于思想領域的一場思想論辯,而是唐宋社會變革的必然產物,是隨著唐宋社會變革的展開而必然出現的一個深層問題”,“離開唐宋社會商品經濟的大發展,義利之辨就成為無源之水”,保富論是“唐宋社會經濟變化在人們思想觀念中的客觀反映。具體說來,則與富民階層的崛起和‘富民社會’的形成密不可分”;“結論”應可視作本書的理論升華。該部分在重申了唐宋社會變革與“富民社會”之關系后,又以“富民社會”為理論基石來反觀中國古代史的主線和體系,或者說是客觀、全面、鄭重地提出了中國式古史解釋體系的建構設想,即“中國社會經歷了從‘部族社會’到‘豪民社會’再到‘富民社會’并朝著‘市民社會’方向發展的變遷過程”。此舉無疑具有開宗明義的重大學術價值。
在《論綱》“導言”中,作者還對全書的寫作思路作過這樣的說明:“總的思路是,試圖以中國古代‘富民社會’體系為理論基石,對唐宋社會變革問題作一個宏觀層面的探討”。通讀之下,筆者認為,這樣的目的確然已經達到。
二
《論綱》是一部深具思想性與創新性的學術專著。這突出地反映在全書始終貫穿著兩條主線:一是商品經濟與唐宋社會變革間的內在聯系,二是中國古代“富民社會”體系的構架,并且這二者互為表里,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緣何說《論綱》具有思想性與創新性?原因有三。
首先,《論綱》抓住了“變革”的本質,突出了體系性。何為“變革”?柳立言先生認為,“變革”不是指一般的改變,而是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變,可說是一種脫胎換骨。對于此點,林文勛教授有著相似的看法,他認為“社會變革是社會的整體變化,而非局部的變化。它包括了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結構的調整、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政治制度的轉變、思想觀念的變化”。《論綱》中,作者即循此思路,從商品經濟與經濟關系、階級關系、國家政策、政治制度、思想價值觀念等方面對“唐宋變革”進行了宏觀勾勒,可以說是抓住了本質,把握了整體。
其次,《論綱》遵循了中國內在的發展理路。張廣達先生在《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中對內藤湖南的治學啟示作了歸納,他認為內藤“從內在理路思考中國的歷史”之路徑非常值得學習,并強調“在異說紛陳的今天,更需要借鑒內藤的經驗,博采眾說,做出獨斷”。某種程度上說,《論綱》很好地詮釋了此點啟示。《論綱》以唯物主義史學觀客觀、系統地對理解中國社會內在發展理路的關鍵——商品經濟,作了根本性的梳理。以此為據,作者在書中屢出新見,他言道,“在中國傳統社會,凡是商品經濟大發展的時期,也就是社會大變革的時期”;“商品經濟始終是推動社會變革與進步的重要力量”;“唐宋時期,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下,商品經濟走出西漢中葉以來所形成的低谷并很快繁榮發展,形成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所謂‘唐宋社會變革’,既不是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后期的轉變,也不是中國傳統社會由中世向近世的轉變,更不是由古代到中世的轉變,而是從漢唐的‘豪民社會’變革為唐宋以來的‘富民社會’”。品讀之,慎思之,明辨之,這些均不失為“獨斷”之見。
最后,《論綱》所建構的學說體系具有典型的理論范式意義。林文勛教授在談及 《論綱》的撰著主旨時講到,“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考述唐宋社會變革的諸種現象與事實,而對引發這一變革的深層原因與動力則分析不夠。本書正是想在此方面作一努力嘗試,意在構建唐宋社會變革的一個理論體系”。毫不諱言,此一“努力嘗試”成效甚佳。《論綱》之付梓,標志著林文勛教授在建構本土性唐宋社會變革論的理論道路上已邁出了夯實的一步。“研究歷史,貴有創見”,其意無外乎此。《論綱》為我們重新認識唐宋社會,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打開了一扇承載著別樣風景的窗口。
三
《論綱》亦是一部具有突破性與引領性的學術專著。書中寫道:“一項真正具有價值和水平的研究成果,既要能夠有助于解決已有的問題,又要能夠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提出新的問題”。其如此說,也是努力朝這個方向去做的。《論綱》最重要的貢獻即在于,以“富民社會”理論為基石,對唐宋社會變革作了新的闡釋,同時又提出了中國古代“富民”階層和“富民社會”這一新的研究課題,為下一步的研究開辟了新的方向。
中國傳統社會,“民”的演變是一條主線。研究中國古代歷史乃至理解近現代中國內部的諸多問題,必須重視從“民”的角度進行觀察和尋找答案。唐宋以來,中國社會最重大的變化之一就是形成了一個新的“富民”階層。
實際上,對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富裕人群進行的研究已有段時日。筆者目力所及,上世紀50年代,傅衣凌先生即對明清江南的富戶經濟進行過研究;梁方仲先生重點考察了富戶與明代糧長制之間的關系;80年代,洪沼對明初的遷徙富戶與糧長制、李龍潛對富戶制度與坊廂徭役制度進行了辨析;90年代,黃啟昌在研究中簡論了宋代的“富民階層”。2000年后,馮賢亮對明清江南富民階層的影響、刁培俊對宋代富民的分類界定、刑鐵對宋代富民的階層歸屬、鄭銘德對宋代富民的身份考辨、張邦煒對宋代富民的斷想等研究都產生了較深遠的學術影響。在日本,奧崎裕司、溝口雄三、檀上寬、植松正等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對這一問題作過個別研究。遺憾的是,這些研究僅僅是停留在研究的“點”上,未曾走向深入,亦沒有形成系統性理論就見于學界。相較而言,林文勛教授在長期研究基礎上凝練出的中國古代“富民”階層學術概念與構架的“富民社會”理論體系無疑具有某種開創性和引領性。
《論綱》中,林文勛教授指出:唐宋社會,在社會流動加快、產權制度確立和整個社會價值取向發生重大變化的過程中,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富民”階層確然業已興起,并迅速成為社會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的核心,成為整個社會的中間層、穩定層和動力層,與社會各個方面發生了廣泛而又深刻的聯系,最終使唐宋社會發生了整體性的結構變化,形成了一個新的“富民社會”。進而,他指出,“從唐宋,到元、明、清諸朝,中國社會都是一個‘富民社會’。‘富民社會’上承漢唐的‘豪民社會’,下啟近代的‘市民社會’,構成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階段”。無可否認,這是一種貫通的認識,且以其新范式、新體系而日益受到學界關注。近幾年,與之相關的研究正不斷問諸史林。
細究開來,“富民”階層和“富民社會”體系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一個值得討論的新興生長點,概因其找到了一把解構唐宋以來中國社會發展與變遷的鑰匙。我們知道,對宋及之后幾朝的研究,中外學者提出了眾所熟稔的“地方精英社會”、“士紳社會”、“科舉社會”、“平民社會”等學術概念和體系,豐富和推進了相關研究。然而,林文勛教授卻從這些研究中洞察出別樣的端倪。正如他在《論綱》中所言,“富民是宋代‘地方精英’和明清‘士紳’的基礎,富民的歷史特征決定著‘地方精英’和‘士紳’階層的特征及發展變化”。這樣的認識附于體系性的范式之上,顯然會對史學界諸多經典研究帶來沖擊與挑戰,也勢必將給相關領域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引發新的思考,收獲新的成果。換言之,其可以補益與增進學界對 “地方精英社會”和“士紳社會”等的準確把握,超越過往研究,拓展討論空間,延伸學術鏈條,為在整體上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與變遷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石。
總而言之,《論綱》不是踵武前賢之作,亦非無本之木。它是有個性、有特色的研究著作。研讀《論綱》,就是要入其境,揣其意;就是要從篇章的設置、定名等處體會到作者的良苦用意;就是要在字里行間覓得方法、尋到方向。這才是《論綱》以專著樣式付梓刊印之價值的最大彰顯,也是它與《唐宋鄉村社會力量與基層控制》、《中國古代“富民”階層研究》的最大區別,更是其在學術理論范式或體系方面帶給學界同仁的最大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