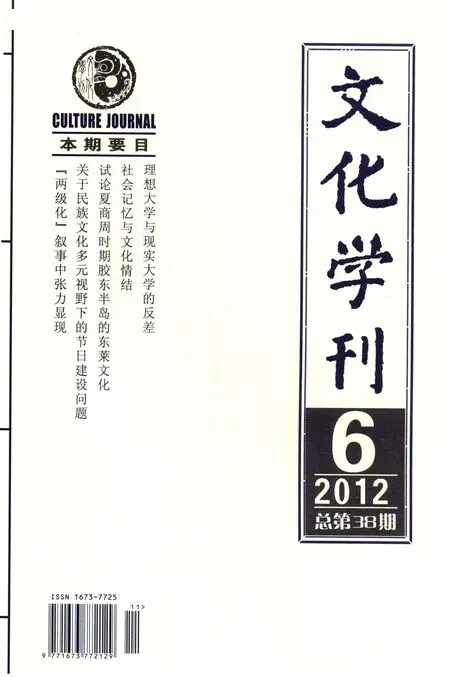“兩極化”敘事中的張力顯現——讀陳映真的 《將軍族》
高小弘
(大連理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遼寧 大連 116000)
被稱為“海峽兩岸第一人”的陳映真是臺灣備受爭議的作家之一,他在將近五十年筆耕不輟的創作生涯中,發表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發表于1964年的《將軍族》是陳映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以這篇小說命名的作品集1999年入選30部 “臺灣文學經典”,并在大陸被評為 “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
短篇小說《將軍族》不僅確立了陳映真在臺灣文壇的地位,而且也鮮明體現了他早期文學創作的主要特征,并以母題的形式潛在的規約著他以后的文學創作。綜觀這篇小說,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作者所采用的“兩極化”敘事方式。在這篇小說中,充滿了互相對立的因素:過去與現在、年輕與衰老、悲與喜、崇高與渺小、墮落與升華、骯臟與純凈等等,這些對立的因素共同存在于文本中,相互之間形成一種強烈的藝術張力,使一篇僅有幾千字的小說顯得豐盈厚重。
“張力”這一概念是美國新批評理論家艾倫·退特從物理學領域借用而來的文論術語,其范疇大致可做這樣的界定:“在整個文學活動過程中,凡當至少兩種似乎不相容的文學元素構成新的統一體時,各方并不消除對立關系,且在對立狀態中互相抗衡、沖擊、比較、襯映,使讀者的思維不斷在各極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觀念的影響下產生的立體感受。”[1]張力的存在使文本圓漲,不僅產生了意義的多元性,而且意義的綻放也造就了文本彎弓待發的緊張感。就《將軍族》而言,其在情節發展、意蘊表達、風格情境等方面都鮮明的體現出了這些特點。
《將軍族》敘述了一個大陸去臺灣的退伍老兵與一個臺灣本省女孩的愛情悲劇。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并未按照傳統的線性敘事模式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而是采用了內向式的敘事方法,即以心理探索式的語言鋪陳人物的心靈狀態,并以人物的心理流程作為情節發展的契機與動力。整篇小說幾乎都是由男主人公“三角臉”的心理流動聯綴起來的,在他的意識流動中,過去與現在的場景像電影中的鏡頭剪接交錯顯現,時空處在不斷的跳躍變化中。
小說開頭“三角臉”在為“高個子”修好伸縮管后無意間發現了已分別五年之久的 “小瘦丫頭”,“伊站在陽光里,將身子的重量放在左腿上,讓臀部向左邊畫著十分優美的曼陀玲琴的弧。”這種站姿使“三角臉”回憶起五年前在康樂隊里與 “小瘦丫頭”的一次月夜交談。在這次交談中,一個是漂泊異鄉無家可歸,一個是賣身為妓有家難回,“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共同遭際使兩個人的心開始走近。之后鑼鼓隊開始作業的聲音使“三角臉”回到了現實,“小瘦丫頭”神氣地指揮著樂隊,但他卻發現“伊的指揮和樂聲相差約有半拍”——因為“伊是個輕度的音盲”,而這又使他回到了五年前與“小瘦丫頭”隔著夾板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一次交談場景。那一次“小瘦丫頭”述說了自己逃出來的真實身份,而他也做出了自己一生中重要的人生選擇——“在伊的枕頭邊留下三萬元的存折,悄悄地離隊出走了。”幾支曲子吹過去之后,“三角臉”的思緒又回到了現實,而這時“小瘦丫頭”也發現了他,飽經滄桑的兩個人終于再次相見,并且以歡樂昂揚的姿態像將軍一樣雙雙自盡。
小說就是這樣在過去與現在的交錯中展示著情節的發展,并在二者的比較映襯中形成一種內在的張力。五年間,“三角臉”與“小瘦丫頭”在年齡外形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五年前的“小瘦丫頭”發育得很不好,又瘦又小,“仿佛一具著衣的骷髏”,現在卻“豐腴了許多”,“留著一頭烏油油的頭發,高高地梳著一個小髻。臉上多長了肉,把伊的本來便很好的鼻子,襯托得尤其的精神了。”而“三角臉”卻“已在蒼老著,像舊了的鼓,綴綴補補了的銅號那樣,又丑陋、又凄涼”,他們“一個生長,一個枯萎”,“一個日出,一個日落”,歲月的流逝帶來了生命不可遏制的變化。然而同樣在過去與現在的對照中,可以發現“三角臉”與“小瘦丫頭”的命運卻并未發生根本轉變。五年前,“三角臉”流落異鄉,孑然一身,在康樂隊里只能吹吹喇叭,編扯些馬賊、內戰、死刑的故事,但女隊員們除了聽他的故事外,沒有人再去理他,他只能在寂寞中思念著家鄉;五年后,“三角臉”依然以為喪家吹喇叭度日,體味著“一個賣給人的人的滋味”。而“小瘦丫頭”五年前被家人像牲口一樣賣給別人,逃出來后來到康樂隊,在舞臺上充當女小丑,“用一個紅漆的乒乓球,蓋住伊唯一美麗的地方--鼻子,瘦板板地站在臺上”,被臺下人笑謔著;五年后盡管她得到了“三角臉”的幫助,但她依然沒有逃離火坑,被賣到青樓,而且還被弄瞎了左眼,苦難的命運不但沒有發生改觀,反而更加重了。因此,在歲月年齡的“變”與苦難命運的“不變”之間,可以清晰地看到臺灣下層社會持續的困苦,小人物朝不保夕艱辛凄楚的生活現狀,使整個小說彌漫著濃烈的憂郁感傷與苦悶。在對苦難現實的描寫中,陳映真對生活于底層的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時也對現實的丑惡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而這種同情與批判不僅反映出作者對人生與社會的思考,而且也反映出作者的一種人道主義情懷,正如他自己所說:“首先要給予舉凡失喪的、被侮辱的、被踐踏的、被忽視的人們以溫暖的安慰,以奮斗的勇氣,以希望的勇氣,以再起的信心。”[2]
《將軍族》篇幅短小,意蘊卻極其豐富,這首先表現在人物內心豐富的表達上。“三角臉”是從大陸逃到臺灣的退伍兵,在他身上沾染著國民黨軍隊中普遍流行的惡習,狂嫖濫賭、放浪、愛吹噓,甚至晚上偷窺“小瘦丫頭”睡覺,這種墮落使他雖年近四十卻也不覺得老。然而與“小瘦丫頭”的兩次交談卻使他的靈魂從墮落的深淵中升騰,面對著“那樣地站著的、那樣輕輕地淌淚的伊”,他“油然一種老邁的心情”,“他是從未有過這樣的感覺的。從那個霎時起,他的心才改變成為一個有了年紀的人的心了”。正是心靈純凈的“小瘦丫頭”的苦難經歷使他的靈魂受到滌蕩,并最終決定傾其所有來拯救和自己女兒差不多大的“小瘦丫頭”,這一舉動與其說是在救贖別人,倒不如說是在救贖自己。而“小瘦丫頭”為現實所迫,被家人賣到青樓,身心都受到極大的戕害,但她在一定要活著再見“三角臉”一面的決心支撐下,終未淪落下去。小說結尾兩個飽受苦難折磨的人終于相見,然而他們自覺自己的身體已被這個社會漿染得骯臟不堪,因此他們只能相約在來世再聚:
“我說過我要做你老婆,”伊說,笑了一陣:“可惜我的身子已經不干凈,不行了。”
“下一輩子吧!”他說,“我這副皮囊比你的還要惡臭不堪的。”
遠遠地響起了一片喧天的樂聲。他看了看表,正是喪家出殯的時候。伊說:
“正對,下一輩子吧。那時我們都像嬰兒那么干凈。”
為了獲得心靈與愛情的純凈,兩個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然而正是在這種鳳凰涅槃式的行為中,靈魂獲得了升華,在墮落與升騰構成的張力之間,不僅構成了對精神的圣潔,心靈的高貴的熱切歌頌,同時也為這個灰暗的現實世界帶來了一抹希望的陽光。
陳映真有著濃濃的中國情結,他在“統獨論戰”中始終捍衛著祖國的統一,正如臺灣著名學者葉石濤所說:“他(指陳映真)的所有小說的主題大多離不開 ‘對于寄寓于臺灣的大陸人的滄桑的傳奇,以及在臺灣的流寓底和本地的中國人的關系所顯示的興趣與關懷’。”[3]陳映真自己也曾在2001年新華網的人物專訪中說:“一個分離和對峙的民族是一個殘缺和悲傷的民族。作為一個作家,我對此十分敏感,一直從文學審美的角度反映這種分離造成的痛苦。”“我希望我們的民族能夠重新團結。”作為陳映真重要的文學作品,《將軍族》也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的這種熱望。小說中的主人公“三角臉”與“小瘦丫頭”,一個是大陸來到臺灣的退伍老兵,一個是臺灣本省的下層居民,他們之間由于共同的苦難命運產生的相濡以沫的戀情隱喻的正是大陸人民與臺灣人民能夠相親相愛,早日實現團圓的夢想。小說由于契合了海峽兩岸人民渴望統一的心態,因此打動了無數炎黃子孫的心,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而這種藝術效果的獲得與共存于文本中的兩種敘事密切相關,一種是男女主人公苦澀愛情的個體敘事,另一種是渴望祖國統一的宏大敘事,二者之間同樣構成了一種張力,這種張力使二者和諧的統一在文本中,不僅具有宏大的現實指向,同時也產生了強烈的藝術審美感染力。
由于《將軍族》的“兩極化”敘事方式,使得它的整體風格也不全是單一的色調,而是斑駁陸離,豐富駁雜。小說敘述的是一個哀傷慘淡的愛情悲劇,但作品中卻又時時洋溢著喜樂的氣氛。小說是如此開頭的:“在十二月里,這真是個好天氣。特別在出殯的日子,太陽那么絢燦地普照著,使喪家的人們也蒙上了一層隱秘的喜氣了。”這種喜氣連感傷的《荒城之月》也“有一種浪漫的悅樂之感”。而在小說結尾當“三角臉”與“小瘦丫頭”決定要自盡時,這種歡樂被涂抹得更為顯眼:
他們于是站了起來,沿著坡堤向深處走去。過不一會,他吹起《王者進行曲》,吹得興起,便在堤上踏著正步,左右搖晃。伊大聲地笑著,取回制帽戴上,揮舞著銀色的指揮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著正步。年輕的農夫和村童們在田野向他們招手,向他們歡呼著,兩只三只的狗,也在四處吠了起來。
太陽斜了的時候,他們的歡樂影子在長長的坡堤的那邊消失了。
一個悲慘的故事卻被包裹在歡樂的氛圍里,這種悲喜倒置造成了強烈的審美效果,悲與喜之間形成了一種內在的張力,不僅不會因為快樂的氣氛沖淡悲劇的效果,反而會更增添悲劇的濃度,正所謂以樂景寫哀,反倍增其哀。尤其是小說結尾兩人殉情的場面,充滿了喜慶,而這種喜慶更令人感到心酸和哀惋。“戀”生“畏”死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但是他們整個死亡的過程不僅十分平和,甚至有幾分絢麗,這里的死亡不像是終結一切的幽靈,而更像是能撫慰苦難心靈的天使,這種反常與顛倒實際上大有深意。當苦難日益將人逼向極處,死亡便不再是“虛無”的了,而是有了解脫甚至是帶來心靈安慰的意義,如果這種意義愈是被凸顯出來,則愈能顯示出存在的無意義,死亡的過程越是輕松愉快,就越能體現出現實生存的沉重悲苦。“三角臉”和“小瘦丫頭”在現實世界中飽受磨難,因此他們將希望寄托于來世,死亡便成了解脫苦難的一種方式,甚至成為一種幸福。正是這種悲與喜的對照映襯,使小說中充斥著濃烈的悲涼與凄苦,產生了強烈的藝術審美效果。
當然除了悲喜風格情調的對照外,《將軍族》中還存在著一種卑微與崇高的對照。小說主人公“三角臉”與“小瘦丫頭”都如草芥般生活于社會的底層,是屬于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然而他們的生活雖艱辛凄楚,但卻不委瑣茍且,他們以頑強的生命力與苦難抗爭,最后甚至用死來捍衛心靈情感的純潔以及做人的尊嚴,小說的題目《將軍族》以及兩人殉情前吹奏的《王者進行曲》都具有這樣的象征意味,他們活得雖然卑微,但他們在精神上是高貴圣潔的,他們的死“看來安詳、滑稽”,但“都另有一種滑稽中的威嚴”,就像兩位大將軍。而小說也正是在這種卑微與崇高的兩極對照中形成一種張力,既表現了對下層社會弱勢群體的深切同情,也熱切地呼喚與期望著人的價值與尊嚴的實現。
[1]孫書文.文學張力:非常情境的營建[J].內蒙古大學學報,2002,(2):61-67.
[2]陳映真.陳映真文集·文論卷[M].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415.
[3]葉石濤.走向臺灣文學[M].臺北:臺北自立晚報社出版社,1990.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