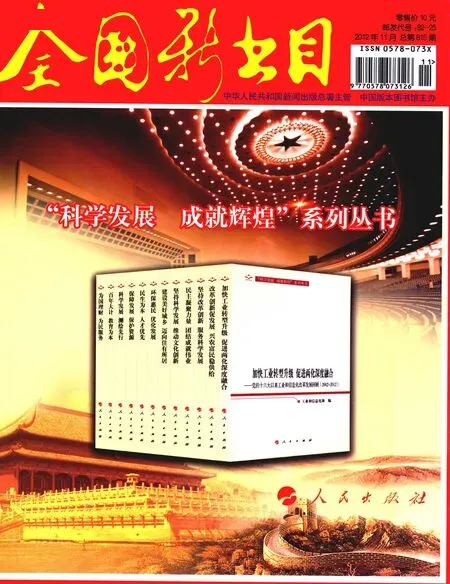理智世界中最快的一桿女槍
——瑪麗·麥卡錫
傳奇
理智世界中最快的一桿女槍
——瑪麗·麥卡錫
生于1912年的麥卡錫六歲就成了孤兒,她的幾位親戚將她撫養長大。當她長到22歲時,這個孤兒就變成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生,稚嫩臉龐上卻凸顯一雙犀利、尖刻的眼睛。那目光中透露著一個能夠寫出一手引人矚目的評論文章的特殊氣質,正是這兩方面才使得麥卡錫的微笑像蒙娜麗莎一樣在文學圈非常出名。
麥卡錫就讀的瓦薩女子學院,有一份官方的文學雜志《瓦薩評論》,因為過于保守,遭到麥卡錫和幾個先鋒學生的一致抵制。她們自費創辦了另一本刊物,取名《通靈者》(也譯作《反精神》)。由于雜志的內容及文風過于尖銳,不久便被學校勒令停刊,但它無疑在校園內掀起了一場“革命”的旋風。大學畢業后,麥卡錫去了紐約,并為《新共和》及《民族》兩本雜志撰寫文章,針對《先驅導報》、《星期六評論》、《時代》的評論家和書評家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22歲,一個剛剛邁出校門的女孩,開始在文學圈建立聲名。這樣的早年寫作經歷,奠定了麥卡錫日后文學作品的底色:“無論我的寫作方式如何,我想都是以批評的方式醞釀而成的。”麥卡錫的諷刺作品《學院叢林》是美國最有名的校園小說,其濃厚的學究氣的冷嘲熱諷讓人過目不忘。
人們經常把她與海明威相提并論。麥卡錫雖然影響極大,但由于我行我素的性格,與美國文學大獎無緣,直到1984年她才獲得國家文學勛章和麥克道爾文學獎;1989年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學院院士。1933年,麥卡錫首次在左翼刊物《新共和》上發表文章,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與批評之路。到1989年止,麥卡錫先后發表24部作品和眾多評論,其中《女研究生群體》銷量過百萬冊,使她在大眾中獲得聲譽;《一位天主教少女的回憶》和《我的成長》成為美國傳記文學的經典之作。麥卡錫的長、短篇小說通常會融入她深刻的個人體驗,她還經常諷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她最著名的小說《群體》(1963年)描寫8位女性1933年從瓦薩學院畢業后的生活。她始終憑借獨樹一幟的風格在美國文化界占據一席之地。被《紐約時報》贊譽為“我們時代唯一真正的女作家。”
麥卡錫作品的特點可以概括為兩個短語:惡意的嘲諷和冷靜的機智。如果說愛爾蘭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認為世界基本由傻子和無賴這兩種人構成,那么麥卡錫跟他的觀點差不多。她從不愛她筆下的人物,這個被同時代人稱為“可能是美國有史以來最聰明的女人”,一直藐視著她作品中的每一個人。麥卡錫大部分小說探討的主題是兩性關系和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她通過對一個個女主人公的塑造,用辛辣的語言和諷刺的態度將自己的觀點一一展示在作品中。從寫第一本書《伙伴》(短篇小說合集)起,麥卡錫就打算震驚世界。憑借其中的《穿布魯克斯兄弟牌襯衣的男人》和《耶魯知識分子肖像》等文章,證明她的確做到了。這些故事中,每個人都有些缺陷,無法適應美國生活,這些判斷是關于階級、品位、才智的論述,麥卡錫的好友德萊特·麥當勞曾這樣概括她對筆下人物的態度:“為什么她要那么自以為是,她是神還是什么?你會對她筆下可憐的人感到同情,他們總是那么荒唐無賴,或者純粹低人一等,令人厭惡——她總是告訴他們正在丟人現眼。對他們僅僅是蔑視,她可憐的傀儡只能在書頁間枯萎……”這一評論雖有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味,卻也并無不公。
最后一部小說《群體》出版后,盡管有人認為它一度敗壞了瓦薩女子學院良好的聲譽,但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還是將它列為了“99部現代主義佳作”之一。麥卡錫關于《群體》,她是這樣說的:“我從羅斯福總統就職儀式開始寫起,從一開始就把幾個女孩推到了那個時代,后來我決定寫到艾森豪威爾總統就職典禮時就打住。打算寫成那種搞笑式的編年體小說,真正要傳達的是關于進步的理念。從女性的視野、從柔弱者的角度審視的進步理念。你知道,會涉及家庭經濟、建筑、室內裝修、墮胎、生兒育女。我要把它寫成20年代在進步理念中信仰失落的歷史。”冷漠的文風和貧乏的人性描寫也貫穿了小說的始終,女主人公的放浪不羈再次受到麥卡錫的“不屑”。她始終是個自傳型作家,需要她的個人歷史來提供她從來不曾完全理解的人物,以及能夠給她興趣和挑戰的現成故事。她和自己的故事為她提供了她不善于編造的情節片段,一個讓她能夠推動故事發展的人物。”
麥卡錫在創作和批評兩個領域展現了那個時代特有的左翼激情。60年代麥卡錫親自到河內和西貢等地奔波,將見聞及感受寫成了《河內》和《越南》兩本書,以第一手資料將美國在越南的所作所為全盤托出,隨后,她還積極參加了在巴黎、倫敦、華盛頓和紐約等地的反越戰活動。她是最早提出美國應該從越南撤軍的少數美國人之一,她把這種思想寫在小說、報告文學和政治評論中,影響廣泛。
麥卡錫的個性素來不喜歡拐彎抹角,任何批評都是直來直去。她更不善于嘩眾取寵,對于大家熱捧的作家她總是有理由潑去一瓢冷水,即便對于“美國人的良心”似的大眾英雄,她也敢在電視上公開“攻擊”。諾曼·梅勒曾列出了一個美國文學圈的“史詩性”人物名單,其中,他把麥卡錫稱作“我們的第一文學夫人,我們的圣人,我們的仲裁人,我們的文學獨裁者,我們的大砍刀,我們的巴里穆爾,我們的貴夫人,我們的主婦,我們的圣女貞德”。談到大砍刀似的批評方式,麥卡錫當之無愧。上世紀60年代前后,塞林格開始名聲大噪,當有人問麥卡錫如何看待塞林格及其作品時,她直截了當地說:“我不喜歡塞林格的作品,他最近的那個東西算不上一部長篇,你說它是什么都可以。它充斥著那種讓人極不舒服的大城市人的矯情,而且還自戀得要命。另外,我覺得他好像還挺假的、挺老謀深算的。在一個普通人身上集中了一種絕對是自大狂的利己主義。我真是一點都受不了。”這席話隨后在社會上引來了一片嘩然。在一次電視訪問中,她還曾公開批評賽珍珠、斯坦貝克、索爾·貝婁等大作家,說他們“名過其實”,真不應該讓他們得到諾貝爾獎金。她說這番話時,賽珍珠和斯坦貝克都還健在,而此話一出,對諾貝爾獎評審們來說也無疑是當頭一棒。麥卡錫一向心直口快,甚至對自己不利的話也一吐為快。這為她招至了不少麻煩。在將近70歲時,她還為此跟莉蓮·赫爾曼鬧上了法庭。
從40年代正式提筆到70年代逐漸隱退,一位喜愛麥卡錫的學者如是說:“對當時那些有見識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而言,是個典范,是個榜樣:不受懲罰的壞女孩,對每個人都大加奚落的刻毒諷刺家,將關于女性感受的陳規俗套推翻的機智的批評家和隨筆作家——總之,她是理智世界中最快的一桿女槍,性感大膽而聰敏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