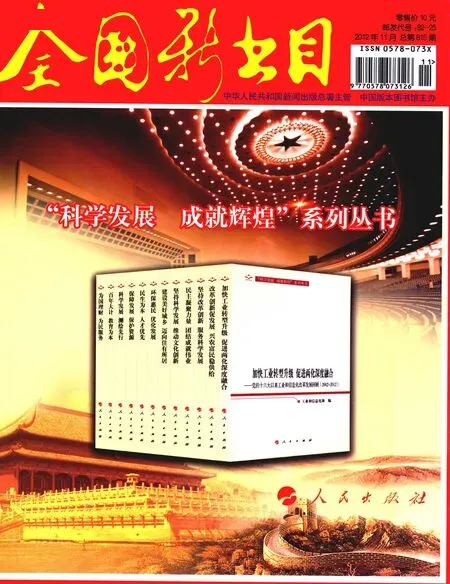那么喧囂,如此孤寂
文 / 覃田甜
那么喧囂,如此孤寂
文 / 覃田甜
有別于《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文茜的百年驛站》是完全不懂政治、不關心經濟的讀者也能親近和擁抱的一部文學作品,書中收錄的大多為陳文茜創作于2010年底—2011年的雜文隨筆,是一本以情感為線索、人物故事為表象、思想為內核的歷史人文散文集,所涵括的既有看得到的世界,也有看不到的內心。
文茜說,“他們的漂泊與沉默,是我一整年的回憶。”“他們”中,既有獻身時代、沉默不語的“父祖輩”,或有數面之緣或神交已久的名流賢達,也有重情重義、英年早逝的友人,在天災面前堅守著自己的土地與信仰的普通民眾,還有風云變幻中令人嗟嘆與凝思的歷史人物。《文茜的百年驛站》,透過沉淀半生的私人記憶,與文茜一起紀念那些過去的人,紀念那個過去的時代,紀念那個時代衍生的各種人生故事。
《文茜的百年驛站》,濃縮了文茜的人生回憶。
她寫下外公何集璧在那個風云變幻的大時代加入共產黨、“二二八”之后避難于南投山區、家族命運不可避免走向悲劇的滄桑故事,寫下外婆面對艱難人生獨力顧養子女的堅強與偉大、蒼老與孤寂,更釋然面對自己深埋在心底三十余年對母親愛恨糾結的情感。大時代中悲劇的家庭、長于海峽彼岸的個人,閱讀這些歲月篇章,我們如同目睹并感受著一個早熟、易感的小女孩如何在大時代里歷經挫折磨難、奮力成長,以至終成為一個美麗、成熟、睿智的女人。
終于,我們在那些浸含著淚水的文字中明白,文茜為什么說“不可能一群人永遠恨著另一群人”,這放下與和解的力量源自于哪里。繼承了家族獨特的熱情、慷慨與勇氣,“愈愛你的人,了解時代愈深,也愈愿意寬恕這一切”,在他人還停留在彼此仇恨的時代,文茜早已跨越族群、政黨、成見、創痛與仇恨,以豁達超脫的態度面對沉重的人生,把種種傷痕與悲涼藏于內心。
《文茜的百年驛站》,簡筆勾勒出臺灣百年的身世記憶。
從“隨風漂浮”的父祖輩到艱難闖關的張仲謀,從臺灣經濟起飛的島嶼女工到有情有義、古道熱腸的孫大偉,這些鮮活生動的人物無一不是臺灣社會和歷史進程的縮影。恰如文茜所說,“我想書寫,紙是我一生永恒不變的戀人。它讓我盡情地抒發心中的悲或樂。”
“沉默的父親”一篇中,文茜用文字救贖了失語的一代國民黨老兵,伴隨他們生命歷程的都是那種揮之不去的濃濃思鄉之情,和隱忍不發的巨大創痛。當我們跟隨文茜的文字進入戰火紛飛的年代、生離死別時的情境,我們的情感仿佛進入熔點,感動的淚水便忍不住奪眶而出。文茜從來不浮泛地談論空洞和宏大的話題,筆端飽含著對每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同情和理解。在悼念鳳飛飛的文章中,文茜書寫的不是舞臺上光鮮亮麗的歌后,而是滿腹辛酸、含淚追夢的林秋鸞,她所記取的“更多的不是掌聲,而是舞臺燦花外深埋落花底下的灰燼”,所追憶的是那個疼痛、貧困,但毅力充沛的臺灣經濟起飛時代。文茜筆下的人物置身于島嶼獨特環境下,其種種遭際和情感所帶來的巨大張力,讓我們不斷地回味和思索。
《文茜的百年驛站》,更是一位女性思想者的箴言集。
在充滿缺憾的歷史里,文茜不斷叩問,無時或已的憂患意識展露無遺。在無情的海嘯面前,文茜將無聲的悲痛、最感恩的惜福化作筆尖的呼喚,呼吁人類勇敢面對地震與我們同在的真相,比起防御“核輻射”,更重要的是建立真正的理性。文茜寫獨裁者的終結,摒棄跟隨西方世界發聲,拒絕媒體片面的洗腦。而在悲歡交集的南京,她面對莘莘學子,看到了令人溫暖的希望,“一個時時鞭策自己的國家,會往上爬;反之,每天自我感覺良好的國度,只會往下走。”一流的文筆之外,更能讓人體會到強烈的時代感與敏銳的歷史感,字里行間所發散的愛與智慧,令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