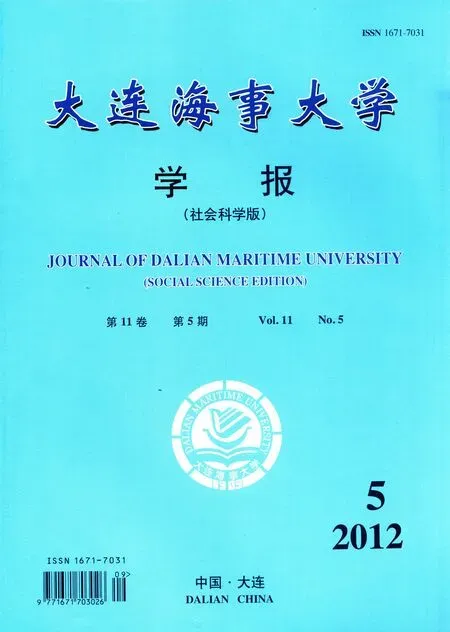論柏拉圖對民主制的批評
申 林
(國際關系學院 國政系,北京 100091)
民主制度是當代世界備受推崇的政治制度,但是在歷史上民主制度長期遭受批評。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批評民主的聲音不絕于耳,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柏拉圖。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于民主制的嚴厲批評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反民主的形象被烙于人們的腦海之中,這使得柏拉圖遭到當代很多政治理論者的批評。①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波普爾對柏拉圖的批評。參閱文獻[1]。本文不是要繼續對柏拉圖進行批評,而是要分析柏拉圖為什么要批評這種民主制以及如何評價柏拉圖對民主制的批評。
一、柏拉圖批評民主制的原因
在闡述柏拉圖對民主制的批評之前,首先應當弄明白的是柏拉圖批評的是什么樣的民主制,也就是說,柏拉圖是反對某些形式的民主制還是對所有形式的民主制一概反對,這是理解柏拉圖民主觀的前提。不然,泛泛談論柏拉圖反對民主制不但了無意義,而且還可能導致對柏拉圖思想的誤讀。
古希臘特別是雅典被看做西方民主制度的搖籃,在這里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從雅典民主的黃金時代伯利克里時代一直到柏拉圖生活的時代,雅典的民主制度都具有以下三個基本特征:其一,直接民主。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公民大會由所有公民組成。在雅典,公民僅限于年滿20歲的男子,他們都可以參加公民大會,直接參與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其二,官員絕大多數通過抽簽的方式產生。盡管公民大會可以由全體公民組成,但其他國家機關不可能也由全體公民組成,所以,必須選舉出一定數量的官員。在伯利克里時代以及之后的雅典民主政體下,官員中的絕大多數通過抽簽的方式產生。[2]其三,平民派在民主政制中占優勢。盡管在民主制度下全體公民都可以參加公民大會,但平民人數占據優勢;民主制度下主要采用抽簽的辦法選舉官員,這有利于平民而不利于寡頭;民主制度下還采用貝殼放逐法,把一些認為有可能危害城邦政制的寡頭首領流放出城邦。所以,在民主制下,多數平民掌握了實際的最高國家權力。
綜上所述,雅典民主制度是平民統治下的直接民主制。柏拉圖批評的民主制正是這種平民統治下的直接民主制。柏拉圖指出,民主制就是在平民政體之下,除一些受到懲罰的敵黨外,“其他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權及做官的機會”[3]557A。
柏拉圖對于民主制(具體而言就是直接民主制,下文同)的批評主要集中于《理想國》中。柏拉圖之所以批評民主制,從根本上來講,是因為古希臘的民主制違背了柏拉圖的國家正義原則與個人正義原則。
正義是柏拉圖《理想國》的核心概念。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提出了兩種正義,一種是國家正義(亦作“城邦正義”),另一種是個人正義。柏拉圖認為,國家中的人由三部分構成,他們分別是統治者、輔助者和生產者,他們的品質也分別是智慧、勇敢和放縱。當一個國家中統治者統治、輔助者輔助、生產者服從,三個等級按照分工各司其職時,它就實現了正義。柏拉圖同時認為,人的靈魂也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構成,它們的品質分別是智慧、勇敢和放縱。當一個人的靈魂由理性處于支配地位、激情輔助理性、欲望服從理性,整個靈魂達到一種節制狀態時,這個人就達到了正義。[3]434C,442D國家正義與個人正義是柏拉圖追求的核心理念,是否符合國家正義與個人正義,是柏拉圖判斷政治制度好壞的主要標準。在柏拉圖看來,民主制恰恰違背了國家正義與個人正義原則。
一方面,民主制違背了國家正義原則。首先,柏拉圖認為,民主制之下不恰當的平等違背了國家正義原則。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圖在此所講的數量平等并非社會財富領域中的分配平等。柏拉圖并不反對社會財富的平等分配,因為這在他看來有利于社會穩定。[3]422A所以,在《法篇》中,柏拉圖明確提出,在土地的分配上一定要平等。[4]754B-E柏拉圖所反對的是政治權力分配領域中的平等,也就是人人可以平等地成為統治者,這正與要求智慧者對非智慧者的統治的國家正義相違背。依據國家正義標準,哲學王統治是最好的政制,因為哲學家富有高度智慧,最適合擔任統治者。在柏拉圖看來,民主制正好是哲學王統治的反面。如果說哲學王統治最能體現國家正義的要求,民主制則是對國家正義的嚴重偏離。民主制賦予每一個公民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利,而不問他們是否具有行使該項權利的能力;民主制賦予公民以同等的政治機會,把執政官、陪審員等重要職位交由抽簽產生,而不問由這種方式產生出來的統治者素質如何。總之,民主制不加區別地承認人人平等,而不管他們應不應當平等。[3]558C柏拉圖認為,這嚴重違背了權力分配中的應得原則。對于民主制下的平等,柏拉圖諷刺性地描繪道:父親盡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兒子,而兒子也跟父親平起平坐。外來的依附者也認為自己跟本國公民平等,公民也自認和依附者平等。教師害怕學生,迎合學生,學生反而漠視教師和保育員。年輕人普遍地充老資格,分庭抗禮,侃侃而談,而老一輩的則順著年輕人,說說笑笑,態度謙和,像年輕人一樣行事,擔心被他們認為可恨可怕。[3]562E-563B
其次,民主制之下的過分自由也違背了國家正義的原則。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圖并不是一味地反對自由,其實柏拉圖也是自由的追求者和捍衛者,不過他所追求和捍衛的是一種共同體的政治自由,而非一種私人領域中個人行為不受干涉的自由。①上述兩種自由也就是近代法國思想家貢斯當所講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以及當代澳大利亞政治學者佩迪特所講的無支配的自由和無干涉的自由。參閱文獻[5-6]。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批評的自由不是共同體的政治自由,而是在共同體政治自由的前提下個人行為的自由。在柏拉圖看來,國家正義要求公民各司其職,但民主制卻賦予個人無限的行為自由,使他們不把自己的職責當回事。柏拉圖以夸大的口吻說道:“在這種國家里,如果你有資格掌權,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權;如果你不愿意服從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從,沒有什么勉強你的。別人在作戰,你可以不上戰場;別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歡,你也可以要求戰爭……那些被判了死罪的或要流放國外的,竟好像沒事人一樣,照舊在人民中間來來往往。”[3]557D-558A就連蓄養的動物在這個城邦也比在其他城邦里不知自由多少倍,狗變得同其女主人一樣,驢子在大街上自由地撞人。[3]563C
再次,民主制容易導致僭主政制,而僭主政制是對國家正義的最大偏離。柏拉圖認為,民主制比寡頭制更容易導致僭主政制。其一,在寡頭政制之下,人們關注財富的積累,對放縱欲望的行為持一種蔑視態度,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利于具有放縱特點的僭主式人物的成長,所以,僭主式的人物相對較少,因而導致僭主統治的機會較少。但鼓勵人們放縱欲望和追求過度自由的民主政制卻是僭主式人物滋生的溫床。其二,在寡頭政制下,寡頭們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因此,僭主式人物除了數量較少外還受到寡頭們的壓制,很難掌握國家權力;而在民主制下,盡管它是多數平民的統治,但多數平民在很多時候卻處于一種消極的狀態,他們無知和輕信,易受僭主式人物的左右,所以僭主式人物處于主宰地位。僭主式人物故意在平民和富人之間制造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平民往往接受僭主式人物為自己的領袖,從而為把僭主式人物推向權力頂峰鋪平了道路。[3]564D-566D
另一方面,民主制違背了個人正義原則。柏拉圖認為,個人正義呼喚人們追求美德,但民主制的本質要求卻是放縱欲望。在民主制下,公民大會制與抽簽制使得多數平民掌握了國家權力,成為國家的統治者。平民在柏拉圖的眼中屬于“生產者”行列,放縱欲望是他們品質的基本特點,他們對美德不屑一顧,只想千方百計尋歡作樂,不知道什么欲望應該得到鼓勵和滿足,什么欲望應該加以控制與壓抑。他們的生活遠遠背離了美德。[3]561C-D在柏拉圖看來,既然民主制不是以美德為目的,那么其對不符合美德的現象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便不足為奇了。柏拉圖批評道,民主制度是寬容的,對建立理想國家時所宣布的莊嚴原則是蔑視的。它以輕薄浮躁的態度踐踏所有這些理想,完全不問一個人原來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轉而從政時聲稱自己對人民一片好心,也就能得到尊敬和榮譽。[3]558B-C
柏拉圖認為民主制敗壞美德。孟德斯鳩卻把品德看做是民主政體的原則,如果人民的品德腐化,民主制國家就會衰敗。[7]23-25托克維爾在談論美國民主時也指出,民主制增進了美國人民的公共精神、權利觀念和法律意識。[8]密爾也認為民主制有利于培養人民的美德,它既能強化人民的公共觀念,同時還有利于形成一種積極進取的民族性格。[9]在民主制與美德的關系上,何以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呢?其實,孟德斯鳩、托克維爾與密爾的觀點與柏拉圖的觀點并不矛盾。就孟德斯鳩與柏拉圖的差異所言,柏拉圖談論的是實然層面的東西,孟德斯鳩談論的是應然層面的東西,也就是說,柏拉圖要表達的是民主制會對道德產生哪些不良影響,孟德斯鳩要表達的卻是民主制下人們應當擁有什么品質。就托克維爾、密爾與柏拉圖的不同所言,一方面,托克維爾和密爾所談論的民主制是代議民主制,柏拉圖談論的民主制是直接民主制;另一方面,托克維爾和密爾所講的公共精神、權利觀念、法律意識、積極進取的民族性格乃是公共美德,柏拉圖所批評的則是人們對欲望缺乏節制,這是一種私人美德。也就是說,他們談論的民主制不是同一種民主制,他們談論的美德也不是同一種美德。總之,柏拉圖對于民主制違背個人正義原則的批評,其主要含義是直接民主制對于人們私德的侵害,尤其是對私德中至關重要的節制品質的破壞。柏拉圖批評道,在民主制度下,人們“稱傲慢為有禮,放縱為自由,奢侈為慷慨,無恥為勇敢”[3]561A。
綜上所述,正因為民主制違背了國家正義與個人正義原則,所以,柏拉圖對民主制(更具體而言就是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制)進行了猛烈批評,并將其放在寡頭制之后。菲爾德和薩拜因從國家正義的角度分析了柏拉圖將民主制放在寡頭制之后的原因。菲爾德認為,柏拉圖之所以將民主制放在寡頭制之后,一是因為它無原則和無目的,二是它阻礙卓越,使所有的人處于同一地位。[10]薩拜因指出,統治者的無知無能是柏拉圖極為厭倦的,而這正是民主國家特有的禍根。[11]巴克則從個人正義的角度分析了它的原因。巴克指出,在柏拉圖看來,寡頭政制、民主政制建立在兩種不同層次的欲望上。寡頭制依賴于生產的欲望;民主制除了依賴于生產的欲望外,還依賴于揮霍的欲望。[12]也就是說,寡頭政制下與民主政制下的人們雖然都追逐欲望的滿足,但寡頭政制下的人們追求的只是金錢和財富的囤積,而對于享樂則保持一定的節制;民主政制下的人們不但追求金錢和財富,而且追求金錢和財富的目的是更好地放縱欲望。
二、如何看待柏拉圖對民主制的批評
如前所述,柏拉圖指出了民主制之下統治者智慧低下、人們追求無限自由而導致社會失序、容易導致個人獨裁和專制統治、人們放縱欲望而缺乏美德等缺陷。在此要分析的是柏拉圖所批評的直接民主制是否真正具有上述缺陷。
統治者智慧低下被柏拉圖認為是民主制度的一大缺陷。這個觀點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在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制之下,公民都有參加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公民大會的資格,在公民大會上,他們決定著國家的重大事務。在古希臘時期,受到過良好教育的公民只是極少數,大多數公民并未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具有閑暇的公民也只是少數,大多數公民為了謀求生計,整日忙于勞作,沒有多少精力來考慮公共事務。所以,大多數公民缺乏治理國家的智慧。盡管公民并不經常參加公民大會,盡管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會參加每一次公民大會,但還是有相當多數的公民經常參加。當他們在公民大會上參與國家重要事務的決定時,由于缺乏相應的智慧,因而也就不具備作出正確判斷的能力。而且,他們往往受少數人的操控,那些善于煽情的少數人能夠左右多數人的情緒。同時,在雅典民主制下,公民大會之外的其他重要機構包括執政官、五百人會議議員(議事會議員)和陪審法官都由抽簽的方式產生,盡管抽簽并不是在所有公民中進行,盡管抽簽有一定的范圍限制,但這個范圍仍然是相當廣泛的。[13]這種做法確實體現了高度民主,但卻犧牲了專業化,導致政治決策和政治管理水平低下。這一點為諸多政治思想家所認同,例如,孟德斯鳩在討論古代共和國時說道:“古代的大多數共和國有一個重大的弊病,就是人民有權利通過積極性的、在某種程度上需要予以執行的決議。這是人民完全不能勝任的事情。”[7]189
為了改善統治者智慧低下的狀況,柏拉圖在《法篇》中對政治制度做了一個新的政制設計。首先,這個政制設計已不再是直接民主制,而成了間接民主制,體現直接民主的公民大會從中消失了。其次,執政官(包括執法官和將軍等)、三百六十人議事會、祭司、法官、市政官、市場專員、教育總監等機構除祭司由抽簽產生外,其余都由選舉產生。而且,多個職位在選舉時,又有等級的限制。柏拉圖劃分了四個等級,每個等級具有不同的權限。以三百六十人議事會為例,盡管三百六十人議事會是由四個等級各出90名代表組成,但每個等級議員的選舉方式不同,第一、二等級的議員由本等級的公民選出,第三、四等級的議員由全部公民選舉產生,第三等級議員的選舉第四等級可以放棄權利,第四等級議員的選舉三、四等級都可以放棄權利。除此之外,柏拉圖又將議事會的權力做了進一步集中,設置了輪值委員會,它從議事會中抽取1/12的人組成,主持議事會的日常事務。[4]753A-768E
民主政制下的過分自由會導致社會無序也被柏拉圖視為民主制的一大缺陷。毫無疑問,對于民主制度下的自由,柏拉圖進行了夸大的描述。無論是實行直接民主的雅典,還是近代以來實行代議制民主的國家,都沒有出現過像柏拉圖所描繪的那種過度自由的情形。實際上,柏拉圖描述的那種情形已經不是國家狀態了,而是一種無政府狀態。民主制度無論是直接民主制也好,還是代議制民主制也好,都是一種國家狀態,而不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民主制度也就不存在了。不過,在下列兩點上,柏拉圖是正確的。其一,過分自由會導致社會無序。如果一個社會中,人們擁有過度的自由,最后連法律都不放在心上,那么,整個社會將會失去規范,陷入一片混亂狀態。從柏拉圖的這點論述中,可以得到一點啟示,那就是一個優良的民主制度必須實行法治。只有實行法治,人們的過度自由才能受到限制。除了法律對人們自由的限制外,道德也是限制它的一種重要手段,它既包括外在的道德規范,也包括內在的道德品質。孟德斯鳩對后一點特別重視,將品德視為民主政體的原則。[7]23其二,民主制度下人們擁有的自由多于寡頭政制下人們擁有的自由。在同一時代中,無論是在直接民主制之下,還是在代議制民主制之下,人們擁有的自由都比在寡頭制之下擁有的自由多。之所以會如此,從根本上來講是因為自由是民主政制的必然要求,而對于寡頭政制來說可能就是危害統治的因素。
容易導致個人獨裁和專制統治被柏拉圖視為民主制的另一大缺陷。柏拉圖對直接民主制的這一批評也是有道理的。盡管在直接民主制下,每個公民都有參與公民大會決定國家事務的資格,但在政治參與上,多數公民一方面缺乏相應的熱情,因為自己還要忙于生計,另一方面也缺乏相應的理性與智慧。所以,多數公民在公民大會中處于消極被動的地位,盡管他們的態度決定著國家重大事務,但在很多時候他們中的相當多數人的態度并非出于自身審慎思考的結果,而是很容易受到群體其他人的影響,特別是受其中比較活躍的極少數人態度的左右。法國社會學家勒龐認為,群體心理具有易受暗示和輕信的特點。[14]在公民大會中,當有人進行極富煽動力的演說時,群體中就很容易出現躁動與狂熱。①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為人們展示了那些具有良好口才的人是如何在公民大會上進行煽動和控制群體意志的。參閱文獻[15]。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喪失了本來就不富裕的理性,成了極少數人意志的俘虜,從而為極少數人篡奪國家權力奠定了基礎。所以,盡管直接民主制度是多數平民的統治,但由于多數平民缺乏統治的能力,因此,國家最高權力最終很可能會落入到極少數人手中形成獨裁統治,而現實中的最高統治者又不具備哲學王所擁有的高度理性,因而其獨裁統治不可避免地導致專制統治。
其實,不僅僅直接民主制可能會導致個人獨裁和專制統治,代議制民主制也不能根除個人獨裁和專制統治。代議制之下的民眾同直接民主制之下的民眾在理性和智識上并沒有什么不同,他們的判斷能力同樣也較弱,他們往往為一些表面的東西所迷惑,從而作出錯誤的判決。米歇爾斯指出,在民主政體中,那些具有演說才能的人在公眾心中獲得了近乎絕對的優越地位。大眾欣賞的首先是演講者的口才,諸如聲音悅耳動聽、鏗鏘有力,才思敏捷而且風趣幽默,而演講的內容則是其次的。[16]所以,在代議制民主制下,極少數人可以通過煽動民眾來贏得競選的勝利,從而獲取國家最高權力并進而建立起專制統治。
人們放縱欲望而缺乏美德是柏拉圖批評民主制的又一個依據,也是柏拉圖認為寡頭制優于民主制的依據。柏拉圖對直接民主制的這一點批評值得商榷。古希臘的歷史表明,民主政體中平民的縱欲行為并不比寡頭政體中寡頭派的縱欲行為更嚴重,相反,由于寡頭派擁有大量的財富,他們的揮霍更厲害。在《理想國》中,寡頭派人物克法洛斯向蘇格拉底說起他們幾個寡頭朋友在聚會時的感言,都為不能像年輕時代那樣縱欲而感到遺憾。[3]329A筆者認為,民主制之所以給柏拉圖留下人們普遍縱欲的印象,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其一,在柏拉圖生活的時代,雅典長期處于民主政體下,所以,柏拉圖對民主制之下的社會風尚感受的更多,而對寡頭制之下的社會風尚感受的較少。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后,正是雅典人比較放縱欲望的時候。據記載,伯羅奔尼撒戰爭后,雅典再度興盛起來,商業獲得了高度發展,債券和支票在商業交易中廣泛流通。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導致了人們對金錢的瘋狂追求。希臘語不得不另創一個字Pleonexia來表示此種欲望的無止境。在美色的問題上,雅典人同樣表現得不節制。婚前的貞操只要求于有聲望的婦女,但是已成年的未婚男人,在性關系上甚少受道德的約束。盛大的慶典,雖然其起源是宗教性的,但卻成為男女私下茍合的好機會。放蕩的性關系得到寬恕,賣淫成為發達行業,同性戀現象非常普遍。[17]柏拉圖可能因此將人們的放縱歸罪為民主制。其二,在寡頭制下,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不但在經濟上比較貧窮,而且在政治上和社會中也備受壓制,他們即使想放縱欲望,也缺乏放縱欲望的條件。在民主制之下,盡管多數平民在經濟上仍然比較貧窮,但他們的社會地位提高了,在政治生活中也不再受到壓制,他們都具備參加公民大會的資格,而且抽簽制的實行使得部分平民獲得了擔任諸如執政官、議事會議員、陪審法官、市政官等重要職位的機會。這些職位在使他們獲取權力和提高社會地位的同時,也增加了他們的收入,這就為他們滿足欲望創造了便利的條件。其他暫時沒有獲得重要職位的公民因為抽簽制度也受到鼓勵,認為自己一旦獲得這些職位,自己的欲望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滿足。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可能會出現一種放縱的社會心理。
綜上所述,柏拉圖所批評的民主制是以古希臘雅典城邦為代表的多數平民統治的直接民主制。在柏拉圖批評的直接民主制的缺點中,雖然有些內容值得商榷,但其中還是有很多地方具有重要價值,并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產生了重要影響。
[1]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M].陸 衡,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2]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54-55.
[3]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4]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3卷[M].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M].閻克文,劉滿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6]佩迪特.共和主義[M].劉訓練,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7]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M].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8]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268-275.
[9]密爾.代議制政府[M].汪 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01.
[10]FIELD G C.The philosophy of Plato[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91.
[11]薩拜因.政治學說史[M].盛葵陽,崔妙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70.
[12]巴克.古希臘政治理論——柏拉圖及其前人[M].盧華萍,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44.
[13]馬嘯原.西方政治制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5.
[14]勒龐.烏合之眾[M].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24.
[15]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M].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16]米歇爾斯.寡頭統治鐵律[M].任軍鋒,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8-60.
[17]杜蘭.希臘的生活[M].幼獅文化公司,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340-341,217-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