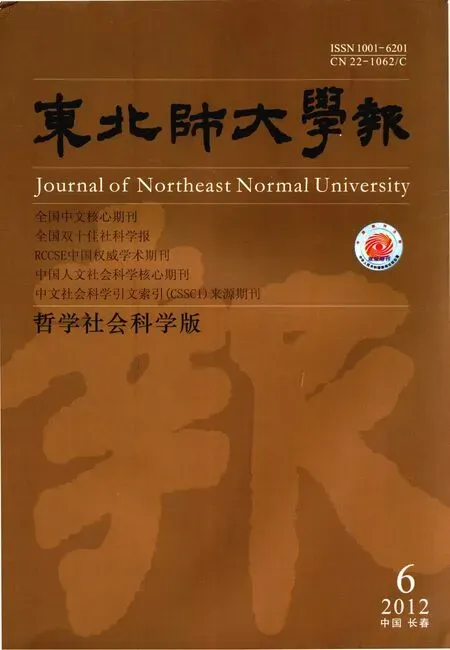秦遼東郡考述
林世香,苗 威
秦遼東郡是在戰國遼東郡的基礎上建立的,本文根據文獻和考古學資料,通過考察遼東長城的主線,力圖闡明秦遼東郡的變遷,同時對秦遼東郡諸縣的位置進行比定,以細化有關東北史的研究。
一、秦遼東郡的淵源
綜合《戰國策·燕三》以及《史記》、《資治通鑒》的相關記載,秦王二十五年(前222年),派遣王賁攻打襄平,虜燕王喜。次年,秦王最后滅掉了齊國,完成了統一大業。秦統一六國之后,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遼東郡是秦三十六郡之一,也是燕國舊制的延續。據《史記·周勃世家》載,當周勃追討燕王盧綰于長城時,“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但彼時遼東郡具體有多少屬縣,現在無從確知。秦之遼東郡應有所發展,史書所記“秦故空地上下障”應該即是其新拓之地。
在探討“秦故空地上下障”之前,應對秦代的“遼東長城”有相應的認識,而探討秦代的遼東長城,首先要廓清戰國“遼東長城”的走向情況。關于后者,學界的認識頗不一致,綜合起來,大致有如下說法。
其一,東端為古“襄平”或“遼東”說。持“襄平”看法的學者,多根據《史記·匈奴列傳》關于“燕亦筑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的記載,認為戰國時代燕國長城的東端僅到達古襄平(今遼陽市)境內,如劉全柱、羅哲文、陸思賢、張維華、王國良等皆持此說。有的學者雖未將燕長城的東端理解為襄平,但亦籠統地視為“遼東”或遼東某地。例如,張馭寰主張燕長城由“錦州延到遼東”;金毓黻認為燕長城東端“迄于遼陽之北”。其二,東端至“琿春”說。張博泉認為燕長城出阜新后,“經彰武、法庫而至遼河”,“再沿河北上至河之上游,又東北折至今吉林市北,東向至琿春濱海一帶。”其三,燕遼東長城“復線”說。閻忠認為燕長城有內線、外線之分,內線西段又分為東、西兩段,西段的東端經北票北、阜新北東行穿過遼水,“最后止于遼陽市老城北”,東段即是“大寧江長城”;外線經庫倫南、彰武北后,“又東北行,經梨樹北,又東南行,經新賓北、桓仁西,然后東至龍崗。”其四,“遼東長城”無復線說。李文信主張燕長城向東經彰武、法庫、開原一帶之后,“跨越遼河,再折而東南,經新賓、寬甸,向東至當時國境”。馮永謙對“襄平說”予以否定,主張燕北長城西段雖有復線(“赤北長城”、“赤南長城”),但遼東段卻僅有單線,認為在遼寧境內的走向是:由彰武東穿越遼河后,經鐵嶺市之北,東南行,越渾河上游,繞過蘇子河源,折而向南,經桓仁縣城之東,至寬甸太平哨和下露河而至鴨綠江邊,認為“大寧江長城”是遼東長城的最東段。蕭景全對張博泉、閻忠的說法予以否定,指出不能因發現二龍湖戰國城址就將長城劃到梨樹境內,同時對馮永謙關于長城東段說予以肯定,但對鐵嶺、沈陽、撫順地區長城障塞提出了新說①劉全柱:《萬里長城》,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9月版;羅哲文:《長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9月版;陸思賢,《長城話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張維華:《中國長城沿革考》(上編),中華書局1979年2月版;王國良:《中國長城沿革考》,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自然科技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金毓黻:《東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1年版;張博泉:《東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學出版社1985年11月版;閻忠:《燕北長城考》,《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第2期;李文信:《中國北部長城沿革考》,《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創刊號;馮永謙:《遼寧古長城》,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東北古長城考辨》,張志立等主編《東北亞歷史與文化》(慶祝孫進己先生六十誕辰文集),遼沈書社1991年12月版;《遼東地區燕秦漢文化與古長城考》,遼寧省考古博物館學會、本溪市文化局、丹東市文管會編《遼寧省本溪、丹東地區考研學術討論會文集》,1985年;蕭景全:《遼東地區燕秦漢長城障塞的考古學觀察研究》,《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從上述諸說來看,學者們在考察戰國遼東長城的走向時各有側重,其中的“襄平說”、“遼東說”以及“復線說”中對“內線”的認識,其主要根據是《史記》的相關記載,而“琿春說”則明顯證據不足。然而,這些說法皆有可商榷之處:
其一,明確夫余及其先人穢人與燕長城的關系。《三國志·夫馀傳》載:“夫馀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這里的“玄菟”應該是指玄菟郡治所的二遷址,即今撫順市勞動公園漢城(一說沈陽城東上柏官屯),這里到夫余王城(今吉林市)大致合古之千里。學界認為,以遼寧省西豐縣西岔溝墓地及吉林省遼源彩嵐墓地、吉林市帽兒山墓地為代表的考古文化是漢代的夫余文化[1]。雖然二龍湖戰國城址的內涵是燕文化,但周邊地區則為土著文化,其特征有似于西團山文化[2],可以理解是夫余—穢人的遺存。由此分析,二龍湖遺址不應在長城之內,而燕國的長城應在夫余與遼東郡的邊界之地,即松遼分水嶺一帶。
其二,明確高句麗及其先人高夷、梁貊與長城的關系。高句麗族初居富爾江流域,西漢昭帝時置高句麗縣,治所在今新賓永陵鎮蘇子河南岸的漢代古城。據《漢書·地理志》玄菟郡高句麗縣條云:“(高句麗縣)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意謂南蘇水(今蘇子河)在高句麗縣的西北,流經塞外。由此可見,向西流入小遼水(今渾河)的南蘇水是在長城之外而不是其內。因此,將燕長城的走向劃在蘇子河之北是不符合歷史典籍的。又《漢書·王莽傳》載:“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三國志·高句麗傳》亦載此事,并云:“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高句驪侯騶(朱蒙)入塞,斬之,傳首長安。”可知,高句麗是塞外之族[3]。如此分析,遼東長城自梨樹縣、西豐縣之南東來之后,應該在今撫順蘇子河口不遠處南折,跨越太子河(古大梁水,即衍水)中游繼續南下,進入寬甸縣境之后,沿北股河至太平哨,再經大西岔附近隔江與“大寧江長城”相望。
戰國遼東長城的走向明確之后,秦代遼東長城的問題亦迎刃而解。《史記·匈奴列傳》載:“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筑四十四縣城臨河,徒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陽,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余里。”學界公認秦代的萬里長城是將戰國時魏、趙、燕的北方長城連接起來,并加以修葺而形成的。僅就遼東長城而言,秦人在燕人的基礎上,又將東段戰國長城段向南延伸了一段,這就是學界所稱的“龍崗”段。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資料,戰國長城暨秦長城進入遼東山地以后,其走向基本清晰,原有的不確分析將隨之消弭。
二、秦遼東郡的遺跡遺物及其轄縣
秦朝經營遼東郡的時間僅有16年,遺跡遺物比起戰國及兩漢要少很多,但從目前已有發現來看,可以說明秦曾經經營過這里。
(一)長城及附近地區
20世紀80年代初,遼寧綏中萬家鎮南部海邊發現大型秦代建筑遺址及窯址。經多年發掘驗證,此系秦始皇東巡的行宮,應該是秦代經營遼東的實證。早年平壤曾出土鑄有二十多個秦篆的“二十五年上郡”鐵戈[4],遼寧省寬甸縣小柱房村遺址出土過刻有公元前209年“丞相李斯造”銘文的銅戈[5],應與秦長城戍守相關。遼寧省桓仁縣大甸子村抽水洞遺址出土過秦半兩錢[6],撫順城區李石寨鎮河東村發現4件戰國青銅兵器,其中一件刻有“三年相邦呂不韋造”的“上郡守”銅矛[7]。沈陽東陵區上柏官屯古城址中曾采集到一件刻有秦篆“廿六年”字樣的陶器殘片,上柏官屯古城被認為是戰國至秦的遼東重鎮[8]。這些秦代文物的發現,為秦人經營遼東提供了實物資料。應當說明的是,撫順、遼陽、沈陽所發現的上述遺址遺物,皆在秦長城之內。彼時這三個地區自戰國至秦漢,人煙比較稠密,交通發達,經濟繁榮,不應是邊塞之地,長城故燧應遠在其東部地區。
(二)其他地區
新金縣后元臺出土魏國的“啟封”銅戈,其正、背兩面都刻有“啟封”二字。正面“啟封”二字和其他銘文是三晉文字,而背面“啟封”二字則是秦篆。根據銘文可知,此戈鑄于魏安厘王二十一年(前256年),后被秦繳獲,加刻秦篆“啟封”二字。秦于公元前225年滅魏,前222年滅燕,此戈應該是秦軍在滅燕或戍守遼東半島之時使用的兵器。
普蘭店市花兒山鄉張店城址之西出土一方“臨薉丞印”封泥,年代在戰國至秦之間。“臨薉”應是縣名,“薉”與“穢”通,應是以穢人居住地命名的,但“臨薉縣”不見漢籍,可視為秦朝遼東郡失載的屬縣。
秦遼東郡的轄縣史無明載,有關地理、地望要素的考證已有很多成果可以參考,但更多的是漢代典籍對所轄行政建制的記錄。
西漢沿襲秦代舊制,其轄區以及所設置的屬縣有所變化。西漢時期已經放棄秦“上下障”之地,使遼東郡的轄區有所縮小。《漢書·地理志》載:遼東郡,秦置,屬幽州。屬縣有襄平等十八個:襄平、新昌、無慮、望平、房縣、侯城、遼隊、遼陽、險瀆、居就、高顯、安市、武次、平郭、安平、沓氏、文縣、番汗。漢代遼東郡收縮的情況,可以從“臨薉丞印”的發現得到驗證。
綜上,通過對遼東長城主線的考證,明確了秦代遼東郡的歷史變遷軌跡,對于東北邊郡的深入探討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1]田耘.西漢夫余研究[J].遼海文物學刊,1987(2):122.
[2]四平地區博物館,等.吉林省梨樹縣二龍湖古城調查簡報[J].考古,1988(6):512.
[3]劉子敏.“高句麗縣”研究[J].東北史地,2004(7):15.
[4]馮家升.周秦時代中國經營東北考[A].李健才.東北地區燕秦漢長城和郡縣城的調查報告[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77:183.
[5]許玉林,王連春.遼寧寬甸發現秦石邑戈[J].考古與文物,1983(3):19.
[6]孫守道.漢代遼東長城列燧遺跡考[J].遼海文物學刊,1992(2):23.武家昌,王俊輝.遼寧桓仁縣抽水洞遺址發掘[J].北方文物,2003(2):27.
[7]許家國,劉兵.遼寧撫順市發現戰國青銅兵器[J].考古,1996(3):86.
[8]佡俊巖.沈陽上伯官漢墓清理報告[J].遼海文物學刊,199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