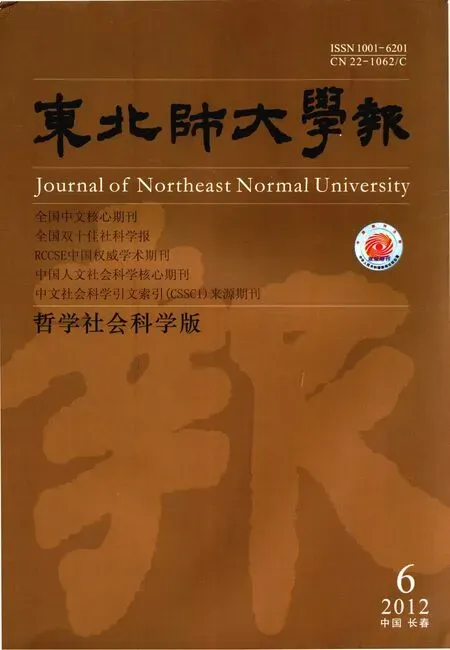“德國裁軍與非軍事化條約”與冷戰的緣起
李鳳艷,王 彥
(東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史學界傳統觀點認為德國并不是使東西方對峙加劇的原因,而是它們之間關系惡化后的主要戰場[1]22。這樣的論斷有失偏頗。戰后初期,在德國,美蘇之間圍繞著“德國裁軍與非軍事化條約”的互動,集中體現了兩國在全球及德國的戰略目標具有不可調和的對抗性,是導致雙方改變對德政策,即由抑制德國轉向拉攏德國以對抗對方的根由。本文擬通過對俄美兩國檔案的解讀,重現蘇美之間圍繞該條約的互動過程,探求條約流產原因及其與冷戰爆發的關系。
一、美國另訂新約的提議與蘇聯的回應
大國之間承擔責任、簽署一項保證德國長期處于非軍事化狀態的條約,最早是由美國參議員范登堡在1945年1月初提出來的[2]126-145。蘇聯對范登堡的提議給予了強烈批評。3月,在《戰爭與工人階級》雜志上登載了一篇署名為索科洛夫的文章,題為《范登堡參議員與他的路線圖》。文章認為“德國非軍事化”(д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Германии)一詞是空洞的、模糊的,是用以掩飾一個大國對其他所有大中小國家進行控制的謊言,并詰問“為什么那些承擔了反抗希特勒德國全部重擔的大小國家,包括強國,現在應為美國參與世界事務而放棄本國的自主性。”[3]19-23文章體現了蘇聯對美國可能主導歐洲事務的警惕和抵制,同時也體現了蘇聯將恃功在戰后歐洲發揮重要作用的決心。
1945年7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形成了一套全面的對德政治經濟原則,被人們簡稱為“四化”方針,即“非軍事化”、“非納粹化”、“非卡特爾化”和“民主化”,此外,德國要對戰爭受害國進行賠償。關于非軍事化規定:解除德國全部武裝,使之完全非軍事化,鏟除或控制可用作軍事生產的一切德國工業,同時規定了為達到這些目的將采取的具體措施[4]508-509。這些原則成為盟國對德進行改造的法律依據,也是蘇美英合作的基礎。
但不久美國就另起爐灶。9月20日,倫敦外長會議期間,國務卿貝爾納斯首次正式向莫洛托夫提議就蘇美英法四方簽訂一項保障德國非軍事化的條約進行協商,在美蘇之間先達成共識之后,再吸收英法參加。貝爾納斯的提議與范登堡的提議并無二致,言稱簽署這一條約旨在防止德國重新武裝、滿足蘇聯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5]234。
對于這項提議,斯大林斷言美國意在對抗蘇聯,具體目標有四個:“一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從遠東移開,在那里美國把自己表現得像是日本未來的朋友,并以此造成一種印象,即在遠東一切安好;二是要蘇聯接受美國在歐洲事務中發揮與蘇聯同樣的作用,以便將來通過與英國結盟控制歐洲;三是使蘇聯與歐洲國家已經簽訂的同盟條約失去意義;四是使蘇聯將要與羅馬尼亞、芬蘭等國簽訂的同盟條約失去其指向。”他指示莫洛托夫:爭取簽署類似的對日條約作為接受美方提議的條件[6]74。
此后,莫洛托夫、斯大林先后在與貝爾納斯的會談中都重申了以簽訂對日類似條約作為接受美方提議的前提條件的立場,而貝爾納斯表示接受這一條件。但索科洛夫的文章和斯大林的電報表明蘇聯是從整個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新格局的角度而非單純的德國非軍事化問題揣度美方動機的,認為美國是在謀求歐亞大陸的主導權,排擠蘇聯,而蘇聯要通過強調德國威脅的存在作為其在歐洲建立和擴大勢力范圍的借口,并據此與美國爭奪歐亞大陸主導權。正如副外長李維諾夫所說:“既然我們的安全得到了保障,那我們的行為和要求就失去了合理性,正是因為這些行為和要求,我們和西方國家之間出現了分歧。”[5]517也就是說,安全并非蘇聯所追求的唯一目標,更是其謀求擴張的借口,為此不惜冒與西方、與美國關系惡化的風險。在此背景下,蘇聯以簽訂對日非軍事化條約作為接受美國提議的條件,意在一箭雙雕,在不動搖歐洲雅爾塔體制的前提下,爭取參與對日本的占領與管制。
二、美國的條約草案與蘇聯的對策
1946年2月14日,美國駐蘇使館參贊喬治·凱南將“德國裁軍與非軍事化條約草案”交給了莫洛托夫。草案由序言和五項條款構成,規定了制定此條約的目的及擬采取的措施。序言言明了簽約目的:有關德國裁軍計劃已基本完成,但為世界和平和安全,仍需進一步加強。第一條列舉了禁止德國擁有的各種武裝力量、軍事機構和組織、軍事裝備及與這些裝備的生產相關的場所、設施、技術等。這與波茨坦公報中的規定沒有實質差別。但該條d款規定的應阻止在德國制造、生產或進口的軍事裝備中增加了“為任何目的的所有可裂變材料,經各締約國批準的除外”一項;第二條規定成立一個四方檢查委員會,負責對第一條中有關規定的執行情況進行檢查,這種機制在盟軍結束對德占領之后開始運行;第三條的核心是“德國明確接受本草案第一和第二條應是盟軍終止對德占領的基本條件”;第四條規定檢查委員會的決策方式為多數同意原則;第五條規定條約的批準和生效方式,有效期為25年。[7]190-193
蘇聯方面對草案初步分析,認為美國的動機是提前結束占領,這就意味著對德國的各項改造將半途而廢,蘇聯也將難以獲取賠償,因而是不能接受的[5]369-371,452。故巴黎外長會議期間,4月28日在與貝爾納斯會談時,莫洛托夫指責其所提議的條約旨在推遲解決德國非軍事化問題,這使貝爾納斯十分惱怒,30日,將草案作為會議正式文件分發給了蘇英法三國代表,并在報紙上全文公布。
草案一經公布,就在西方引起了強烈反響。記者們敏銳地意識到美國這是投石問路,如果蘇聯拒絕,就意味著它所追求的并非是正當的安全利益,而是謀求擴張[5]77。德國西占區各派政治力量則歡欣鼓舞,他們把此項提議看成是美英改變對德政策的標志,盟國的占領將提前結束。與此同時,西占區包括西柏林的反蘇勢力借此大肆進行反蘇、反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宣傳。這使蘇聯陷于被動。在東西方對抗格局初露端倪的背景下,這一問題的復雜性和敏感性,促使蘇聯高層進行深入研究。
參與研究條約草案的蘇聯官員,包括了十幾位國家高層領導人,這在蘇聯對外政策決策史上是十分鮮見的。他們都對美國的提議感到困惑不解,因為條約草案所列舉的各項非軍事化措施,在波茨坦會議公報中都做了具體規定,德國無條件投降就意味著其已接受了這種改造。而且,這些措施也將是未來將簽署的對德和約的組成部分,沒有任何理由重新審議這一問題,也沒有必要擬制一項專門條約。這些人分析美國的動機主要有以下七個方面:
一是縮短占領期限。依據是草案中關于裁軍計劃“已經基本完成”和“德國接受第一、二條是結束盟國占領的必要條件”這樣的表述,而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美國希望縮短占領期限,加里寧認為這是擔心蘇聯的占領將使德國民主化,而朱可夫認為美國是希望促使蘇聯從德國、繼而從波蘭和巴爾干撤軍;二是阻止蘇聯獲取賠償;三是放松對德國的管制。因為相對于盟國管制委員會來說,擬成立的檢查委員會更沒有權威性,更沒有能力將德國非軍事化進行到底;四是削弱蘇聯對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影響。因為擬成立的檢查委員會根據多數同意原則做決策,而美英與其他國家之間正在形成同盟關系,這將使蘇聯在德國所采取的措施置于美英的監督之下;五是放棄對德的軍事和經濟改造,保留德國的強國地位。因為草案的非軍事化措施沒有包括全面銷毀德國可用于軍工生產的工業及德國和平工業所不需要的生產能力,一旦放松監管,德國大量的各類專家很快就會將這些企業發展成新興工業的基礎,德國就將復興為一個軍事經濟強國;六是加快德國復興,使其成為資本主義基地和對抗蘇聯的堡壘。結束占領,將為美英資本進入德國創造條件,這就為反動勢力在整個德國的鞏固提供了可能,不久就會爆發美英德針對蘇聯的戰爭;七是重新審議盟國協商一致通過的所有關于德國的決議。
關于應采取的對策,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主張直接拒絕。理由是:簽訂這樣的條約有悖于先前達成的協議,由檢查委員會取代盟軍對德國的占領為時尚早;另一種意見認為直接拒絕不妥。這會授人以柄,為英美進行反蘇宣傳提供口實,會使德國民眾產生敵視蘇聯的心理,主張在德國所有占領區對波茨坦決議的執行情況進行檢查,以進一步揭露美英兩國背離該決議的行為,同時建議對條約草案進行修改和補充,前提條件是必須就繼續保持四國對德占領達成一致[5]574-582。莫洛托夫采用的是第二種方案。
三、條約流產與蘇美對德政策的調整
就在蘇聯國內仍在對貝爾納斯條約草案進行研究的時候,在4月28日與貝爾納斯會談時,莫洛托夫指責美方提議簽訂的條約旨在推遲解決德國非軍事化問題,但表示原則上支持簽署這樣的條約,條件是對日本也簽署類似條約,并建議由盟國管制委員會組建一個專門委員會,對各占領區的裁軍情況進行檢查。貝爾納斯否認莫洛托夫的指責,重申簽訂此項條約的目的是為了使德國的非軍事化狀態至少保持25年,這可以幫助法國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時,也將向全世界表明,蘇聯謀求的確實是自身安全而非擴張。貝爾納斯表示美國政府準備簽署對日類似條約,并同意立即組建一個委員會檢查有關德國裁軍決議的執行情況[5]427。這是貝爾納斯第一次明確表示,他的提議有試探蘇聯外交意圖的用意。
對于這次會談,斯大林批評莫洛托夫沒有揭露美國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奉行擴張主義政策[5]794。故在5月5日的會談中,莫洛托夫幾乎一字不差地重復了斯大林的用語。貝爾納斯對此予以否認,并反問莫洛托夫:如果蘇聯謀求保障國家安全而不是擴張,為什么要在境外保持大量駐軍,為什么不接受美方提議[5]475-478。兩人的交鋒道出了美蘇由戰時合作走向冷戰對抗的根本原因,即兩國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所導致的碰撞,在德國非軍事化問題上立場相悖是這種碰撞的一個縮影。
5月13日,在巴黎外長會議非正式會議上,莫洛托夫再次提議成立一個四方檢查委員會,被三國代表接受。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蘇聯的立場很快就發生了變化,5月20日拒絕了美國提出的關于成立一個負責檢查德國經濟非軍事化分委會的提議,理由是“在尚未制定賠償計劃和拆遷軍工廠計劃的情況下,這種檢查將是對世界輿論的欺騙。”[5]79。顯然,這樣的理由即牽強又令人費解,因為蘇聯一直主張對各占領區經濟非軍事化情況進行檢查,認為這種檢查有助于揭露西方未誠意履行波茨坦會議決議。
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蘇聯出爾反爾,主要是擔心西方專家會借機掌握蘇占區內正全力開展的鈾開采和加工情況。而在美國提出的條約草案中,規定應阻止在德國制造、生產或進口“為了任何目的的所有可裂變材料”,盡管有“經各締約國批準的除外”這種例外。蘇聯忌憚簽署這樣的條約將使自己在蘇占區的鈾開采和加工項目置于西方的監督之下。而且,在美國應蘇聯要求而提出的“對日裁軍與非軍事化條約草案”中沒有此項規定,這不免使蘇聯對美國的動機心生疑慮[5]518。而此時,美國正在努力維持其核壟斷地位,聯合國也開始討論對原子能的國際監管問題。所以,規避“核限制”是蘇聯拒絕貝爾納斯條約草案的原因之一。
1946年7月9日,莫洛托夫在巴黎外長會議上宣讀了一份關于貝爾納斯條約草案的公開聲明。聲明認為草案所規定的預防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措施不充分,必須對草案進行徹底修改[5]807,而貝爾納斯則認為沒有修改的必要[7]847-848,蘇美之間圍繞著這項條約的互動走進了死胡同。1947年初,條約草案又被列入了莫斯科外長會議的議事議程。莫洛托夫重申了蘇聯不能接受美國提議的原因,并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歸納而言,就是:盟國承擔責任對德國實行全面的“四化”改造,條約有效期為40年,在其有效期內,保持盟國對德國的軍事占領。顯然,這與美國擬借非軍事化條約結束對德軍事占領、促使蘇聯撤軍的初衷相悖。而且,不論是國際大背景還是德國局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進一步討論的環境和基礎都不存在了,美國對莫洛托夫提出的修改意見未作回應,貝爾納斯條約胎死腹中。
蘇聯對德政策的調整體現在莫洛托夫于7月10日在巴黎外長會議上所宣讀的一份題為《關于德國的命運與對德和約》的綱領性文件中。文件闡述的對德政策,可以概括為三原則:政治獨立,領土完整和無障礙地發展和平工業[8]67。這表明蘇聯不再謀求分裂和削弱德國,而是在保證其和平發展的前提下,“使其成為統一、民主、愛好和平、擁有發達工農業和對外貿易的國家”[5]808。在貝爾納斯看來,這則意味著蘇聯的對德政策發生了危險的“轉折”,旨在拉攏德國并把其變成自己的盟友以對抗西方[9]181。相應地,美國也開始轉向利用德國對抗蘇聯,其標志是1946年9月6日貝爾納斯在德國斯特加特發表的演說。演說中,對蘇美關系最具殺傷力的是他聲稱將努力最終確定德國的東西部邊界[5]817。這是美國首次提出要修改雅爾塔會議所確定的德國邊界,包括東部的奧德-尼斯河邊界。在蘇聯看來,這意味著美國背離了雅爾塔會議協議,蘇美之間在德國進行合作的基礎也就不存在了。這次演說是“戰后美國與其前敵國(至少是德國的西半部)和解的歷史開端”[10]491,同時也是蘇美在德國問題上由合作走向對抗的開端。
通過對俄美兩國檔案的綜合性分析,重現蘇美之間圍繞貝爾納斯條約草案的互動過程,可見蘇美兩國都贊同解除德國武裝并對其進行非軍事化改造,但對于“非軍事化”一詞的內涵與范疇理解不同。美國是從單純的軍事意義來框定“非軍事化”的,試圖通過解除德國武裝、由美蘇英法簽署保障德國長期處于非軍事化狀態的條約防止德國再次威脅歐洲安全,并藉此遏制蘇聯的擴張。而蘇聯則從廣義上來理解和操作,即不僅包括純粹軍事意義上的解除武裝,還包括解除德國的經濟武裝,即消滅德國維持其基本生存所不需要的經濟力量、消滅德國的經濟壟斷組織;而且,作為化解德國威脅的手段之一,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其他領域的改造相輔相成。所以,蘇聯謀求一攬子的、全面的對德改造,而在蘇聯看來,沒有盟國對德國的直接占領,這些目標都將成為空中樓閣。但這都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蘇聯拒絕美國提議的根本原因是要保持對德占領,使德國成為維系和擴展蘇聯勢力范圍、抵制美英主導歐洲事務的基地,這一動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國在未來調整了有關歐洲的戰略思想[11]。總之,蘇美之間圍繞著條約草案的互動充分顯示了兩國的對外戰略目標具有無法調和的對抗性,條約流產是兩國在德國問題上走向冷戰對抗的一個關節點,盡管不如在伊朗和土耳其海峽地區那樣激烈。
[1][美]沃捷特克·馬斯特尼.斯大林時期的冷戰與蘇聯的安全觀[M].郭懋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22.
[2]Arthur H.Vandenberg.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D].Boston.1952.
[3]СоколовА.СенаторВанденбергиегосхема[J].Войнаирабочийкласс.1945(5).
[4][蘇]薩納柯也夫,崔布列夫斯基.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Z].北京:三聯書店,1978.
[5]П.Кынини Й.Лауфет.CCCPигерманский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архивавнешней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M].T.2.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2000.
[6]ПечатновВ.ПерепискаСталинасМолотовым[J].Источник.1999(2).
[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VolumeⅡ[EB/OL].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2011-06-20.
[8]А.М.Флитов.Германскийвопрос:расколакобъединению[M].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1993.
[9]Byrnes.J.Speaking frankly[D].New York,1947.
[10]Roger Morgan.Washington and Bonn:A Case Study in Alliance Politics[J].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1971,47(3).
[11]劉文山.冷戰后尼克松有關歐洲的戰略思想論析[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8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