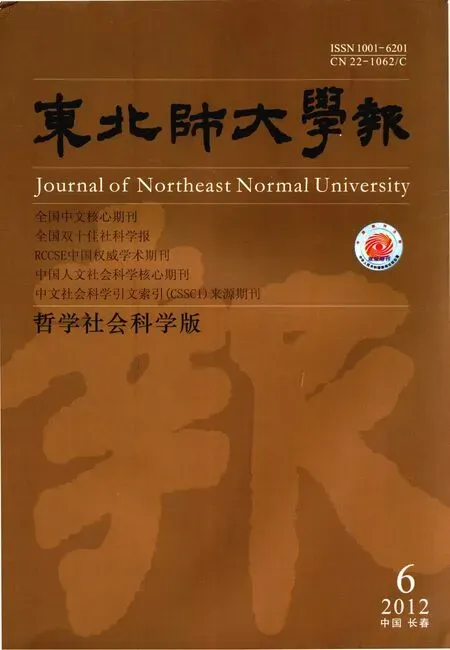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與中古漢語音韻對應規律研究
劉富華,趙世海
(1.吉林大學 國際交流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2.吉林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日語語音體系中原本沒有長音。長音是在吸收中古漢語音韻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這已成為學界共識。如史存直的“至于長音、拗音、拗長音和促音、撥音,則都是在和漢語接觸后逐漸發展出來的,雖不能說盡處于漢語的影響,但不妨說主要出于漢語的影響”[1]的觀點。中田祝夫同樣認為拗音、長音、撥音、促音“這些語音作為日語音韻固定下來是在平安時代末期,其產生和確立都受到漢字音的強烈影響。”[2]
“‘既然世界上的語言沒有一個是新產生的,既然它們的結構和系統都有其歷史背景,那么各個語言共時態里所見到的各種規律性和非規律性,應當說都是歷史變化的產物。’顯然,我們可以將空間橫向的方言土語看做是語言在時間縱向上的展開。”[3]所以我們通過對比中古漢語和同一時期的古代日語,以及對比古代日語和現代日語,完全可以找出它們之間的對應規律,并能探明中古漢語語音系統對日語語音系統的影響。
一、日語長音的產生和發展
日本學者筑島裕把長音定義為同一元音音素的連續[4]。所謂長音實際上就是由兩個元音組合而成的。這種元音組合在公元8世紀即奈良時代以前只是少量出現在日本古地名和感嘆詞中,但不能據此認為奈良時代以前的古代日語中長音就已經存在。
既然長音不是日語固有音,那么它就應該是受外來語音傳入影響而形成的。在奈良時代中國的漢字伴隨著漢文書籍傳入日本,學習漢字字音成為必須。此時的漢字讀音基礎是“吳音”(大約在公元6世紀傳入)。但是漢語的語音體系不同于日語語音體系,漢語中的一些音韻在日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要想吸收漢字字音,就得改良日語固有語音。長音就是吸收了漢語復合韻母的特點,結合日語語音規律,新增加的語音形式,并歷經時代變遷及古代中國各朝代語音影響才發展成現在的樣子。
那么,長音是怎樣吸收漢語復合韻母的特點產生的呢?
首先,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多以“い”、“う”結尾。因為“い”、“う”的發音近似于漢語復合韻母中的韻尾[i]、[u],在音節中的位置比其他元音相對自由。
奈良時代以前單個元音一般不獨立使用在詞頭以外的地方[5]。如果以“い”、“う”轉寫漢語復合韻母的韻尾,那么它們必然要出現在詞中或詞尾,這是日語固有語音體系不允許的。但是“い”、“う”有些例外,它們可以偶爾單獨出現在詞中或詞尾處。正是有這樣的語音基礎,它們才被用來轉寫漢語復合韻母。而一個新的語音若想在舊的語音體系中固定下來,必須有舊的語音體系的類似語音基礎支撐,否則它無法被舊的語音體系吸收。長音也是如此,如果沒有一定的日語語音基礎(例如感嘆詞中的類似長音的語音),它是不會在日語語音體系中形成的。
其次,奈良時代以前的中古漢語陰聲韻音節末尾是[i]、[u]的情況不少,又多是兩個或三個元音結合的復合韻母。
日語的5個元音只能單個使用,不能結合使用,而且中古時期的日語音位比漢語音位少,所以如何轉譯漢語中諸如復合元音、鼻音韻尾以及入聲韻尾等復雜韻母就成為古時日本人難以解決的問題。于是在不動搖日語固有語音體系基礎上,只用一個音位轉譯多個漢語音位,實在不行就增加音位。而長音就屬于一對多的情況。例如,以“い”對漢語的[ǐ?i]、[ei]、[ɑi]等的韻末音[i],以“う”對[ou]、[u]、[iu]、[ao]等的韻末音[u]和[o],形成這一時期的長音。漢語的鼻音韻中的[o?]、[u?]、[a?]、[e?]、[??]的韻尾[?]以“い”或“う”轉譯成長音。
此外p尾入聲韻也轉譯成了長音。它的演變過程是:開始以“ふ”表記,后來一部分與“う”混同成為“う”尾長音,最后形成“お”段長音,另一部分形成拗長音。例如,“納[nap]”等經過ナフ→ナウ→ノー([nafu]→[nau]→[no:]),形成長音;“給[kip]”等經過キフ→キュー([kifu]→[kyu:]),形成拗長音。
二、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與中古漢語陰聲韻、[?]尾陽聲韻、[p]尾入聲韻對應規律
從以上分析可知,日語長音是在吸收和改造漢語復合韻母后形成的。從其形成來源看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1.韻末為[i]的復合韻母形成“い”尾長音;
2.韻末為[u]或[o]的復合韻母形成“う”尾長音;
3.鼻音韻尾為[?]的復合韻母形成“い”尾長音或“う”尾長音;
4.入聲韻尾為[p]的復合韻母先形成“ふ”尾長音,后轉為“う”尾長音。
為了更清楚地顯示漢語語音對日語長音形成的影響,下面以《廣韻》和日語吳音、漢音兩種譯音對照,找出它們之間的對應規律。之所以選擇《廣韻》,是因為《廣韻》雖然是北宋早期的一部韻書,但它是在唐代《唐韻》的基礎上增訂、重修而成的,而《唐韻》又是在隋代《切韻》的基礎上增修而成的[6]。南北朝時期的南方語音體系和唐代的北方語音體系也應當包含在《廣韻》中。日語吸收的吳音對應南北朝時期的語音,漢音對應唐朝語音,所以《廣韻》適合與日語語音對應。
從以上長音形成來源看,一種是中古漢語陰聲韻末尾為[i]、[u]、[o]的音韻;另外兩種來源是中古漢語陽聲韻和入聲韻。它們與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形成整齊的對應關系。具體對應規律如下:
1.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與中古漢語陰聲韻末為[i]的音韻的對應規律——祭部的三、四等韻與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相對;
2.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與中古漢語陰聲韻末為[u]的音韻的對應規律——豪部的一、二等韻和侯部一、三、四等韻與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相對;
3.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與中古漢語陽聲韻的對應規律——[?]韻尾的陽聲韻與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相對;
4.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與中古漢語入聲韻的對應規律——[p]尾入聲韻與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相對。
三、中古漢語復韻母形成日語長音的音韻學上的解釋
(一)中古漢語陰聲韻形成日語長音的解釋
中古漢語陰聲韻中以元音[i]和[u]為結尾的漢字音形成日語長音,但不是所有的韻部都形成日語長音,具體如下:
(1)韻末為[i]的陰聲韻
祭部里的漢字音融入日語后成為長音,但并不是祭部所有的漢字音都轉譯成了長音,只有其中的開三[ǐ?i]、開四[i?i]和合三[ǐu?i]、合四[iu?i]中漢字音形成了長音。由于日語中不存在介音音節,所以直接以輔音加元音轉譯。開三和開四中的[?i]是復合元音,必須以兩個元音對應,于是日語以“エイ”對譯。例如“雞”在中古漢語中讀作[ki?i],進入日語后,[i]介母脫落成[k?i],表記為“ケイ”。而合三和合四的[u]介母卻沒有脫落,因為日語中有對應的[u]音,所以把[ǐu?i]和[iu?i]轉譯成“ヱイ”,讀作[wei],它屬于唇音,來對應[u]含介音復元音。后來日語唇音逐漸消失,到江戶時期“ヱ”變為“エ”,這樣合三、合四與開三、開四都轉譯成“エイ”,不再區別。
漢語復合韻母中韻腹[?]是主要元音,韻尾[i]是次要元音,所以轉譯成日語“エイ”時,“エ”自然也成為主要元音,“イ”成為次要元音[7]。日語的“エ”和“イ”發音部位相同,只是開口度稍大于“イ”。而且由于[?i]是前響復合元音,發音特點是開頭的元音素響亮清晰,收尾的元音音素輕短模糊,收尾的[i]只表示舌位移動的方向,所以整個音節的音色是漸變的,[?]與[i]之間的分界是模糊的。然而日語即使是兩個元音相連時也是界限分明的,由[e]到[i]不是滑動的而是瞬變的,所以最初[?i]進入日語轉譯成“エイ”時,“エ”和“イ”是分離而獨立的。
但是兩個元音并列共同成為一個音節的核心只是存在于最初的一定時期內,日語固有語音體系也不“允許”這種外來語音的長期存在。在中古漢語復合元音的發音特點的影響下,日語轉譯音“エイ”中的收尾元音“イ”不再保持獨立地位,逐漸向主要元音“エ”靠攏并融入到“エ”中,這樣就由兩個元音變成了一個元音,但是原來“イ”如同中古漢語的復合元音中的韻尾[i],不能完全消失,還保留著原來一拍的時間,所以需要把“エ”延長一拍。這個延長了的音就是長音。即“エイ”→“エ-”,從而完成長音的演變。“イ”向“エ”靠攏形成現代長音完成于江戶時期[8]。
(2)韻末為[u]的陰聲韻
豪部的開一[au]和開二[ǎu]形成的是長音,豪部的開一和開二的漢字音日語都轉譯成“アウ”。由于豪部開一和開二中的[a]和[ǎ]是主要元音,[u]是次要元音,所以日語中的“ア”也是主要元音,而“ウ”成為次要元音。[au]也屬于前響復合元音,在日本人聽來象日語元音“オ”,因此,日語譯音的“アウ”為對應漢語豪部的發音,逐漸同化成一個元音“オ”。先是韻尾“ウ”受到前面主要元音“ア”的同化,口腔由閉轉開,形成開音[?]與[a]“ア”對應。即“アウ”→“アオ”。“ア”和“オ”發音部位相同,都屬于后低元音,只是開口度稍不同,這樣二者具備了合并的基礎。為了保持以一個元音為核心的日語固有語音體系的特點,[au]的日語對譯音“アウ”最終合并成一個元音“オ”,并延長一拍來保證原來兩個音的時值。例如“考”由最初的“カウ”變為“コー”形成“オ”段長音。即[kau]→[kao]→[ko:]。
侯部的開一[ou]日語轉譯成“オウ”,屬于前響復合元音,侯部的[o]也是主要元音,韻尾[u]是次要元音。為保證譯音與漢語原音相對應,“ウ”逐漸失去獨立地位向“オ”靠攏,最后被同化。兩個元音雖然變成了一個元音“オ”,原來的兩個音的時間還要保持,于是“オ”被延長一拍形成長音。例如“侯”就是由“コウ”變為“コー”形成“オ”段長音。即[kou]→[ko:]。
侯部的開三[ǐou]和開四[iou]的漢字音中的一部分形成了日語長音。它們的形成規律如下:
1.現代漢語聲母為[y]的字,如尤、郵、憂、由、游、有、又、幼、幽等,進入日語后形成長音。
因為這些字音在魏晉南北朝音系中屬幽部合三,王力擬測音值為[ǐu],日語譯音只能表記為“イウ”,這樣才能與漢語原音完全對應。后來幽部合三漢字音在中唐音系中演變為侯部開三和開四,擬測音值分別為[ǐou]和[iou]。又由于幽部合三的漢字音的聲母都屬于喻四[j],與日語ヤ行的輔音[j]相對應。受到漢字原音發生變化的影響,日語漢字讀音自然也發生變化,由イウ[iu]逐漸演變為ユー[ju:],最終形成長音。
2.現代漢語聲母為[f]的字,如,婦、否、副、富等,日語輔音中也有[f],于是譯音與原音相同形成[fu:],日語漢音表記為長音“フー”。
(二)中古漢語[?]尾陽聲韻形成日語長音的解釋
中古漢語輔音韻尾的“ng[?]”在中古日語中轉譯成“ウ”尾或“イ”尾長音。從音節構成因素的性質看,中古漢語的輔音韻尾的陽聲韻和塞音韻尾的入聲韻屬于閉音節,而中古日語音節都是元音韻尾。因此,在對譯漢語鼻輔音韻尾[?]時,日語仍保持著自身的這一特點,把輔音韻尾[?]轉換成元音韻尾[u]或[i],并延長一拍而成為兩個音節。
ng陽聲韻尾之所以形成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與中古漢語的演變規律有一定關系。上文提到,日語長音實際上就是將日語單元音延長一拍從而變成兩個元音,以對應中古漢語的復合元音。由于[?]為輔音韻尾,日語以元音對譯,并不只是由于古代日語音系中不存在輔音韻尾,還因為“漢字音的輔音韻尾逐漸消失和鼻韻尾的簡化是漢語西北方音自身發展演變的規律或趨勢。西北方音即隋唐音,也就是中古時期進入日本的漢音。在漢音的這種演變制約和影響下,日語才以元音韻尾對譯漢語[?]韻尾字音。”[9]日語將中古漢語陽聲韻輔音韻尾ng以元音對譯后,就使得原陽聲韻除了主要元音外又多了個元音,從而形成長音。例如東字的中古音為[tu?],日語以[o]對譯中古音[u],并以[u]對譯韻尾[?],于是東字的日譯音為[tou],[u]融于[o]后形成長音[to:],日語表記為とう。
(三)中古漢語入聲韻形成日語長音的解釋
中古漢語入聲韻中的[p]韻尾進入日語后,轉譯成“フ”。“フ”讀作[fu],是以元音結尾的合口韻。一部分帶[i]介音的字音形成拗長音;另一部分形成長音。在日語長音的形成過程中語尾“フ”后來變為“ウ”。例如:枼部的“塔”日語譯音為[tafu],表記為“タフ”,而現代日語讀作[to:]表記為“トウ”。這說明“フ”經過演變脫落了輔音[f]后形成[u],即[fu]→[u]。[p]韻尾字音的日語對譯音由“フ”尾變為“ウ”尾。那么日語“塔タフ”在變成“タウ”后,又是怎樣演變成“トウ”的呢?
“タフ”的演變過程從讀音看即[tafu]→[tau]→[to:],從韻母看是[au]→[o:],這與前面(一)中的[u]韻尾的陰聲韻豪部開一和開二的漢字音的長音演變過程和演變原因相同。枼部的其他字,如“甲”、“踏”、“閘”、“押”等;以及業部的“乏”、“法”等;合部的“合”、“答”、“踏”、“雜”等被日語吸收的常用漢字與“塔”的演變相同。
此外,入聲韻枼部的“枼”字最初以“エフ”對譯中古漢語音[?p],與“塔”類字一樣演變為“エウ”,形成復合元音。基于以上論述的復合元音進入日語后都演變為單元音的特點,“エウ”與[au]融合成[o:]一樣,也逐漸融合成[o:]。又由于“枼”字聲母為半元音[j],日語的ヤ行的輔音[j]與之相對應,于是日語譯音為[j+o:]→[jo:],日語表記為“ヨー”,形成長音。
綜合以上關于日語漢字音中的長音與中古漢語音韻的對應規律研究,我們認為原本日語音系中所沒有的長音,是在日本學習漢文化的過程中,為對譯中古漢語各種復合韻母形成的“新型語音”。這種在中古漢語音韻影響下形成的語音,豐富了日語語音系統。
[1]史存直.日譯漢音、吳音的還原問題[C].漢語音韻學論文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239.
[2][日]中田祝夫.音韻史·文字史[M].東京:大修館書店,1972:27.
[3]張士東.“夫余”與“句麗”語義考釋[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54.
[4][日]筑島裕.國語學[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11.
[5][日]橋本進吉.國語音韻の研究[M].東京:巖波書店,1961:81.
[6]唐作藩.音韻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75.
[7]李東哲.再談漢日翻譯中的幾個問題[J].延邊大學學報:社科版,2008(2):125.
[8][日]橋本進吉.國語音韻の研究[M].東京:巖波書店,1961:98.
[9]劉富華.從鼻音n,ng與撥音ん的關系看漢語對日語的影響[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