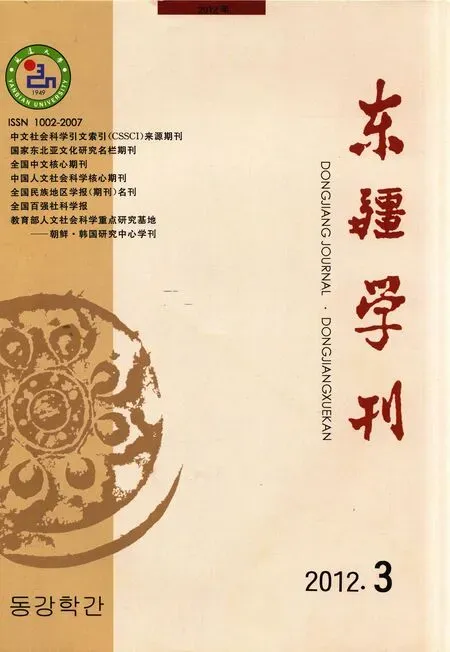論元雜劇的口頭編創特征
鄭劭榮
論元雜劇的口頭編創特征
鄭劭榮
元劇“曲白相生”的藝術體制可能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否定“伶人自為賓白”的觀點需要謹慎。現存元劇文本中的種種跡象顯示,伶人在許多方面參與了劇目的營造工作。具體表現在詩詞韻語的因襲套用,即興插科打諢,關目情節的相互蹈襲以及插入表演片段等諸多方面。伶人編劇方式與劇作家案頭式的寫作不同,它主要在舞臺演出中完成,采取口頭編創的方式。
元雜劇;即興;口頭編創;形態
一
元人雜劇中的唱詞,自然為劇作家所寫,而賓白的作者,歷來頗有爭議。學界對此有兩種意見:其一,賓白與曲詞均為劇作家所為。此說以王國維為代表:“填詞取士說之妄,今不必辨。至謂賓白為伶人自為,其說亦頗難通。元劇之詞,大抵曲白相生;茍不兼作白,則曲亦無從作,此最易明之理也。”[1](102)后代曲家徐朔方、徐扶明等持類似觀點。其二,作家制曲伶人作白。明萬歷時王驥德即云:“元人諸劇,為曲皆佳,而白則猥鄙俚褻,不似文人口吻。蓋由當時皆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卻命供奉詞臣作曲,謂之填詞。凡樂工所撰,士流恥為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辭句多不通。”[2](148)臧懋循亦謂:“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或又謂主司所定題目,止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為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3](3)該說得到了鄭振鐸、唐文標、洛地、任光偉、傅謹等一大批學者的認同。如鄭振鐸提出:“元曲一般有一個特點,即曲子極好,而說白極其庸俗、重復。這是因為原來只有曲子,而說白是明人后加的。《元刊雜劇三十種》中就只有曲無白,白只是‘云云了’,這是讓演員自己根據當時的情節自由發揮的。”[4](132)
王國維否認伶人作白的一個主要理由為:雜劇是“曲白相生”的。何謂“曲白相生”?通常的理解是“曲”與“白”具有互相生發、補充的作用。曲生白,白生曲。或者曲詞呼應,回答賓白;或者賓白召喚,引發曲詞。賓白敘事,曲文抒情。可見,“曲白相生”是傳統戲曲一種重要的文體特征。問題在于,王國維以曲白俱全的《元曲選》為參照系所得出的結論是否可靠?
現有研究表明,科白俱全、曲白完整的劇本形制是雜劇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的。《元刊雜劇三十種》除正旦、正末有簡要的賓白,次要角色念白之處一般只注明“等……云了”、“……云了”、“等……云住”等語,大多沒有說白的內容。可見,元刊本“曲白相生”的戲劇特征并不十分明顯。賓白減省的劇本形式一直延續至明代初期。明初劉東升所撰《嬌紅記》雜劇,其宣德刊本常用“……一折了”、“……云了”等形式省略賓白。朱有的雜劇,凡宣德、正統年間所刻,在劇名之下均標明“全賓”,說明當時有些雜劇仍可能是賓白不全;即使在朱有的雜劇里,一些老套角色的程式化自我介紹同樣被省略,有的插科打諢沒有具體內容,只注明“凈打諢科”。很顯然,這是讓演員自己去措辭說白。[5](37)曲白俱全的元人雜劇選本出現于明代,但明本雜劇與元刊本并不存在直接的繼承關系。孫楷第在研究《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時提出:《改定元賢傳奇》、《古名家雜劇》、《元人雜劇選》、《陽春奏》等與《元曲選》屬于不同系統。前者“其文皆大同小異,知同出一源。其所據底本今雖不能盡知,然余意當直接自明內府或教坊本出。明內府本曲與教坊本同,故亦可云自明內府本出。……(《元曲選》)師心自用,改訂太多,故其書在明人所選元曲中自為一系”[6](150-151)。換言之,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明本元人雜劇,大多反映的是明代宮廷舞臺演出情形,把經過后代加工改造的作品直接視為元代劇作家的初始創作恐怕是不妥的。同樣,依據明人雜劇選本來推斷元代劇目的編創機制亦須謹慎。
眾所周知,“曲本位”思想幾乎貫穿于我國古代戲劇史之中,劇作家主要在曲詞的寫作中顯示才情,重曲輕白的創作傾向始終存在。“今人以成熟的‘真戲劇’的觀念解讀元人雜劇,認為雜劇曲、白自雜劇之初便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由雜劇作家一手完成,可能是有很大問題的。”[7](96)總之,在中國戲曲中,“曲”和“白”是否具有與生俱來的“相生”關系,在元劇中兩者是否由同一作者完成,依然是一個值得繼續探討的話題。由此提出一個研究元劇的重要問題,元代伶人究竟在戲劇的哪些層面、以何種方式參與了雜劇的編創工作?
二
王國維認為:元曲為活文學,明清之曲,死文學也。[8](1)此語盡管有些偏激,卻無意間揭示出元雜劇與明清文人傳奇劇本在演出形態上的巨大差異:前者可以在劇作家文本的基礎上加以改動、變異;后者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式的表演,甚至要求伶人演唱“一字不易”。
諸多跡象顯示,如同后代民間戲劇,元雜劇亦“劇無定本”,因為元代伶人在很多方面也參與了劇本的創作工作。他們的創作主要不是案頭式的寫作,而是在舞臺演出中完成的一種口頭編創方式。這里最明顯的佐證是,元劇中存在大量的因襲雷同現象,舉凡人名、上下場詩、家門、情節、劇目等皆有現成熟套可供搬用,體現出與明代文人傳奇迥然不同的審美特征。
在現存元劇中,除了曲詞,很多方面均出自伶人,最典型的是上場詩中陳詞套語的運用。大體上只要戲劇人物的性格、身份、年齡、職業相似,就可念誦相同或相近的上場詩。如衙內出場,其上場詩中常有“花花太歲為第一,浪子喪門世無對”這兩句,然后便是“則我是權豪勢要某衙內”。如《望江亭》中的楊衙內、《燕青博魚》中的楊衙內、《陳州糶米》中的劉衙內、《生金閣》中的龐衙內等,均有這種公式化的上場詩。在演出當中,雜劇藝人可以靈活地選取、變化這些套話,充分發揮舞臺上的臨場創造性。如《看錢奴買冤家債主》中的店小二上場詩為“酒店門前三尺布,人來人往圖主顧。做下好酒一百缸,倒有九十九缸似頭醋”,《包龍圖智勘后庭花》中為“酒店門前七尺布,過來過往尋主顧。昨日做了十甕酒,倒有九缸似頭醋”。
比較元刊本和明代抄本、刻本,在不同版本中,同劇目同場次的人物上場詩往往存在差異。如《醉思鄉王粲登樓》第一折店小二上場詩,脈望館本為“買賣歸來汗未消,上床猶自想來朝。為甚富家頭先白?曉夜思量計萬條”,而《元曲選》本作“酒店門前三尺布,人來人往圖主顧。好酒做了一百缸,倒有九十九缸似滴醋”。再如《秦修然竹塢聽琴》第一折梁公弼的上場詩,顧曲齋本、古名家本中作“白發刁騷兩鬢侵,老來灰盡少年心。等閑贏得貪天夢,但得身安抵萬金”,而《元曲選》本后兩句為“雖然贏得官猶在,怎奈夫人沒處尋”。《元曲選》本《看錢奴買冤家債主》第三折賈長壽詩為:“一生衣飯不曾愁,贏得人稱賈半州。何事老親恁善病,教人終日皺眉頭”,息機子本作“四脈八肢身帶俏,五臟六腑卻無才。村入骨頭挑不出,俏從胎里帶將來”。該詩還用于《東堂老勸破家子弟》揚州奴、《風雨像生貨郎旦》中的魏邦彥、《黑旋風雙獻功》中的白衙內等。兩相比較,《元曲選》本中的上場詩更切合劇情,明顯有后人加工改造的痕跡;息機子本采用的是市井浪子的陳套熟語,更符合藝人舞臺演出時的口吻。類似現象在元劇中非常普遍,因此不再一一贅述。
筆者以為,上述上場詩在不同選本之間形成的差異,其根本原因恐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版本問題,更可能是因舞臺演出本的不確定性和可改易性造成的,是伶人按照當時的演出套路加以改編、移植的結果。上場詩的編演大致呈現以下規律:首先,要求詩句合仄押韻,尤其與核心詩句的韻腳必須保持一致;其次,與戲劇情境相關聯,切合劇中人物的身份、年齡、性格等;最后,它是一種類型化的表達方式,具有較強的普適性,可以靈活運用于不同的劇目之中。可以推想,只要伶人掌握了以上規律,就可輕松自如地口頭編創上場詩,無需劇作家的寫定。
元劇中高度雷同的陳詞套話是怎么來的?唐文標認為是來自于優伶們自己成立的“行會”。伶人的伎藝代代相傳,所學所聞皆有“宗譜”,父子師徒往往口傳心授一些技藝口訣。《武林舊事》中所載“掌記”,即為類似口訣的梨園隨身寶。[9](184-189)這種分析不無道理。王利器先生注意到元明小說、戲曲中存在一種“留文”現象。關漢卿《趙盼兒風月救風塵》第三折寫道:“那唱詞話的有兩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我為你斷夢勞魂。”《水滸全傳》第四十五回亦云:“……話說這一篇言語,古人留下云云。”王先生認為,“這種留文是書會積古師師相傳的枕中秘本。是書會才人們‘饋貧之糧’的隨身寶。《醉翁談錄·小說開辟》所說的‘說收拾尋常有百萬套’,就是指的這種留文”。[10](225)我們認為,留文中可能就包含有用于戲曲的詩詞韻語,它在伶人間輾轉傳抄,供編演新劇使用。留文絕大多數是由下層藝人編制,當然也不排除有文人的寫作。總之,留文以及近似于梨園口訣的材料是元雜劇中陳言套語的重要來源。
我們還注意到,同一詩詞不僅在不同劇目中反復使用,而且存在于宋元說唱藝術中。有學者研究,北曲雜劇上場詩、下場詩與宋元講唱文學中的入話詩、段落收束詩、文中贊詞相類,因襲的痕跡十分鮮明。[11](187)如官員坐衙時的上場詩多用“冬冬衙鼓響,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岳嚇魂臺”(《崔府君斷冤家債主》第四折崔子玉、《王月英元夜留鞋記》第三折包公、《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第四折包公、《包待制智斬魯齋郎》第四折包公),宋元小說話本《陳可常端陽仙化》描寫臨安府尹升廳:“冬冬衙鼓響,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殿,東岳攝魂臺。”《皂角林大王假形》趙知縣坐衙亦用到同樣的詩句。戲曲中老年人常用“月過十五光明少,人過中年萬事休”詩句,小說話本《種瓜張老》亦有同樣的表述。類似情形比較普遍。
比較合乎情理的解釋是,高度雷同的上、下場詩是藝人事先編好、記好或抄錄在本子上的。它們是編撰故事的通用構件,不僅用于戲劇演出,還可用在說唱藝術中。我們有理由相信,元雜劇中的陳詞套語主要來自口頭傳播,是舞臺演出的產物,其編創者就是歷代的勾欄藝人。
三
元雜劇藝人臨場發揮的內容不局限于上場詩這類套詞,不少劇中的插科打諢、插入性的表演片段也是由伶人編制的。王驥德云:“古戲科諢,皆優人穿插,傳授為之,本子上無甚佳者。”[2](141)在王氏看來,伶人造的科諢要勝過固定劇本所寫的,它們為藝人歷代相傳。伶人自造科諢的傳統源遠流長,自先秦優戲至宋代雜劇,優人一直以滑稽戲謔見長。早期的優戲演出沒有腳本,僅靠演員臨場發揮,具有明顯的即興編創特征。王驥德也注意到這一點,說古之“優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習現成本子,俟主人揀擇,而日日此伎倆也。如優孟、優旃、后唐莊宗,以迨宋之靖康、紹興,史籍所記,不過葬馬、漆城、李天下、公冶長、二圣環等諧語而已”[2](150)。
元劇賓白中存在不少慣常的表達方式,它與詩詞套語不同,是一種散語套話,只要遇到類似戲劇情境,便會出現于伶人口中。如需要提示重要角色出場,則在人物開場白的結尾處說“看有什么人來”。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人常會感嘆“天那!我有這一片好心,天也與我半碗兒飯吃”,或者說“憑著我這片好心腸,天也與我條兒糖吃”(如《河南府張鼎勘頭巾》中的道士、《朱砂擔滴水浮漚記》中的邦老、《羅李郎大鬧相國寺》中的侯興)。當表現劇中人走街串巷時,便說“驀過長街,轉過短陌”(如《張天師斷風花雪月》、《錦云堂暗定連環計》等劇)。
雜劇藝人常將他們擅長的伎藝有機融入戲劇演出,諸如口技、雜耍、說唱、隱語、滑稽小戲等。有的與劇情相關,有的明顯游離于劇情之外。不管何種情況,它們均留下了伶人創造的痕跡。插入性的演出有三類:第一、穿插與劇情相關的非戲劇類的表演技藝。如《逞風流王煥百花亭》表演“叫果子”:“(正末提查梨條從古門叫上,云)查梨條賣也!查梨條賣也!才離瓦市,恰出茶房,迅指轉過翠紅鄉,回頭便入鶯花寨,須記的京城古本老郎傳流。這果是家園制造,道地收來也。……”“叫果子”是北宋即已流行的市井伎藝,以模仿各種叫賣的市聲為樂。據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吟叫”條載:“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戲。其本蓋自至和、嘉佑之間叫‘紫蘇丸’,洎樂工杜人經‘十叫子’始也。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聲調,間以詞章,以為戲樂也。今盛行于世,又謂之吟叫也。”[12](353)耐得翁《都城紀勝》稱這類伎藝為“叫聲”。南宋后依然流行,吳自牧《夢粱錄》載:“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物之聲,采合宮商成其詞也。”[13](310)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八載: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時,“自早呈拽百戲,如上竿、弄、跳索、相撲、鼓板、小唱、斗雞、說諢話、雜扮、商謎、合笙、喬筋骨、喬相撲、浪子、雜劇、叫果子、學像生、倬刀、裝鬼、砑鼓、牌棒、道術之類,色色有之。”[14](48)雜劇明確交代叫賣“查梨條”是“京城古本老郎傳流”,可以肯定,在這里,雜劇藝人按照歷代流傳下來的表演套路,將“叫果子”運用到了戲劇演出中。此外還有《風雨像生貨郎旦》中的“說唱貨郎”、《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第三折中的“說唱愚鼓”(漁鼓),均屬于同性質的演出形式。這些表演形式是歷代勾欄藝人流傳下來的,藝人臨場搬演,無需劇作家來設計。
第二,在劇情演繹中融入院本演出。胡忌先生在元雜劇中找到一些宋金雜劇的殘留,有“先生家門”下的“清閑真道本”和“卒子家門”下的“針兒線”兩種。前者見于李文蔚《張子房圮橋進履》中喬仙化身道士所云,后者見于元無名氏《飛刀對箭》第二折凈扮張士貴上場的一段念白。“清閑真道本”不論哪位道士出場都可套用,“針兒線”則凡是庸將也無不可念。[15](249-250)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院本名目》“打略拴搐”目下“先生家門”載有“清閑真道本”、“卒子家門”有“針兒線”。毫無疑問,它們在元劇之前就存在,當然不應歸為元雜劇作家的創造。可以推想,宋金時代這類體制短小的院本一直在勾欄藝人口頭流傳,當新興的元雜劇盛行以后,只要與戲劇情節大體扯上聯系,就可任意穿插到相關劇目中去,成為雜劇藝人編創新劇的現成材料。
第三,在雜劇的折與折之間插演歌舞雜技。黃天驥先生指出:元劇在演出時,折與折之間往往穿插爨弄、隊舞、吹打之類的伎藝,用來填補因演員換裝所出現的舞臺時間上的空白。這些雜藝究竟如何表演和調度,劇本上并沒有明文規定,很可能是由藝人即興發揮的,后代的劇本選家們也就無從記錄。[16](43)此論甚是。劇本選家關注的是戲劇的文學性,他們看重的是出自劇作家之手的曲詞,對于伶人的藝術創作,是不屑于記錄在案的。
元劇情節關目與劇情結構雷同現象亦非常突出,徐朔方《金元雜劇的再認識》所論甚詳。例如文人落魄,讓其受親故冷落,被迫出走,文人由此發奮讀書,成就功名后準備報復時,則由旁人道破實情——原來親人為激勵自己上進,表面上故意為難,實際上卻暗中資助盤纏,最后誤會化解。《凍蘇秦》、《王粲登樓》、《漁樵記》、《舉案齊眉》、《裴度還帶》、《破窯記》等劇均使用該關目。再比如,原以為死去的親人忽然出現在眼前,為了驗證對方是人是鬼,就會說:“你是人呵,我叫你,你應的一聲高似一聲;是鬼呵,一聲低似一聲”;有時恰好堵了一口氣應不出聲來,或者對方故意低聲回應,制造有鬼的誤會,產生滑稽詼諧的舞臺效果。該關目見于《合汗衫》、《桃花女》、《貨郎旦》、《羅李郎》等劇。又如劇中人物原本平靜地生活,在街上碰見算命先生,告知有“一百日血光之災,必須外出躲災”,然后遠走他鄉,結果反而遭遇不測。《朱砂擔滴水浮漚記》、《張孔目智勘魔合羅》、《梁山七虎鬧銅臺》、《玎玎盆兒鬼》等劇便是如此。有時甚至一折或整本雷同或因襲,如《梧桐雨》因襲《拜月亭》,《還牢末》因襲《酷寒亭》,《勘頭巾》與《魔合羅》雷同等。
如何解釋上述現象?徐朔方認為金元雜劇是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當時傳統劇目有的可能只有口口相傳的簡單梗概,或幾支主要曲牌,然后由各書會才人寫定全劇的曲白。”[17](118)徐先生分析頗具創建性,元劇的雷同因襲與其劇目的營造方式密切相關。眾所周知,元劇不少故事題材早已在民間藝人口頭輾轉流傳,故事在傳播中必然有相互之間的借鑒、套用,劇作家據此編創劇本,出現劇目情節的雷同因襲,便不難理解。因此,王驥德所云“教坊樂工先撰成間架說白,卻命供奉詞臣作曲”的傳聞,可能并非空穴來風。
由上所見,元代雜劇藝人廣泛參與了戲劇腳本的編創工作,舉凡上場詩、科諢笑料、插入性的表演片段,均可以按照伶人自己的套路臨場發揮。即使有文字劇本,也并非全部按照劇作家設置的規定動作來表演,賓白字句可以增刪、更改,舞臺動作可以按照一定演出程式靈活處理。這提醒我們,戲劇史上的文字劇本往往遮蓋了許多生動的歷史細節,其中既有傳統文人戲劇觀和后代“真戲劇”觀的影響,也與伶人口頭編創的即時性、易變性所帶來的文字記錄上的缺失相關。
總之,元雜劇劇本編創問題的提出,使我們對元雜劇劇目的營造方式、伶人在編創劇本上所起的作用等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在元代,伶人不只是被動地接受劇作家書寫的文字劇本,他們還廣泛參與了雜劇的創作工作,在表演中融入了歷代口傳的表演技藝和戲劇元素。因襲、套用和臨場發揮是藝人編創劇本的常用方法,既延續了伎藝的傳承譜系,又重塑了戲劇作品,使之符合舞臺藝術的要求,使劇目常演常新,富于鮮活性和創造性。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案頭文學與舞臺腳本之間的裂縫。通過這種藝術實踐,伶人掌握了大量的劇本文學資源,提高了編劇技巧,為他們獨自營造戲曲劇目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這啟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戲劇史,需要透過書寫文明的壁障與誤解,重視戲劇的口述歷史,才能不斷揭示劇史真相。
[1]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
[2]王驥德:《曲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
[3]臧懋循:《元曲選》序》,《元曲選 (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4]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戲曲傳統》,《鄭振鐸說俗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伊維德:《朱有的雜劇》,張惠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6]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年。
[7]解玉峰:《元曲雜劇“題目正名”推考》,《民俗曲藝》,2003(140)。
[8](日)青木正兒原:王古魯譯,《中國近世戲曲史(上)》,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
[9]唐文標:《中國古代戲劇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
[10]王利器:《〈水滸傳〉留文索隱》,《文史(第十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11]范麗敏:《互通·因襲·衍化——宋元小說、講唱與戲曲關系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
[12]高承撰、李果訂:《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13]吳自牧:《夢粱錄》,《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
[14]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
[15]胡忌:《宋金雜劇考》,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16]黃天驥:《元劇的“雜”及其審美特征》,《黃天驥自選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7]徐朔方:《金元雜劇的再認識》,《徐朔方集第一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I237.1
A
1002-2007(2012)03-0036-06
2012-03-28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傳統戲曲口頭劇本研究”,項目編號:11BZ W078;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記憶·編創·表演——傳統戲曲口述劇本形態研究”,項目編號:10YJC751133。
鄭劭榮,男,長沙理工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戲曲研究。(長沙 410004)
[責任編輯 梁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