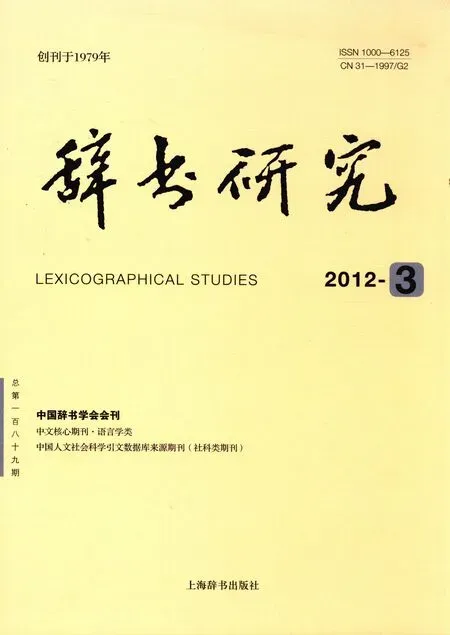談《急就篇》等秦漢字書的性質——與張金光先生商榷
張傳官
秦漢兩朝是字書迭出的時代,秦代的舊“三蒼”(《倉頡》、《博學》、《爰歷》),漢代的新“三蒼”(《蒼頡》、《訓纂》、《滂喜》)以及《凡將》、《急就》、《元尚》等層出不窮,或修訂前著,或另撰新篇,在中國早期字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關于這些字書的性質,學界大多認為是幼童識字教材,屬于古代蒙學的范疇。但是,從古至今,也有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唐代顏師古就曾質疑:“至如雜寶奇繪,殊俗異服,及疾病刑獄,官曹職務,豈非當時庠校之內悉自有乎?”不過,他隨即將這種情況視為“皆泛說耳”。[1]這一解釋雖然語焉不詳,卻基本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清代陳本禮在《急就探奇》中認為《急就篇》是史游“勤心納忠”之作,不是一般教學童識字的蒙本。但該書“把此篇視為史游諷諫元帝的一篇政論,其中字字微言大義;而且又把陰陽五行和程朱理學牽扯在一起來注釋史游的思想。結果,不但不能真正探明《急就》的大旨所在,反而制造了混亂”(沈元1962:86)。陳說避實務虛、求之過深,顯然不通。沈元(1962:78)指出:“漢代的宦官中很有一些人是善于書記的,皇子幼年時期的保傅兼啟蒙老師,多半選擇老成而多職的宦官擔任。”在其位謀其政,史游編書很可能只是為了教學需要或進行教學總結。
近年來,張金光研究秦漢教育史,頗有創見。他對秦漢字書的性質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張先生于1984年首次提出他的新觀點,又在2003年再次加以強調。[2]兩處論述除個別文字不同外,觀點基本一致,今引述后者如下:
秦之《倉頡》《博學》《爰歷》,漢之《急就篇》,皆系當時學吏者識字、學書、識名物所使用的課本,并非一般的啟蒙教材。
這樣大量的物名姓字,只有以治書定簿為務的文吏才為急切之需。……《急就篇》所列諸物名稱,為少吏造簿籍、搞出納所必用,見諸漢簡廩簿、器物簿中之物名,皆不出《急就篇》所列。……一部《急就篇》所說總不外諸物名稱,人名姓字,百官職守,典章制度,為吏之道。全部切關吏事,處處從小吏著眼,這不足以證明《急就篇》是學吏者的識字學書課本嗎?明乎此,便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居延等處漢簡中出現了不少邊吏們抄的《倉頡》《急就篇》的竹簡(引者按:當為木簡、木牘),這也證明了《急就篇》等被吏徒用作課本的事實。就連《急就篇》之為名,也是取學吏速成課本之意。
秦之《倉頡》未傳下,全貌不知。但其性質當亦類后世之《急就篇》。這一觀點存在合理的地方,如《急就篇》與基層庶務密切相關,吏徒以之為教材等都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是根據這些情況并不能得出秦漢字書為學吏者專用的啟蒙教材的結論。
秦漢教育制度中的受教育對象,主要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階層。從當時字書的內容來看,其中的姓名、名物、職官、制度固然是基層官吏須臾不可離的,卻也與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因此沈元(1962:62)稱《急就篇》為漢代“生活的一面明亮的鏡子”。秦朝獨尊法家,焚禁諸子百家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法律條令成為各階層的必修課;兩漢經學盛行,《論語》、《孝經》、“六經”等成為進一步深造的教材;而當時字書所包含的“百科全書”式的內容可以為這些中高等教育提供基礎知識。一般民眾需要了解的,更多的是與法令、醫藥、卜筮、種植、方術等實用技能有關的知識。而秦漢字書充滿了實用性的內容,也與一般民眾的知識結構相合。雖然學吏者以字書為教材,是為了更好地處理基層庶務,但我們顯然不能將這些字書的使用范圍局限于學吏者。
確實,就學童啟蒙來說,受教育者包括不少基層官吏子弟。《說文解字·自敘》引《尉律》曰:“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也有相似的內容:
史、卜子年十七歲學。史、卜、祝學童學三歲,學佴將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學童詣其守,皆會八月朔日試之。〔試〕史學童以十五篇,能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卜學〕童能諷書史書三千字,誦卜書三千字,卜六發中一以上,乃得為卜,以為官佐。其能誦三萬以上者,以為卜上計,六更。……以祝十四章試祝學童,能誦七千言以上者,乃得為祝,五更。大祝試祝,善祝、明祠事者,以為冗祝,冗之。 (簡 474—479)[3]
這些學童大多是史、卜、祝等疇官之子,身份比較特殊。他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繼承父業擔任基層官吏。但這種情況的出現,只是字書作為童蒙教材造成的結果,而不能成為字書只用于基層官吏教學的證據。疇官子弟學習字書,并不能否定其他階層學習字書。
就這些字書的編者自道來看,也難以得出它們與基層官吏教材有唯一且必然聯系的結論。《急就篇》首章云:“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介紹了此編列字體例,并勉勵讀者刻苦勤學。已有學者根據典籍和漢簡的記載,基本復原出漢代某種七言本《蒼頡篇》首章的內容:
〔蒼頡作〕書智不愿,以教后嗣世〔□□。幼〕子承詔唯毋〔□,謹〕慎敬戒身即完。勉力諷誦槫出官,晝夜勿置功〔□□,茍務成〕史臨大官。計會辯治推耐前,超等秩群〔□□□,出尤別異〕黑白分。初雖勞苦后必安,卒必有〔喜□□□。愨愿忠信□〕事君,微密痣〈痰〉塞天性然。奸佞〔□□□□□,□□□□□□□〕。[4]
文中雖然說到出官、臨大官,又談到忠臣與奸佞,但恐怕只是泛論,并無專門針對基層官吏的意思,而更突出的還是其勸人向學的意圖。
張先生新說也無法解釋魏晉之前字書的演變和傳播情況。在西漢以后的六百多年間,《急就篇》作為啟蒙教材風行一時。史游生活的年代,距西漢滅亡只有四五十年,而居延出土的西漢木簡中就已經發現了《急就篇》文句。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此編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從首都傳播到邊疆,可見其流傳速度之快。在河北等地發掘的東漢墓葬中,甚至出現了用《急就篇》文字與數字、干支等一起給磚塊編號的情況,可見當時人們對此編的熟悉程度。[5]史籍中也屢見人們幼年學習《急就篇》的記載,如《魏書·崔浩傳》:“人多托寫《急就章》。”浩自表:“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北齊書》謂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魏書·儒林傳》載劉蘭始入學“書《急就篇》”,又《北齊書》李繪未入學,“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而他們都不是學吏者或疇官子弟。凡此種種,以及魏晉書家如鐘繇、衛夫人、王羲之多以《急就篇》為內容進行書法創作等情況,均可以說明《急就篇》等秦漢字書的使用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學吏者。
此外,《漢書·藝文志》明確記載漢代“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的編者為“閭里書師”,而與基層官吏無涉,亦可見這些字書在民間廣為流傳。
張先生以邊地出土簡牘作為佐證,也是不合適的。西北地區氣候干燥,木簡木牘容易保存,這是敦煌、居延漢簡大量出土的特殊原因。這并不能說明其他地區的實際情況,更不能說明字書為學吏者專用。
實際上,《說文解字》之前的字書,羅列文字,缺乏注釋,收字也不求全面,往往兼有蒙學讀物的性質(徐梓1996:31)。同時,從《史籀篇》到秦“三蒼”再到漢“三蒼”、《急就篇》,都與各個時代的籀文、小篆、隸書等書體密切相關,都是當時的書寫范本。字書、啟蒙教材、書寫范本三位一體,是廣泛適用于社會各個階層的。因此,張先生的新說似不能成立;對于秦漢字書的性質,我們仍取舊說,視之為通用的啟蒙教材。
附 注
[1] 史 游(漢)著,顏師古(唐)注,王應麟(宋)補注.急就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36.
[2]張金光.論秦漢的學吏制度.文史哲,1984(1):35;張金光.論秦漢的學吏教材——睡虎地秦簡為訓吏教材說.文史哲,2003(6):65.
[3]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96—301.本文引用簡牘釋文,皆據寬式隸定,缺文可補者以〔〕補出,不識者以□代替,錯字以〈〉改正。
[4]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讀水泉子簡《蒼頡篇》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11—11.
[5]李捷民,姚鑒,李錫經執筆.望都漢墓簡介.∥北京歷史博物館,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望都漢墓壁畫.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5:13;孟昭林.無極甄氏諸墓的發現及其有關問題.文物,1959(1):45.
1.沈元.急就篇研究.歷史研究,1962(3).
2.史游(漢)著,顏師古(唐)注,王應麟(宋)補注.急就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3.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4.張金光.論秦漢的學吏教材——睡虎地秦簡為訓吏教材說.文史哲,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