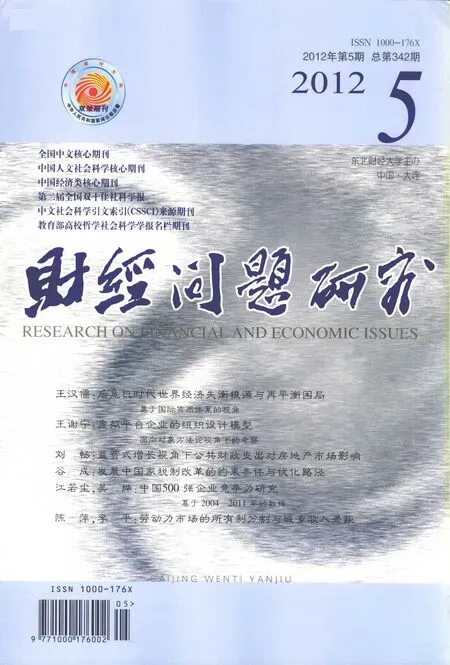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的約束條件與優化路徑
谷 成
(東北財經大學 財政稅務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一、引 言
作為政府彌補公共產品成本、鼓勵或抑制某些類型的行為以及矯正市場缺陷的重要手段,稅收的必要性不僅體現為以非通脹方式為政府支出籌集資金,還應盡可能保證這些支出負擔在納稅人之間的分配是公平的。實踐表明,任何國家的稅制改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觀念、既得利益和財政體制的影響。稅收政策的選擇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增加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需求和意愿以及征管能力等因素,還取決于非稅收入(如自然資源租金和外國援助等)的可獲得性以及政府對公平收入分配和提高經濟增長率等公共政策目標的偏好。因此,稅制改革不僅是一個經濟學問題,還反映了對公平的關注以及維護社會穩定等政治訴求。本文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稅制改革目標,考察了實現這些目標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約束條件,在此基礎上提出進一步優化稅制的政策建議。
二、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的主要目標
1.增加財政收入
好的稅制必須能夠為政府支出籌集足夠的資金。為了維持既定的政府規模,稅收收入的增長應當與經濟增長幅度大體相當。稅制的收入彈性被定義為稅收收入變化的百分比除以GDP變化的百分比,用以衡量相對于經濟增長而言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①例如,彈性為1,意味著稅收收入占GDP的份額保持固定的比例;彈性大于1,則表明稅收的增長快于收入的增長。**稅收彈性取決于稅收結構、稅收管理質量以及經濟增長的幅度和結構性特征。
從稅收結構上看,最富有彈性的是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和按照平均收入水平確定的免征額使得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增長幅度可能超過經濟的增長幅度。相反,采用比例稅率課征的稅種,稅收收入的增長幅度將與經濟增長幅度持平。由于稅制的總體彈性是各稅種彈性的收入加權平均值,因此相對于單一的收入來源而言,多樣化的稅收工具有助于降低稅收收入的不穩定性。經濟增長的幅度和結構性特征表明,主要依靠自然資源(如石油或礦產)取得稅收的國家更易受到經濟周期的影響。此外,在采用從價征收而不是從量課稅的情況下,如果商品稅的征收范圍包含著經濟總量中增長更快的產品和服務而不僅局限于傳統產品,就會使商品稅更富有彈性。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增長只是提供了可供征稅的稅源——對這些稅源是否課稅、哪些應當課稅、如何課稅、課什么稅和課多少稅由稅收制度決定——至于最終能實現多少稅收收入入庫,則要受到稅收征管水平的制約。①改善稅收管理短期內使稅收顯著增加的最典型事例是阿根廷1989—1992年間收入的迅速增長(從GDP的13%提高到23%)。Morisset和Izquierdo估計,大約2/3的增長源于征管努力的提高[1]。然而,另一些文獻指出,阿根廷后來的情況表明,長期維持這種增長非常困難。在技術改良和征管努力提高使收入增加的情況下,政治壓力往往很快阻礙甚至完全抵消稅收水平的凈增長[2]。
2.降低稅收成本
稅收減少了可用于實現社會福利的資源,從而導致了經濟成本。②從經濟整體角度看,稅收本身并不是一項成本,因為它們只是將資源從私人部門轉移至公共部門。只有當社會可使用資源的數量(無論是由公共部門使用還是由私人使用)因征稅而減少時,成本才會產生。稅收成本主要產生于如下方面:首先,稅收的征收需要成本。目前,發達國家僅將1%的稅收收入用于彌補征稅的成本。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征稅成本則普遍偏高,③例如,Cuatemala的研究估計,這些成本大約占稅收收入的2.5%[3]。其中所得稅的成本又遠遠高于商品稅。從收入上看,在商品稅體系中(包括增值稅和消費稅和關稅等)投入管理成本取得的邊際收益明顯高于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支出,尤其是用于工資薪金扣繳所得稅之外的部分。其次,除了實際支付的稅收外,納稅人在履行納稅義務的過程中還會發生遵從成本。④當遵從成本增加時,征收成本可能會降低。例如,當納稅人被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時,遵從成本就會增加,而使征管更為便利,成本降低。但征收成本和遵從成本之間的這種此消彼長關系并不總是存在。例如,在更為復雜的管理要求納稅人提供更多信息或接受更多稽查等情況下,遵從成本和征收成本可能都會增加。遵從成本主要由負有申報或扣繳義務的經濟活動主體承擔。遵從成本包括因納稅而導致的資金和時間成本,例如按要求建立會計賬簿,獲取必要的稅收知識和信息,取得并傳送為完成扣繳或申報稅款所需的數據,以及向中介機構支付的費用等。盡管對這些成本的衡量并未引起過多關注,但對發達國家的估計表明,遵從成本可能要比政府的直接管理成本高4—5倍[4]。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遵從成本要高得多。⑤Chattopadhyay和Das-Gupta有關印度個人所得稅遵從成本的研究表明,該國遵從成本比發達國家高10倍[5]。最后,稅收還會導致效率成本。大多數稅收通過改變征稅對象的相對價格對企業和個人的決策產生潛在影響。⑥也有一些例外,例如一次總付稅。此外,對經濟“租金”的課稅(如對自然資源和土地的合理課稅)可能不會導致經濟扭曲。再者,在某些情況下,合理設計的稅收不僅不會導致經濟行為的扭曲,甚至還將引致理想的行為——某些環境稅和受益稅都具有這種效應。但是,政府籌資所需的大部分稅種將來源于其他方面,并產生效率成本。由此而導致的結果是,經濟活動主體的行為變化通常會減少資源的使用效率,進而降低一國的產出和福利水平。例如,對工資課稅(包括個人所得稅、工薪稅和社會保障稅等)降低了對工作的激勵——正式部門的工資稅率越高,相對于在不課稅(或不直接課稅)的非正式部門而言,在正式部門工作的吸引力就越差。⑦隨著非正式部門勞動力供給的增加,(相對于正式部門而言)非正式部門的工資將下降,因此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勞動者也間接地負擔了一部分稅收。商品稅同樣對工作具有抑制作用。一方面,對消費的課稅使個人必須在工作上花費更多的時間,以購買市場上的產品和服務。由于對閑暇并不課稅,因此所有稅收都在邊際上對工作產生抑制效應。另一方面,由于稅收減少了個人收入,因此人們也可能選擇更多地工作,以補償失去的收入。稅收變化對工作產生的凈效應表現為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6]。
3.促進社會公平
稅制的公平性很大程度上影響納稅人的內在遵從意愿。因此,要想使納稅成為一種被社會成員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合理的稅制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行為經濟學家的研究結果表明,對公平的認知和感受在納稅人的逃稅行為中影響顯著[7-8-9]。稅收制度能否存續下去,一方面取決于政府能否負責而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則取決于稅制公平的可觀察性和可接受性。如果可感知的稅收負擔分配不公被認為是導致財富和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就將導致納稅人對稅制信任程度的降低并增加逃稅和避稅。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逃稅更多地被視為一種榮耀,而不是犯罪。水平較低的稅收道德和不完善的稅收管理導致了負面的“稅收文化”[10]。
實踐表明,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傳統思路并未取得明顯的效果,近年來個人所得稅占稅收總額或GDP的比重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很多發展中國家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收入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僅為5%—10%,還不到GDP的2%。這與大多數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結構中占比最高的情況大相徑庭[11]。由于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相對于商品稅而言小得多,因此即使累進程度很高的所得稅對財富和收入分配結果的影響也十分有限。盡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征稅進行再分配的努力往往事倍功半,但是,對從經濟發展中獲益最多的群體課稅在政治上不僅是必要的,也是理想的①Webber和Wildawsky將所得稅視為“民主的鏡子”,意為主張人人平等的標志和對社會公正的崇尚與追求。此外,Cavanaugh指出,稅收是政治體制用以實現分配公平的最重要手段。在民主社會中,朝這一方向的努力(盡管并不一定產生明顯的效應)在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12-13]。——必須使稅制的公平性得到納稅人的接受。
三、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的約束條件
1.非正式經濟規模較大
近來很多有關發展中國家稅收的討論都對所謂的“非正式經濟”(又稱地下經濟、影子經濟)十分關注。②非正式經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非法行為,例如毒品、賣淫和走私;另一類是合法行為,主要包括來源于未申報的個體經營收入、非正式就業工資和易貨交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非正式部門的規模和結構存在著很大差異,平均而言,非正式經濟活動在發展中國家大約占GDP的40%,差不多是發達國家的二倍[14]。
在評價稅收政策的效應時,對一個規模較大且不繳納所得稅的經濟部門的考察是無法回避的。無法對非正式經濟課征所得稅不僅會左右資源在正式部門和非正式部門間的分布,而且削弱了個人所得稅的收入調節職能,不利于再分配效應的發揮。再者,非正式經濟規模的擴大還將導致稅收收入總量的降低,從而減少政府可以用于再分配支出計劃的財政資金。非正式經濟規模較大的現實環境要求發展中國家采用更為合理的方式實現稅制改革的目標。
2.國際環境約束
貿易自由化和WTO規則成為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的新制約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和WTO的推廣以及國外投資競爭的加劇,稅制結構中國際貿易稅收收入大幅度減少,各國對稅制引起的國際結果非常關注。從稅收方面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完全脫離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例如,幾乎所有國家都會關注美國和歐盟的稅制變化,并進行效仿或者以某種制衡的方式予以應對[15]。
與30年前相比,現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目的是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經濟全球化和資本流動使稅收結構不再依賴于公司所得稅,因為資本會因為利息率和稅率的微小變化自由地在各國之間流動。既有文獻表明,東道國的稅率非常重要。Echavarria和Zodrow估計,外國直接投資的稅率彈性為-0.6[16]。實際上,近年來全球個人和公司所得稅稅率都大幅度下降。世界各國的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幾乎普遍保持在20%—30%的范圍內[17]。這些數據比經濟學家的探討更加充分地反映了近幾十年來國際環境的競爭性。
3.薄弱的稅收管理
如果無法有效實施,那么即使世界上最好的稅收制度也毫無價值。因此,稅收制度的設計必須考慮稅收管理水平。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征管成本較低的政府運行良好;反之,以高成本課稅的政府則舉步維艱[18]。現實的情況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大規模不易課稅的傳統農業部門和大量游離于正式稅收制度之外的非正式經濟。此外,許多遵從率較低的小企業的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與非正式部門交搭。對促進這些企業增長與財政收入需求之間的權衡使許多國家更傾向于對小企業采用推定(或簡化的)稅制。盡管采用推定課稅方法估計納稅義務可以將小企業納入稅收網絡,但稅收的收益—管理成本比率較低[19]。同時也使很多具有納稅能力的企業被排除在一般稅收網絡之外[20],稅務機關面臨著不良稅基侵蝕一般稅基的風險。可見,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可獲得的潛在稅基僅占經濟活動總體的一小部分。非應稅經濟的規模在一定程度上是稅收政策的函數。由此而導致的更少的稅收收入通常會使政府提高稅率,并進一步產生對逃稅的激勵。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改善稅收管理對于稅收結構的選擇和征稅而言非常重要。
遺憾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稅收管理遠未達到理想的水平。相關研究表明,目前發達國家用于彌補征稅的管理成本僅為稅收收入的1%。相反,發展中國家的稅收管理成本則要高得多[3]。從稅種上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得稅和財產稅的成本高于商品稅。目前的情況表明,無論通過資本利得稅還是財產稅,對城市和農村不動產的有效課稅仍然處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稅收管理的能力之外[21]。
4.財政分權
財政分權是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許多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重視中央以下各級政府在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中的作用。然而,迄今為止,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分權大多數仍集中于支出的分散化。經驗分析表明,支出分散化率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而提高,在多種族大國中更高[22]。與支出的高度分散化相比,稅收的分散化則明顯滯后。實際上,在發達國家,向中央以下各級政府的分稅并不鮮見。
然而,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央政府不愿賦予中央以下各級政府征稅權。發展中國家中央以下各級政府收入在總收入中的份額僅為10%,而工業化國家為20%。①近30年來,這些數字幾乎沒有發生變化[22]。發展中國家通常將重要的支出責任轉移給中央以下各級政府,卻極少下放收入取得權,大多數中央以下各級政府支出通過轉移支付籌資[23]。盡管通過轉移支付向地方政府撥款有助于中央政府實現地區間財政均等的政策目標,但也無法回避稅收與地方政府支出決策之間的聯系被割裂的事實。經濟理論表明,權衡公共支出的成本與收益是地方政府做出正確財政決策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將地方財政支出調整至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點上,才能取得有效率的結果。如果資金不是來源于地方政府轄區本身,公共支出的邊際收益就會偏離其邊際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地方與更高級次政府間有關地方公共項目補貼規模和形式的談判結果就成為決定地方公共服務范圍和水平的關鍵因素[24]。因此,如何在分權環境下進一步優化稅制仍然是值得發展中國家考慮和權衡的問題。
四、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的路徑選擇
1.保持稅收收入與支出水平之間的聯系
稅收是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成本補償方式,用于滿足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要。②例如,Bastable指出,所謂稅收,就是個人或群體為取得公共權力機構提供的服務而在財富方面做出的強制性貢獻[25]。可見,稅收不僅是一種政府籌資手段,也是作為國家基石的一種最為顯見的社會契約。公民遵守稅法的一個關鍵原因是他們認為國家是合法的和可靠的。換言之,除非國家被認為是合法的,否則就無法取得足夠的資源用以實施統治或進行發展。一國在某一時點上的稅收水平和結構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各種政治群體間的某種利益均衡。特定稅收及其征收方式可能在一定時期內改變這種均衡,并且影響未來的稅收水平和結構。因此,任何稅制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不同政治群體看待改革的方式以及由此做出的反應。盡管迄今為止Wicksell將支出與收入相聯系的主張對發展中國家稅收政策的影響不大③對于目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而言,稅收政策的制定仍在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的預算支出完全脫離[26]。,但對財政支出管理的更多關注最終可能改變公眾在稅收意愿上的態度。為保障納稅遵從和減少稅制改革面臨的政治阻力,必須使那些將要支付更多稅收的人相信,他們繳納的稅收將會得到某些回報。相反,如果從納稅人的角度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與自身繳納的稅收之間距離遙遠,那么潛在的稅收遵從問題將使政府收入的長期可持續性面臨相當大的約束。
目前的情況是,全球范圍內都在討論財政分權問題。為提供能夠滿足地方居民需要的公共服務,地方政府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收入來源,以滿足支出分權的要求。然而,從很多方面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間稅收劃分都是不理想的。各級政府的支出與收入之間都存在著明顯的縱向不均衡是其中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①通常的情況是,即使是最富有的中間或中央以下各級政府(比如聯邦制國家中的“州”)也需要通過轉移支付為其支出籌集部分資金,盡管籌資比例在各州之間可能存在差異。這種不均衡影響著中央以下各級政府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供的自主性、有效性和責任感。在支出分權化條件下,收入與支出責任失衡的政府間財政體系將導致高昂的管理成本、遵從成本和效率損失。為避免資源配置的無效性,劃分給中央以下各級政府的稅收原則上應當滿足如下條件:一是能為最富有的中央以下各級政府提供相對充足的收入,以使其大體上實現財政自主。二是使中央以下各級政府能夠在邊際上履行重要的財政職責。三是不會對資源的有效配置產生扭曲效應。從根本上說,分稅實際上是采用特定的方法確定各級政府自身稅收收入能力的過程。如果不能確定對什么征稅,稅基如何界定,稅率是多少以及征稅的緊迫性如何,那么中央以下各級政府實際上就無法對稅收收入加以控制——即使在它們可能得到某些收入的情況下也是如此。②Breton將“分配”定義為“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權力”。他明確指出,如果一個政府指定了一個代理人——比如另一個政府——執行它(第一個政府)制定的政策,那么這不是分配權力,也未將政治責任轉移給執行政策的政府[26]。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賦予中央以下各級政府制定稅率的權力可能是實現上述目標最簡單和最好的辦法。
2.拓寬稅基
對于政府而言,稅基并不是“既定”的:它們可能會隨著稅收的課征模式而得以增長或者受到破壞。例如,稅收可以抑制或促進經濟的“正式化”,并對進口等“稅收把柄”的增長產生促進或抑制作用,或者從多種角度、采用多種方法將經濟增長引入特定的路徑和軌道。正如Emran和Stiglitz指出的那樣,從長期看,稅收的征收模式不僅影響經濟增長和分配,還會影響稅基的規模和結構[27]。為使征稅的非必要成本最小化,稅基應盡可能廣泛。盡管稅基廣泛的商品稅也會對工作努力產生抑制,但是,對所有或絕大多數產品和服務都征稅有助于實現征稅對產品消費產生的扭曲效應最小化。③理論上說,為使效率損失最小化,應當對不同商品采用不同的稅率,對于行為變化較小的產品和服務采用更高的稅率。然而,這種方法對稅收如何改變行為的信息要求比大多數國家能夠得到的信息高得多。此外,這種模式也沒有考慮管理和公平問題。因此,在實踐中,一般的建議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對產品和服務征收單一稅。所得稅的稅基也應盡量寬泛,對所有來源相同的收入盡量同樣對待。除減少效率損失外,寬稅基還可以使政府以較低的稅率取得既定的收入。稅收的效率成本產生于由相對價格變化導致的替代效應,其大小與稅率的平方成比例。④例如,稅率提高為原來的2倍意味著其效率成本增加為原來的4倍。因此稅率的提高會導致效率損失的增加,尤其是影響外國投資者在生產要素具有流動性的部門間的投資決策。從效率的角度看,通過對廣泛的稅基征收單一稅率取得收入要優于將稅基分為多個部分并對各部分采用差別稅率征稅。
在實踐中,基于多種原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常采用成本高昂的稅收激勵計劃。盡管受到經濟活動主體歡迎,但現實表明,這些計劃既減少了稅收收入,又無法有效實現既定的目標。此外,稅收激勵的過度使用還會導致稅收管理復雜化、逃稅和腐敗的發生。Bird指出,要想使稅收激勵的收益最大化并減少因設計和實施未盡合理的稅收激勵造成的損失,各國至少應堅守以下三項原則[28]:一是盡量簡化。稅收激勵在數量上應盡可能減少,結構上盡可能簡單。二是對受到激勵的主體、激勵的種類以及放棄的收入成本進行追蹤。如果激勵的意圖是實現某種特定目標,則還須采用可度量的結果反映既定目標的實現情況。三是定期評價稅收激勵的結果與成本。如果二者不相匹配,則應取消。為保證稅基的可獲得性,合理的政策選擇是對稅收激勵項目進行更好管理。
3.強化商品稅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相對于商品稅而言,所得稅具有更明顯的可觀察性,這也使得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大部分有關稅收分配職能的討論主要集中于個人所得稅。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個人所得稅表現出如下特征:一是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結構中所占比重較小。二是個人所得稅納稅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偏低。三是主要通過對工資進行源泉扣繳取得收入。四是能夠有效征收個人所得稅的稅基范圍相對狹窄[29]。此外,在發展中國家,累進稅制對企業和個人行為的影響也比在發達國家中更為明顯——納稅人對稅收制度的信任程度因所得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而降低,逃稅和避稅行為的增加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稅收管理成本和遵從成本偏高。實踐表明,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累進綜合個人所得稅可能不是實現收入分配職能的最優策略。①實踐表明,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無論從財政收入、經濟增長還是收入分配角度看,實施該策略的成本和風險相對于成功的機會而言都顯得過高。那些試圖在發展中國家完成這項工作的人最后都放棄了傳統教科書中的觀點,即將綜合累進個人所得稅作為稅制支柱的建議[30]。
從稅收結構上看,發展中國家的商品稅比個人所得稅占有更高的比重,因而可能產生更為重要的收入分配效應。在稅制改革的推進過程中,有必要對商品稅的設計和實施予以更多關注。在非正式經濟活動占比較高的情況下,盡管那些完全采用現金交易的企業和個人逃避了所得稅和銷售中的增值稅,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購買正式部門提供的消費品和服務。由于無法抵扣投入品的增值稅額,因此這些經濟活動主體最終還是繳納了增值稅。從這個意義看,課征商品稅是對非正式部門征稅的理想方法。實現商品稅的收入分配作用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對機票、賓館房間以及高價酒精飲料等富人消費比例更高的商品課稅。二是規定對某些基本的食物免稅。稅收可能無法使窮人變得更富有,卻能夠使他們更貧困。因此,應當避免對構成貧困人口基本需要和占消費支出主要部分的項目課以重稅。雖然貧困人口并不是這些基本食物產品的全部消費者,換言之,部分減免收益會被一些非貧困人口取得,但減免措施的設計仍將對收入分配產生積極影響——在低收入群體的開支中,生活必需品占有較大比重,因而對生活必需品的稅收減免可以通過減少低收入階層開支的方式達到相對提高其可支配收入的效果。②一項對牙買加稅制的研究表明,僅對一些主要的食物項目免稅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低收入家庭的稅收,并使增值稅具有輕微的累進性[31]。
4.完善稅收管理
稅收管理的有效實施包含三個要素:對稅制進行有效管理的政治意愿、實現這一目標的戰略措施以及完成該項任務的充分資源。其中,資源問題如需要訓練有素的稅收管理人員、充分的信息技術等通常最受關注。但是,離開有效的實施策略或者沒有足夠的政治支持,即使充分的資源也無法保證稅收管理的有效實施。
極少有政治家愿意接受由稅收政策和稅收管理改革帶來的經濟和政治成本。在取得收入的同時,各國政府都盡力避免傷害政治上處于強勢地位的群體的利益。如果政治愿望存在,實施有效稅收管理的目標和方案就相對明確。稅收管理應采用適當的制度形式,配備經過充分培訓的稅務人員,進行合理的組織,建立基于職能或客戶群的組織結構。在這一過程中,大規模的信息歸集和整理通常要求稅務機關從納稅人、相關第三方以及其他政府機構取得信息,并及時予以處理,因此計算機化以及現代信息技術的合理使用非常重要。但是,單純依靠技術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其與稅收管理制度細致地加以整合。
值得注意的是,提高稅收遵從并不等同于抑制不遵從。現代稅收管理方法的基點是將納稅人假定為接受服務的顧客(盡管納稅人可能并不情愿),而不是被抓捕的竊賊。對納稅人行為的研究結果表明,提供使納稅人更為便利的申報、填寫和納稅等服務,或者教育并使納稅人了解有關自身依法履行納稅義務的信息在保障遵從方面通常要比直接用于治理不遵從的措施(稽查、懲罰)更有效[32]。從另一方面看,低遵從度可能是高遵從成本、稅收與利潤之間缺乏必要聯系以及對稅收公平的理解等基本問題的函數。稅收管理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防止不遵從趨勢的蔓延。為實現這一目標,不僅要使不遵從的實現變得更加困難,還要使稅收遵從更加易于實現[33]。因此,為納稅人簡化納稅程序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去掉納稅申報表中要求填寫的冗余信息。
由于納稅人并不都是誠實的,因此稅收管理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進行稅務稽查以使納稅人減少逃稅。為實現這一目標,稅務機關必須掌握潛在稅基的范圍和性質。如果對未申報稅基及其決定因素缺乏了解,稅務機關就不能將管理資源合理地用于稅收征管,無法確保稅制規定的納稅人及時繳納稅款和稅收負擔在納稅人間相對公平地分配。對于未能按時繳納稅款的納稅人,必須足額收取滯納金,以保證欠繳稅款不至于成為廉價的財政資源。此外,還要建立完善的處罰體系,以保證應當注冊、申報卻未注冊、申報以及未足額申報稅基的納稅人受到應有的處罰,提高其逃稅成本。
五、結論與啟示
19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實施了以“寬稅基、低稅率、簡稅制”為主要內容的稅制改革,旨在實現減少財政赤字或縮小短期收支缺口、降低稅收成本和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目標。然而,發展中國家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和面臨的約束條件制約了上述目標的實現。首先,規模較大的非正式經濟不僅降低了稅收收入總量,使政府可用于再分配支出計劃的資金減少,而且削弱了個人所得稅的再分配效應。其次,隨著經濟全球化和WTO的推廣以及國外投資競爭的加劇,資本會因稅率的微小變化自由地在各國之間流動,因此,近年來全球個人和公司所得稅稅率都大幅度下降。再次,由于大規模不易課稅的傳統農業部門和大量游離于正式稅收制度之外的非正式經濟的存在,發展中國家有效的潛在稅基僅占經濟活動總體的一小部分。無論通過資本利得稅還是財產稅,對城市和農村不動產的有效課稅仍然處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稅收管理的能力之外。最后,盡管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重視中央以下各級政府在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中的作用,但迄今為止,財政分權仍集中于支出的分散化,稅收的分散化則明顯滯后。中央政府不愿下放征稅權,中央以下各級政府支出主要依靠轉移支付籌資。這種模式割裂了地方政府支出決策與稅收之間的聯系,使地方與更高級次政府間關于地方公共項目補貼規模和形式的談判結果成為決定地方公共服務范圍和水平的關鍵因素。
發展中國家稅制改革的經驗對我國稅制優化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價值。首先,為保障納稅遵從和減少稅制改革面臨的政治阻力,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稅收收入與政府支出水平之間的聯系,使納稅人相信他們繳納的稅收得到了相應的回報。在我國“自上而下”、強調中央政府宏觀調控和保證中央政府財力的分權模式中,中央政府沒有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稅收自主權,而是希望通過轉移支付實現財政分權目標。因此,在支出分權化條件下,為提高中央以下各級政府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供過程中的自主性、有效性和責任感,改變現行的收入分成制,采用稅率分享制,使中央以下各級政府能夠與中央政府相對平等、規范地分享某些大型稅基(如消費稅、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課稅權可能是更為可行的辦法。其次,為使征稅的非必要成本最小化,應盡可能減少稅收優惠的數量,以保證稅基的廣泛性。建立稅式支出預算,定期評價稅收優惠的結果與成本,通過制定落日條款規定稅收優惠繼續實行下去的評估條件并按年度提供稅收支出評估報告。再次,為改善稅制的公平性,我國個人所得稅在實現由分類制向綜合制的轉變之前,應進一步調整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的稅負水平。為體現生計扣除的科學性和家庭稅負的公平性,應當按照納稅人家庭人口數量和就業狀況對費用減除標準加以細分。在商品稅改革中,可以考慮對農業生產資料以及低檔服裝、嬰幼兒食品和用品以及普通藥品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免征增值稅;調整營業稅稅率,對與低收入群體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服務項目實行低稅率或予以免稅;將更多奢侈品納入消費稅的征收范圍,以擴大消費稅的稅基。最后,在稅收管理上,一方面要為納稅人提供更為便利的申報、填寫和納稅等服務,或者教育并使納稅人了解有關自身依法履行納稅義務的信息以保障納稅遵從;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處罰體系,對于未能按時繳納稅款的納稅人,必須足額收取滯納金,以增加逃稅成本,保證欠繳稅款不至于成為廉價的財政資源。
[1]Morisset,J.,Izquierdo,A.Effects of Tax Reform on Argentina's Revenues[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 1192,1993.
[2]Bergman,M.Tax Reforms and Tax Compliance:The Divergent Paths of Chile and Argentina[J].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03,35(3):593-624.
[3]Mann,A.J.Estimat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sts of Taxation:A Methodology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Case of Guatemala[M].DevTech Systems Inc.,2002.
[4]Evans,C.Studying the Studies:An Over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Taxation Operating Cost[J].e - Journal of Tax Research,2003,1(1):64-92.
[5]Chattopadhyay,S.,Das- Gupta,A.The Compliance Cost of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and Its Determinants[M].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and Policy,2002.
[6]Rutkowski,J.J.Taxation of Labor[A].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C].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7.281 -313.
[7]Becker,L.A.,Spicer,M.W.Fiscal Inequity and Tax Evasion: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J].National Tax Journal,1980,33(2):171-175.
[8]Cowell,F.A.Tax Evasion and Inequity[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1992,13(4):521 -543.
[9]Falkinger,J.Tax Evasion,Consumption of Public Goods and Fairness[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1995,16(1):63-72.
[10]Frey,B.S.Deterrence and Tax Morale in Tax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J].European Review,2003,11(3).
[11]Tanzi,V.,Zee,H.Tax Policy for Emerging Markets:Developing Countries[R].IMF Working Paper No.35,2000.
[12]Webber,C.,Wildawsky,A.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6.
[13]Cavanaugh,M.B.Democracy,Equality,and Taxes[J].Alabama Law Review,2003,54(2):415 -481.
[14]Schneider,F.,Enste,D.The Shadow Economy:An International Survey[M].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5]Boskin,M.J.,McLure,C.E.World Tax Reform:Case Studie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M].ICS Press,1990.
[16]Echavarria,J.J.,Zodrow,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Business Tax in Colombia[A].Bird,R.M.,Poterba,J.M.,Slemrod,J.Fiscal Reform in Slemrod,J.Colombia[C].Cambridge MA:MIT Press,2005.153 -190.
[17]Baunsgaard,T.,Keen,M.Tax Revenue and(or)Trade Liberalization[R].IMF Working Paper WP/05/112,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5.
[18]Lindert,P.Growing Public:Social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9]Engelschalk,M.Creating A Favorable Tax Environment for Small Business[A].Taxing the Hard to Tax:Lessons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C].Amsterdam,2004.275-312.
[20]Bird,R.M.,Wallace,S.Is It Really so Hard to Tax the Hard to Tax?The Context and Role of Presumptive Taxes[A].Wallace,S.,Alm,J.,Martinez-Vazquez,J.Taxing the Hard to Tax:Lessons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C].Amsterdam,2004.121-158.
[21]Bahl,R.,Martinez- Vazquez,J.,Youngman,J.Making the Property Tax Work[M].Cambridge MA: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2008.
[22]Bahl,R.,Wallace,S.Public Finance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J].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2005,25(4):83-98.
[23]谷成.財政分權下政府間稅收劃分的再思考[J].財貿經濟,2008,(4):74-78.
[24]谷成.財產課稅與地方財政——一個以稅收歸宿為視角的解釋[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5):73-78.
[25]Bastable,C.F.Public Finance[M].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32.
[26]Breton,A.Com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s Theory of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7]Emran,M.S.,Stiglitz,J.E.On Selective Indirect Tax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599 -623.
[28]Bird,R.M.Tax Incentives for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Fiscal Reform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Palgrave Macmillan,2000.201-221.
[29]谷成.稅收與收入分配:基于發展中國家個人所得稅的思考[J].經濟管理,2010,(7):153-159.
[30]Bahl,R.,Wallace,S.Comprehensive Tax Reform in Jamaica[J].Public Finance Review,2007,35(1):4 -25.
[31]Edmiston,K.D.,Bird,R.M.Taxing Consumption in Jamaica[J].Public Finance Review,2007,35(1):26 -56.
[32]Slemrod,J.Why People Pay Taxes:Tax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2.
[33]Torgler,B.Tax Compliance and Tax Morale: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