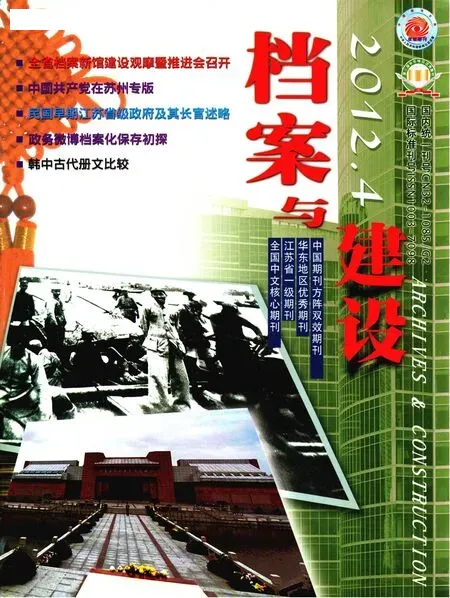“蘇南模式”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
張秀芹(蘇州市委黨史辦,江蘇蘇州,215004)
上世紀70、80年代,蘇南的蘇錫常農(nóng)村依靠緊鄰上海大城市的區(qū)位優(yōu)勢和歷史傳統(tǒng),大力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探索出一條農(nóng)村發(fā)展途徑。1983年2月5日,鄧小平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江蘇蘇州等地考察,2月6日下午抵達蘇州。第二天,鄧小平就約見陪同考察的江蘇省委原第一書記江渭清、省長顧秀蓮以及蘇州地委、市委的負責(zé)人等,聽取匯報。談話一開始,鄧小平就問:“到2000年,江蘇能不能實現(xiàn)翻兩番?”江蘇的同志回答: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時間,就有把握實現(xiàn)翻兩番。鄧小平又問蘇州的同志:“蘇州有沒有信心,有沒有可能?”江蘇的同志告訴鄧小平:像蘇州這樣的地方,我們準備提前5年實現(xiàn)中央提出的奮斗目標!鄧小平接著問:“人均800 美元,達到這樣的水平,社會上是一個什么面貌?發(fā)展前景是什么樣子?”蘇州的同志告訴他,若達到這樣的水平,下面這些問題就都解決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問題解決了,人均達到20 平方米;第三,就業(yè)問題解決了,城鎮(zhèn)基本上沒有待業(yè)勞動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農(nóng)村的人總想往大城市跑的情況已經(jīng)改變;第五,中小學(xué)教育普及了;第六,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犯罪行為大大減少。”
聽了這些介紹,鄧小平很振奮,繼續(xù)追問:“蘇州農(nóng)村的發(fā)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江蘇的同志告訴他,主要靠兩條:一條是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依靠技術(shù)進步。還有一條是發(fā)展了集體所有制,也就是發(fā)展了中小企業(yè);在農(nóng)村,就是大力發(fā)展社隊工業(yè)。江蘇的同志匯報說,蘇州的社隊工業(yè)之所以能夠快速發(fā)展,歸根結(jié)底,憑借的是靈活的經(jīng)營機制,實行的是市場經(jīng)濟體制。聽了這番話,鄧小平說:“看來,市場經(jīng)濟很重要!”這是從實踐上高度肯定發(fā)展農(nóng)村工業(yè)對于推動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重大作用。
1983年10月3日至8日,費孝通第七次訪問江村。除了參觀村絲織廠和繅絲廠外,還到附近的震澤、梅堰等鄉(xiāng)鎮(zhèn)進行調(diào)查,同與村辦企業(yè)橫向聯(lián)營的蘇州光明絲織廠和蘇州益明化工廠的負責(zé)人座談城鄉(xiāng)工業(yè)合作關(guān)系問題;參加了吳江小城鎮(zhèn)研究會成立大會并擔(dān)任該會名譽會長,聽取家鄉(xiāng)小城鎮(zhèn)研究和改革試點工作的情況匯報。費孝通深刻指出農(nóng)村工業(yè)經(jīng)濟的繁榮是小城鎮(zhèn)復(fù)蘇的原因,他還就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與大中城市的企業(yè)聯(lián)系,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向,商品流通、家庭副業(yè)、集鎮(zhèn)建設(shè)規(guī)劃、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等問題發(fā)表了意見。他的《小城鎮(zhèn)再探索》一文是這次考察的總結(jié)。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模式”一詞和“蘇南地區(qū)模式”(蘇南模式)。費孝通用“蘇南模式”概括蘇南地區(qū)發(fā)展經(jīng)濟的路子,開始從理論上研究發(fā)展農(nóng)村工業(yè)的普遍意義。
“蘇南模式”興起的動因是什么?首先,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的動力來自農(nóng)村內(nèi)部。“蘇南模式”的出現(xiàn)有其歷史必然性。農(nóng)村要辦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的深層次原因,是當時農(nóng)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需要尋找出路。家庭承包責(zé)任制普遍實行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怎樣把大批農(nóng)民從土地上轉(zhuǎn)移出來,是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的關(guān)鍵問題。顯然,就地辦工業(yè),是農(nóng)民自己找到的一條“活路”。費孝通指出,中國農(nóng)民找到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的道路是“逼上梁山”。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是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以新的勞動手段與新的勞動對象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但也有人對農(nóng)民辦工業(yè)很不以為然,“有人說社隊工業(yè)挖了社會主義的墻腳,是不正之風(fēng),是資本主義復(fù)辟的溫床,各種帽子都有,問題提得很嚴重。”這種僵化與保守的觀念,沒有阻擋得了農(nóng)民辦工業(yè)的潮流。費孝通明確支持社隊工業(yè)的發(fā)展,旗幟鮮明地說過:“中國的草根工業(yè)如今長成參天大樹,實在是億萬農(nóng)民長期艱苦奮斗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成果。作為一名社會學(xué)工作者,有責(zé)任對他們的實踐活動做點理論性的分析和總結(jié),并在輿論上給予支持。”
蘇南地區(qū)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的實踐,開創(chuàng)了我國特有的農(nóng)村工業(yè)化模式。費孝通在三訪江村時指出,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多種多樣的企業(yè)不應(yīng)當都集中在少數(shù)都市里,而應(yīng)當盡可能地分散到廣大的農(nóng)村里去,我稱之為‘工業(yè)下鄉(xiāng)’”。工業(yè)下鄉(xiāng)同樣可以在國家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中增加工業(yè)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卻不致過分集中,甚至可以不產(chǎn)生大量脫離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勞動者。在這個意義上,為具體實現(xiàn)工農(nóng)結(jié)合,或消除工農(nóng)差距的社會開辟了道路。在農(nóng)工相輔、共同繁榮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農(nóng)村工業(yè)化、城鄉(xiāng)一體化,這可能是中國的工業(yè)化進程不同于西方工業(yè)國家發(fā)展模式的一個基本區(qū)別,也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可行道路。
費孝通認為:“由于這些地方工業(yè)辦得好,因而富裕起來的鄉(xiāng)村,農(nóng)副業(yè)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斷降低,這個事實應(yīng)當大書特書。中國社會基層的工業(yè)化是在農(nóng)業(yè)繁榮的基礎(chǔ)上發(fā)生、發(fā)展的,而且又促進了農(nóng)業(yè)發(fā)展,走上現(xiàn)代化的道路。”這個特點的重要意義,只要和西方早年工業(yè)化歷史相對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歐洲工業(yè)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機器工業(yè)興起的同時,農(nóng)村卻瀕于破產(chǎn),農(nóng)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離鄉(xiāng)涌進城市,充當新興工業(yè)的勞動后備軍。資本主義國家現(xiàn)代工業(yè)的成長是以農(nóng)村的崩潰為代價的,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工業(yè)化道路。與此相比,我國農(nóng)民在農(nóng)業(yè)繁榮的基礎(chǔ)上,以巨大熱情興辦集體所有制的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這種工業(yè)化的道路是農(nóng)民群眾在實際生活中自己的創(chuàng)造。
農(nóng)村辦工業(yè)、集體經(jīng)濟為主、政府推動,是人們強調(diào)較多的“蘇南模式”初期的重要特征。對于蘇南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為什么最初大多以集體企業(yè)形式出現(xiàn),一直是人們關(guān)注的問題。有人把這種現(xiàn)象歸結(jié)為“思想保守”、“模式終結(jié)的原因”。這是缺乏正確歷史觀的看法。
蘇南農(nóng)村集體的農(nóng)業(yè)原始積累,已經(jīng)達到傳統(tǒng)行業(yè)中創(chuàng)辦企業(yè)所需的資本預(yù)付規(guī)模。蘇南以集體積累孕育起來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必然是集體所有制,可以把它稱之為“社隊共有制”。同時,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之初尚處于計劃經(jīng)濟時期,人們對于興辦集體所有制企業(yè)比較容易接受。因而,“村村點火,隊隊冒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蘇南大地上率先發(fā)展了起來。
蘇南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初期受到了強有力的行政推動。當年從公社主任、鎮(zhèn)長到縣長,都缺少經(jīng)費搞建設(shè)與福利項目,不辦工業(yè)則地方財力過弱。他們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chǎn)資料,將能人和社隊資本結(jié)合起來,依靠“政府信用”從銀行取得貸款。沒有計劃指標,他們就帶領(lǐng)農(nóng)民找市場、造市場,沖破計劃經(jīng)濟的層層障礙,自找門路解決原材料短缺等問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起來以后,不僅增加了農(nóng)民務(wù)工經(jīng)商的就業(yè)機會與收入,鄉(xiāng)鎮(zhèn)政府還可以利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部分利潤,增加行政、教育與福利經(jīng)費,承擔(dān)一些政府與社會的職能。
“蘇南模式”的實質(zhì),是一種新的工業(yè)化模式。西方傳統(tǒng)工業(yè)化的道路,是“城市——工業(yè),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不僅搞農(nóng)業(yè),也發(fā)展工業(yè),這是出現(xiàn)在蘇南地區(qū)的一種新生事物。我國是個農(nóng)業(yè)大國,農(nóng)村辦工業(yè)是加速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向工業(yè)經(jīng)濟轉(zhuǎn)變的重要途徑。正如黨的十四大報告所說:“是中國農(nóng)民的又一偉大創(chuàng)造”。
90年代以來,“蘇南模式”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戰(zhàn)。一是買方市場的出現(xiàn),使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與產(chǎn)業(yè)升級的壓力加大;二是所有制結(jié)構(gòu)比較單一,使經(jīng)濟體制與經(jīng)濟增長的活力減弱。蘇南地區(qū)的對策思路與實踐,是以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為動力提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競爭力。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第一步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是興辦合資企業(yè),通過利用外資加快自身發(fā)展。吸取浦東開放開發(fā)的啟示,江蘇與新加坡共建蘇州工業(yè)園區(qū),大力發(fā)展蘇州、無錫、常州等高新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以及自費建設(shè)昆山經(jīng)濟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出現(xiàn)了令人稱羨的實際利用外資的“蘇南速度與規(guī)模”。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大規(guī)模利用外資,進一步打開了國際市場,提高了整體素質(zhì),加快了向現(xiàn)代企業(yè)轉(zhuǎn)變的步伐。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第二步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是實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與轉(zhuǎn)讓。1999年,蘇南地區(qū)的中小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全面完成了改制,2000年大中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并組建了一批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集團。一些村辦小廠發(fā)展起來的集團公司,主動與跨國公司實行成熟技術(shù)、先進技術(shù)的動態(tài)合作,走到了國際科技前沿。一些集團公司重視自主開發(fā),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
蘇南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通過二次創(chuàng)業(yè),增強了企業(yè)內(nèi)部發(fā)展動力,自主經(jīng)營、自主約束的運行機制初步建立,整體上實現(xiàn)了自我突破與超越,再創(chuàng)輝煌。以資本經(jīng)營聞名全國的“江陰板塊”,逐步發(fā)展到22家上市公司,在境內(nèi)外募集巨額資金,成為我國資本市場上一道亮麗的風(fēng)景線。
同時,蘇南模式發(fā)生了全面的創(chuàng)新,個體私營經(jīng)濟大發(fā)展。2004年6月,蘇州民營經(jīng)濟注冊資本達到1150 億元,是溫州的2.4 倍。從而形成個人、社會法人、外商等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新格局,相應(yīng)地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就業(yè)機會。1990年,江蘇省流動人口130 萬人,其中省外流入52 萬人,省內(nèi)流動78 萬人;2005年,江蘇省流動人口1532 萬人,其中省外流入422 萬人,省內(nèi)流動1110 萬人。蘇南地區(qū)吸納的流動人口在全省最多。外來務(wù)工人員80%左右集中在蘇南地區(qū);經(jīng)商人員60%左右集中在蘇南地區(qū),15%以上在蘇中地區(qū),20%以上在蘇北地區(qū);服務(wù)人員65%左右集中在蘇州、南京與無錫等蘇南三市。
蘇南區(qū)域經(jīng)濟本身處于不斷開拓與發(fā)展過程之中,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率先發(fā)展的典范之一,無疑“做模式”是一種成功的實踐。而“寫模式”卻出現(xiàn)了一些不同的觀點,“蘇南模式”經(jīng)常被拿來同“溫州模式”比較,先是“揚蘇抑溫”,后又“揚溫抑蘇”。其實,從集體辦廠到民營經(jīng)濟、從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到中外合資、從粗放加工到高新產(chǎn)業(yè)、從代價過大到重視綠色GDP,“蘇南模式”并不是一個靜止與固定不變的模式,而是一直在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