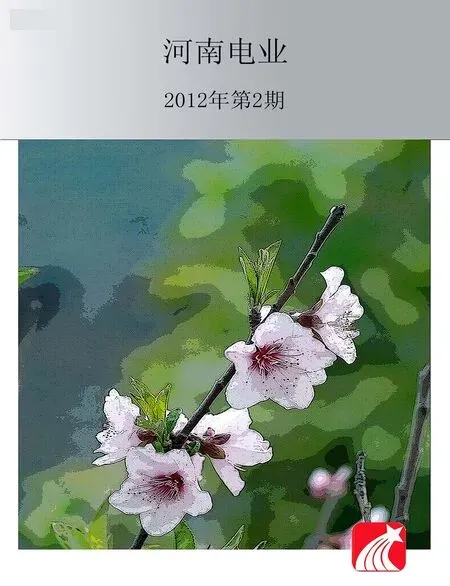治堵的車聯網堵在哪兒
_黃金萍
隨著全國“兩會”的臨近,關于交通擁堵的話題讓“車聯網”概念再次浮出水面。
這個陌生的名詞首次露面是在2010年10月28日,無錫舉行的中國國際物聯網大會上傳出風聲,“車聯網”項目將成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第三專項的重要項目,預期2020年實現可控車輛規模達2億輛。
這個消息在第二天引發了銀江股份等相關公司的股價暴漲。但很快,在投資者還沒搞明白這個概念之前,傳聞就煙消云散了。
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教授史其信對此感到很惋惜,他認為,如果能夠以治堵為背景推動車聯網立項,或許用不了幾年就可以推動車聯網建成。
實際上,車聯網概念所描繪的是一幅汽車與信息技術相結合的遠景——裝有電子傳感裝置的汽車,可以與其他車輛、城市智能交通系統實現在一個平臺上的信息共享,從而實現解決城市擁堵等多種目的。
車聯網背后是汽車制造商、車載終端企業、電信運營商、交通信息內容運營商及服務商等組成的一長串產業鏈條。但這個鏈條為何遲遲難以搭建?
僅僅走出第一步
中國公眾對車聯網的最早認知,要歸功于通用汽車。那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通用汽車館內一個短片,講述了通用汽車對2030年交通的展望——電動汽車各行其道,隨時找地充電,車內觸屏終端接收交通、通訊信息,停靠后汽車自己進停車場。此間,通用汽車還辦了一個名為Mobility Internet的論壇。
通用汽車中國汽車研究院院長杜江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Mobility Internet的中文譯名就叫車聯網。
雖然車聯網提供的是全方位解決車與車、車與路、車與人關系的系統方案,但目前最熱的還僅僅是解決車與人關系的車載產品。杜江陵表示,這得益于車載產品此前十多年的發展,技術和市場相對成熟。
通用旗下的汽車采用的就是其與上汽合資的上海安吉星公司的產品——這個車載終端通過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和無線通信技術為車主提供碰撞自動求助、路邊救援協助、全音控免提電話、實時按需檢測和全程音控導航等服務。
美國人江海德在2007年獲知自己要來中國上任,籌建安吉星在中國的合資公司。他回憶說,當時很興奮,因為中國汽車市場發展很快,這對自己、對安吉星都是很好的機遇。
上海安吉星最早于2009年12月開始向凱迪拉克車主提供服務,豐田汽車則在這半年之前將G-Book引入中國——他們不約而同選擇了中國作為第一個海外市場。
除了安吉星、豐田的G-Book等車載終端,三星電子和現代汽車,華泰和英特爾,長安、吉利汽車也與電信運營商展開了跨界合作。由科研機構、車商、IT廠商主導的無人駕駛試驗也在進行中,這預示著汽車將不僅僅是一件工業產品,更是一件科技產品,汽車廠商將不僅是汽車產品供應商,也是服務供應商。
但現在這些車載產品充其量也只是一個誘人的賣點而已。車載終端一個重要應用是導航,而它面臨的尷尬是目前只能提供靜態信息。在車聯網的大系統中,車載產品僅僅走出了第一步。而整個車聯網的搭建,則要依托城市智能交通系統的建立及信息共享。
將希望寄托于政府?
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教授史其信一直在推動車聯網的進程。1995年,他和外國學者交流時,第一次聽說了智能交通這個概念,隨后開始研究,并出現在智能交通國際會議上,成為最早在中國倡導智能交通的人。他現在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智能交通技術委員會主任。
1997年4月,中國第一次智能交通大會在北京召開。史其信至今還記得自己作為大會主席的發言內容。1999年,他用課題經費辦了《ITS通訊》雜志,自己約稿自己編,介紹國內外智能交通情況,后因拿不到正式刊號,不得不在7年后放棄。
他一直將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1997年第一次智能交通大會上,史其信就在呼吁將智能交通列入國家計劃。2002年開始,中國政府確實開始從國家層面推動智能交通研究,在“十五”計劃中立了兩個重大專項。
但效果并不明顯。以RFID(電子標簽)為例,企業一直找不到產業化的著眼點。大多數企業從工信部、科技部拿到扶持資金后,轉身買國外的芯片,然后做一些二次開發、應用而已,最后仍然缺乏核心技術。
一個地方一年要開四五次會議討論智能交通,史其信趕場般走下來,“我發現我們走歪了,企業一窩蜂地上來發展,其實是不健康的。”
2004年,史其信向國家信息產業部門建議,搞國家汽車計算平臺工程,即類似今天的車聯網平臺。他認為,這不僅是為了解決交通問題,還因為未來是智能汽車時代,而汽車電子是智能汽車的關鍵。建好這個平臺,正好可以幫助中國汽車工業翻身。但他的這個計劃沒有得到回應。
按照史其信的設計,車聯網有三層,第一是感知層,就是RFID等感知系統,這是很多企業正在做的,也是最簡單的層面;第二層是互聯互通,即車與車、車與路互聯互通;第三層是通過云計算等智能計算,調度、管理車輛。
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現在很多企業還處在車聯網最前面的部分,做第二層的少,第三層就更不用說了。事實上,沒有政府的配合,企業是很難介入后兩個層面的。
智能交通的共享難題
2010年10月28日,無錫會議傳出車聯網重大專項立項消息之后,創業板上的銀江股份第二天立刻漲停。這家前身為電子貿易公司的企業,2009年在創業板上市時打上了物聯網概念的標簽,智能交通業務是其收入中最大的一塊。
在杭州市的智能交通應用中,銀江股份的占比高達90%,可以說是銀江智能交通的最好試驗場,卻也不能免于交通擁堵的厄運。銀江股份首席技術官吳越苦笑著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智能交通并不能根治交通問題,但可以緩解。
但真正的問題在于,智能交通需要實現信息共享,而在上海、杭州等城市,雖然已經實現了智能交通路況信息采集,并發布在路面信息牌上,但人們只能到了相應路段才能看到,而無法事先獲取。如果能夠把數據庫接口公開,讓這些交通信息變成社會公共資源,讓車載終端實時接受,車主即可據此調整線路,自動疏導交通。
在銀江的智能交通業務中,同樣也有不同平臺之間不對接的問題。他們承接的平安城市項目,屬于公安系統,而交通誘導項目,則屬于交通部門。這既有重復投資的嫌疑,兩個平臺上獲取的數據也都不完整。
吳越相信,基于產業發展和民生問題的考慮,政府遲早會把這兩個平臺打通。從技術上說,交通信息數據既然可以出現在路面誘導牌上,當然也可以出現在車載終端上。
在銀江股份承接的杭州BRT系統中,為了保證快速公交車準時到站,在快速公交車通行道路上,實現車輛與交通燈之間的感應及紅綠燈時間間隔調節,就是由政府出面打通的。
此外,銀江股份也試圖聯通停車場,將車位信息實時化。這樣,車主在半路上就可以知道目的地的車位情況。雖然在個別停車場有過成功的智能化應用案例,但大多數停車場仍對此缺乏合作的動力。原因是,一方面停車場各有利益訴求,聯合不起來;另一方面車上必須要有一個接受終端才能實現車位信息的實時更新。
雖然車聯網搭建困難重重,但好消息是,越來越嚴重的城市擁堵困境,讓很多城市對智能交通系統產生了興趣。南京市政府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全市智能交通項目建設的意見》,廈門絕大多數車輛已經打上了電子標簽,北京、廣州、武漢、深圳、上海等城市也都提出要打造智能交通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