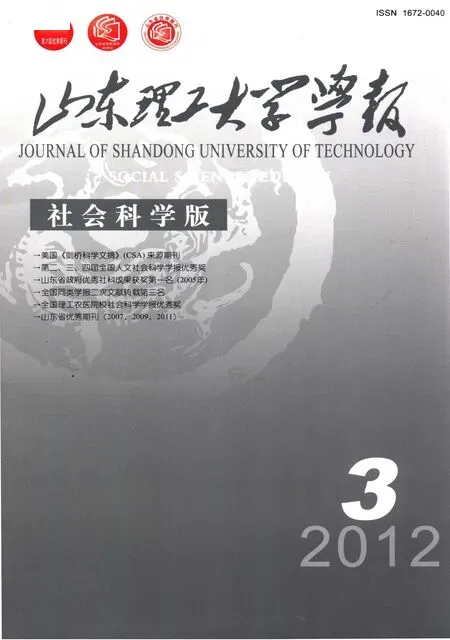書法產業(yè)化背景下為展覽而創(chuàng)作的偏失
馬鴻民
(天津商業(yè)大學藝術學院,天津300134)
一
“書法產業(yè)化”是近兩年提出的新詞語、新概念。“產業(yè)”本屬經濟學范疇。當書法藝術已經不僅僅作為欣賞用途,還衍生出分類詳盡的藝術創(chuàng)作、教育培訓、作品展覽、銷售、收藏、拍賣、投資等多方面的配套產業(yè)時,“書法產業(yè)化”便風生水起了。
書法產業(yè)化實現是以書法創(chuàng)作、展覽、代理、宣傳、營銷、拍賣、收藏、投資等為關節(jié)點的配套產業(yè)鏈,在相關法律法規(guī)制約監(jiān)管下進行有序的市場化運作,被認為是21世紀中國書法的發(fā)展方向。當今社會工業(yè)化的生產模式和大眾性的消費模式是藝術產業(yè)的主要運作模式。藝術產業(yè)與生俱來的雙重身份決定了它要受到藝術、經濟這兩個領域雙重運動規(guī)律和發(fā)展邏輯的作用。書法藝術作品的豐富的價值特性,不僅取決于作品本身,更取決于包括經濟、文化、政治、道德在內的社會性話語的介入。“經濟話語對藝術的介入、滲透與覆蓋,就是在藝術與社會生活前景中愈來愈突出的一種歷史現象”。[1]334在西方,從古羅馬、文藝復興時期的寄食制,到十八、十九世紀的國家資助,再到20世紀的企業(yè)基金支持,不少藝術家得以摒棄公眾和流行作為價值標準,與此同時,對讀者、觀眾等藝術公眾和藝術市場的依賴也與日俱增,并逐漸成為富有生命力的新的藝術文化話語。“這倒不是說這之中在藝術內部有強烈的經濟動機,而是說,是日益發(fā)展的社會現實在事實上把一種商品化的無選擇性的處境交給了整個世界,交給了別無選擇的藝術家”。[1]337
任何藝術是否具有社會價值和具有何種社會價值,決定著這種藝術的存在形式和發(fā)展狀態(tài)與前景。書法藝術走向市場,實現產業(yè)化是藝術家們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的問題。這種情況和環(huán)境也促進了書法創(chuàng)作主體思想解放和價值觀念的變化。社會的發(fā)展使人們的生存內涵得到豐富,人性的自然性、社會性和實踐性得到結合統一,書家的個性得以張揚,將時代氣息自然地融進書法。書法從單純的士文化、雅藝術審美形式,逐漸過渡為一種大眾娛樂方式和消遣方式,并由過去的士文化、雅藝術,向大眾文化、通俗藝術轉變,從精英文化向民間化、大眾化,分流、發(fā)展,書法受眾日益擴大。
中國書法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其涵蓋范圍不僅僅是書法創(chuàng)作過程、創(chuàng)作群體、展賽活動等小圈子,而應指向更廣范圍的文化的、社會的意蘊,應輻射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角落。書法業(yè)內各種活動被引入產業(yè)化范疇,使各類書法展賽及書法相關各類活動與“產業(yè)”、“市場”結合,在文化產業(yè)大背景下書法展賽、研討、雅集、會議等活動的內容、形式上尋求探索與革新,這對書法的發(fā)展和藝術價值的體現是有現實意義的。
二
書法產業(yè)中的供求流通體系由生產、推介、營銷、接受等主要鏈環(huán)構成。生產方由書法創(chuàng)作個體、群體等構成;推介供銷部分包括展覽、展廳、文化推廣等;接受終端指廣大的書法需求方以及社會上與書法相關的消費需求方。其中展覽是書法產業(yè)的重要一環(huán),對推動書法產業(yè)化作用異常凸顯。
雖然經濟貿易類展覽也具有傳播功能和作用,可以被用作傳播媒介,但是就其根本作用和性質而言,經濟貿易類展覽是一種特殊的市場。書法展覽是一種特殊的交流方式和傳播媒介,通過書法展覽使得受眾與發(fā)送出來的藝術信息完成面對面交流與溝通。隨著整體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改變,書法從私人空間走向公眾空間,展覽作為一種全新、優(yōu)質的展示方式,成為當代展示書法的必然選擇。書法展覽一方面成為作者向社會展示其作品的最佳途徑;但另一方面書法展覽也左右了作者的創(chuàng)作理念,進而影響公眾的審美價值取向。
雖然書法展覽是一種展覽性傳播,但隨著書法產業(yè)化的展開,書法展覽的市場特性越發(fā)凸顯,這充分體現展覽是經濟交換(流通)的一種形式,展覽曾是人類經濟交換的主渠道現在仍是重要渠道之一。書法展覽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古已有傳承有序的文人“自娛式”的創(chuàng)作觀,讓書法在創(chuàng)作上更加注重“藝術表現”與“市場效應”;而且“表現與市場”往往相互生發(fā),只有上佳的“表現”,才能有豐厚的“市場”回報。
無論怎樣,藝術和藝術家的意義總存在于其藝術活動和現實、歷史、傳統的相關性之中,我們雖然不必說經濟規(guī)律強制性地支配著藝術觀念與行為,但藝術與環(huán)境、藝術與社會的密不可分的聯系,是不能否認的。在商品時代,藝術家受制于社會功利氛圍,在社會的經濟的壓力誘使驅促下,努力使自己的觀念合乎公益世界與經濟規(guī)律,也是極其自然的。“即使是在一種與世隔絕的審美靜觀的狀態(tài)中,也并不意味著它真的是與世隔絕的。因此,當我們考察整個知覺系統時,所謂的與世隔絕很難具有實質性意義、在決定性的水準上它其實并不存在”。[2]345
三
書法從古代文人小范圍內的展示,到當代大型展覽,書法所處的文化環(huán)境已經發(fā)生根本上的變化。新的傳播方式必然對書法創(chuàng)作進行反向的引導和影響。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中的許多根本性問題,都是與書法傳播方式的市場化乃至整個文化環(huán)境息息相關。書法展覽的導向正深刻地影響著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以往書法創(chuàng)作中對功力和藝術修養(yǎng)的依賴逐步被作品的表現形式、市場意識的經營所置換。隨之而來的是創(chuàng)作觀念、心態(tài)、目的的極大改變。書家將展覽當作檢驗、展示自己書法創(chuàng)作和獲得藝術與市場雙贏的一種主要方式。書法為展覽而創(chuàng)作,為市場而展覽,書法創(chuàng)作重形式表現,而乏功力、缺內涵、少自然,這些都對公眾審美期待和共鳴造成擠壓,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思考。
首先,出于“競技”的性質規(guī)定,出于廣泛地向公眾傳遞信息的宣傳的需要,創(chuàng)作者力爭使自己的作品脫穎而出,因此“形式”被書家推到了歷史以來最自覺的高度以契合“展覽至上”。書法創(chuàng)作的幅式普遍向大幅、巨幅發(fā)展,條屏盛行,追求書法作品幅式的大規(guī)模化。與之相應,小幅作品也為追求展廳效應,劃分若干塊面,上下左右相續(xù)而成大幅。這反映了傳統的幅式(如尺牘、文稿之類)不得不作順應性調整。作品中較多地出現了色紙、框格,多印章,仿古格式,紙張染色做舊等層出不窮。從書體角度看,行書及行草書的藝術表現性較強故而盛行,其書體結構、墨色變化靈活。大篆、甲骨文既因其字形結構意趣多變,亦出于表現形式上的避難從易,也為書家所青睞。具體到書法的筆法、字法、章法、墨法,偏重于形式感強烈奇異的傾向也十分突出。諸如此類,形式表現之潛能得到極大發(fā)掘與發(fā)揮。
創(chuàng)作形式的變更只是一種花樣的翻新,這種為滿足欣賞者視覺暫時愉悅所采取的做法僅僅是表面化的不斷升級,而并非藝術風格的深層次展現。如果“因為那窮奢極侈的人嘗試過一切方式的享受,對他來說不再有什么新的享受了”。[3]140
形式刻意追求折射出功力的缺乏。功力的缺乏和對傳統的漠視,使得諸多展廳作品最基本的筆墨蕩然無存,作品中既沒情感,又無神采,只有僵死的線條。“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4]62神形兼?zhèn)洚敒闀ú欢ㄩT。
藝術創(chuàng)作需要長期的技巧法度訓練和對傳統精神的把握,僅靠外在形式的新穎,無異于買櫝還珠。歌德認為“見識和實踐才能要區(qū)別開來,應該想到,每種藝術在動手實踐時都是艱巨的工作,要到純熟的掌握,都要費畢生的經歷”。[5]79唐代孫過庭認為自己“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昧鐘張之馀烈,挹羲獻之前規(guī),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4]125顯然當今絕大多數書法實踐者缺乏對功力積累的重視。明代書論家馮班在《鈍吟書要》中說:“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功夫細也”。[4]551
歌德在1825年談到當時的藝術創(chuàng)作的現狀時認為:學習先于創(chuàng)作,應集中精力搞專業(yè)。“如果盡早使每個人都學會認識到世間有多么大量的優(yōu)美的作品,而且認識到如果想做出能和那些作品媲美的作品來,該有多少工作要做,那么,現在那些做詩的青年,一百個人之中肯定難找到一個人有足夠的勇氣、恒心和才能,來安安靜靜地工作下去,爭取達到已往作品的那種高度優(yōu)美。有許多青年畫家如果早就認識和理解到象拉斐爾那樣的大師的作品究竟有什么特點,那么,他們也早就不會提起畫筆來了”。[5]77這段話對今天的書法創(chuàng)作仍然具有現實針對性。
其次,任何一門藝術必然涉及到內容和形式。席勒在談到二者的關系時說“目的和形式之間,關系極為密切。形式由目的決定,并由目的規(guī)定必須如此,而目的得以實現,則是形式相宜的結果”。[6]50從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來看,藝術家總是先有一定的內容,然后才選取適當的形式,總是先考慮反映什么樣的社會生活,選擇什么樣的題材,揭示什么主題,然后再根據內容的需要,決定采用什么樣的形式來表現。完美的形式,能夠幫助內容的充分表達,增強作品內容的藝術感染力。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藝術家在致力于創(chuàng)作形式時,同時洗練著內容,形式更加完美,內容也更加完善。當我們被某一完美的藝術形式所吸引時,并不覺得僅僅是受到形式的感染,而同時深深意識到包含在形式中的藝術內容。
一味強化展廳效應即視覺刺激的強度,熱衷于書法的形式與技巧,在展廳適應性、迎合性上出奇制勝,勢必會只注重表象而忽視內涵的充實。“高韻深情,堅質浩氣,缺一不可以為書”。[4]713形式、技巧的出新應是藝術家在為表現某種自我精神境界的追求中自然產生的。精神內容貧乏的作品雖然在形式表象上能使觀者在視覺感官刺激上產生一定的新鮮感,但不能從精神意蘊上深深打動觀者。
書法的“高韻深情、堅質浩氣”,主要來自書家個性氣質、道德情操以及所書內容的文學情境和與之相應的情感的共鳴,是書家個性精神與審美理想的藝術表現。如劉熙載所論:“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4]715書家通過毛筆起伏頓挫、輕重徐疾各種變化,產生不同的勢感、形感、質感的線條,從而表達自己的情感、格調、意向和神采。書法的內容是書法家沉積于心靈的“遠取萬物、近取諸身”的體驗,是與書法家的個性、學識修養(yǎng),與當時的情境等有著密切的聯系,還與書法家的功力密不可分。這樣“然后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jié),千古依然”。[4]126也正是基于此,書法才能成為藝術。書法的品位和持久感染力也在于此。
為了掩蓋自身功力的不足和內涵的匱乏,徒以外在形式取悅,以最短的時間出最高成效,當是市場化影響下,尋求耗費少而收益多的經濟學意識的折射。但所有的這一切都在使自己逐漸遠離書法的本真。作品的深沉微妙處只有在靜心品味時才能獲得真切的感受。展覽效應造成了當今書法創(chuàng)作普遍浮躁而熱衷形式效果的取巧傾向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當代展廳書法主要對明清書法,特別是明清大尺幅書法的效仿。明末清初特定歷史時期下,書壇出現了一批個性張揚和不拘成法的書家,他們用書法來抒寫個性自由,展現思想和內心情感,追求奇絕,表現“拙”、“丑”,反對因襲古人,這些極大地改變了人們以往對于書法語言的審美習慣。明清書家創(chuàng)作的成功在于張揚自我的外在形式語言和豐富的內在人文精神內涵,在作品中達到了高度的和諧與統一,藝術表現成為其創(chuàng)作主旨。但他們作品中的“拙、丑”被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強化、夸張。這固然顯示了當代書法審美空間的拓寬,但又往往由于作品內涵的蒼白和功力的缺乏而失之于“丑怪”。
同時,現代書家為追求作品的視覺沖擊力,把西方美術中的藝術構成理論引入書法作品中,肆意制造各種矛盾。正是由于這種刻意的做作,造成對自由意識與自性本真的遮蔽。作品中存在的夸張對比造成的并非康德所說的“崇高使人感動”[7]3的感動。“崇高必定總是偉大的,崇高必定是純樸的”。[7]4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也說:“丑就是不成功的表現。就失敗的藝術而言,有一句看似離奇的話實在不錯,就是:美現為整一,丑現為雜多。”[8]479
當代書法家效仿明清書法,為追求展廳效果與市場效應,把書法作品的分量等同于物質材料的大小,把物質材料的“大”等同于精神的“大”。書法家的創(chuàng)作所選擇幅式的大小應該是一種自然而然、天然默契的選擇,是對幅式大小“度”的恰當把握。書法家對于審美價值的理解決定了他們的創(chuàng)作行為,創(chuàng)作境界決定藝術作品語言形式,進而決定尺幅的大小。一個缺乏駕馭大幅式作品的書法家,其作品所承載的信息必然是消極的、矯揉造作的,無法看到書法家本人的生命體驗。托爾斯泰說:“洞察一己之長,或者更確切地說,洞察非己之所長,這便是主要的藝術。”[9]127書法作品外在的規(guī)定性必須與內在精神層面的因素緊密地聯在一起,欣賞者才能看到作品整體性的效果,感受藝術所帶來的精神愉悅與升華。否則就是孫過庭《書譜》所批評的“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4]125
書法作品說到底是一種精神的產品。書法展覽也好,書法產業(yè)化也罷,書法是精神產品這一點不能被消解。魏晉以來的經典作品大多都是尺幅較小的簡札、冊頁、題跋,雖然簡短,卻體現了作者深厚的筆墨功力,充滿了作者的個性與才情而日久彌新。這些作品是后人無法回避的,甚至是無法超越的。作品中呈現出高遠、深邃、豐富的精神空間,蘊含著創(chuàng)作者興猶未盡的高峰體驗。如南北朝劉勰說:“夫情動而言形,理發(fā)而文現,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10]256作品神采煥發(fā),情趣盎然是許多大幅式作品所不能比肩的。
此外,書法語言講求點線的節(jié)簡含蓄,舒朗通透,避免冗長。在這方面,明清書家創(chuàng)作中大多是繁筆疾書,以展現壓抑、強烈的內心,這已失之于簡靜。當代書法家更缺乏這種簡靜心態(tài),加之功力的缺乏,致使抒情阻礙,疏遠了象征、暗示、隱喻這些書法不可或缺的語言特征。列夫·托爾斯泰在談到藝術創(chuàng)作時說:“樸素,這便是我所希望的比其他一切更緊要的品格。”[9]122清代劉熙載在《藝概》中說:“書能筆筆還其本分,不消閃避取巧,便是極詣。”[4]705此外,中國書畫講求“師法造化,中得心源”、“道法自然”,只有當作品達到了自然的狀態(tài)、是自然的流露時,作品才達到一個較高的層次和境界。再大的尺幅,如果不是自然的表達,而是強意為之,都很難產生持久的感染力。林語堂在闡釋中西藝術精神時說,“西方藝術的精神較為耽于聲色,較為熱情,較為充滿藝術家的自我;而中國藝術的精神則較為高雅,較為含蓄,較為和諧于自然。”[11]284我們這里并不是排斥、否定西方藝術精神,而是說如果書法中沒有了含蓄、自然,書法的內涵就所剩無幾了。
第四,書法為展覽而創(chuàng)作,為市場而展覽,使得書法創(chuàng)作重形式表現,而乏功力、缺內涵、少自然,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擠壓了公眾對書法本應有的審美期待與審美共鳴。
伴隨著大眾文化的勃興,以高雅藝術形態(tài)呈現出來的書法,已經不再占據文化生活的中心,有了審美泛化的趨勢,表現領域不斷拓寬。“大眾文化是以大眾媒介為手段、按商品規(guī)律運作、旨在使普通市民獲得日常感性愉悅的體驗過程”。[12]8大眾文化本身就具有功利性、世俗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等多方面的特征。使得從書齋里走出來的書法遭遇了史無前例的沖擊。
我們無法否認藝術創(chuàng)作的個人化指向,但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是不會忽視公眾的存在,在藝術家開始創(chuàng)作之際,公眾的藝術趣味以及對即將塑造的藝術形象類型的可能性反應,都成為藝術家表達嘗試的重要參考值。“嚴格地說來,‘個人的藝術’這幾個字,雖則可以想象得出,卻到處不能加以證實。無論什么時代,無論什么民族,藝術都是一種社會的表現,假使我們簡單地拿它當作個人的現象,就立刻會不能了解它原來的性質和意義”。[13]39“藝術不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和虛構的純粹娛樂,它總是保持與現實的緊密聯系,并努力利用自己的影響去改變對現實的知覺”。[14]154
根據接受美學理論,沒有接受主體的參與和響應,任何藝術活動都是潛在的甚至是不完整的。作為接受主體的觀眾是藝術家作品的二度闡釋者,但他們對藝術品的接受不是機械的接受,而是對藝術家體驗的接受與升華。書法藝術從創(chuàng)作到鑒賞這一審美創(chuàng)造過程中,藝術家與公眾應當處于一種良性合作的對話與交流中,這種對話交流既是顯性也是隱性,是雙向互動的循環(huán)流動。這無疑是對優(yōu)秀作品而言的。“藝術接受的最高旨歸是實現人性的復歸和人性的重建”。[15]268
從藝術公眾角度看,面對一件優(yōu)秀藝術作品,一個有審美知覺的公眾是不會無動于衷的,作為鑒賞者獲得精神上的滿足與愉悅即是審美享受。公眾被藝術作品里的思想感情、藝術形象所打動,從而形成審美高峰體驗;與藝術家在情感、趣味、理想達到較高的共振與溝通;審美共鳴使鑒賞者處于一種愉悅、和諧的審美情境中。公眾的情感在共鳴中得到調節(jié)、慰籍、疏導和升華,公眾進入藝術作品所營構的審美境界,異化的心靈得到糾正,扭曲的人格獲得升華,精神上得到解放,這是一種生命智慧的飛躍。公眾在挖掘、追尋藝術的深層意蘊中,達到了徹悟的審美境界。“文學藝術具有一種減輕心理壓迫的功能,所有的藝術歸根到底是一種撫慰,而這種撫慰主要的是來自于作品給予讀者的種種解決辦法,而這種解決辦法必定是和讀者的期待方向相一致的”。[15]299康德說“快樂是生命力被提高的感情,痛苦則是生命力受阻的感情”。[3]138公眾欣賞藝術應該獲得的是快樂而不是痛苦。
中國書法已經歷數代,在受眾中形成了廣泛的審美心理共鳴和審美期待,異類的藝術樣式,即使建立在深厚的內涵基礎上,尚且對此期待與共鳴產生沖擊,何況缺乏內涵的光怪陸離的作品,對受眾審美期待的擠壓與變形便可想而知了。當欣賞個體將自己的規(guī)范、標準、目標、價值取向與此類光怪陸離藝術作品中的“理想榜樣”執(zhí)著地聯系在一起時,并對此類作品長期模擬中,個體自覺不自覺地“修正”自己的感悟、體驗并與作品中的取向相參照,遲早會誘發(fā)藝術心理的片面發(fā)展。這是一種虛假的變形的審美接受。接受者尤其是藝術認知結構不盡完善的接受者,可能會一味地與這種扭曲的審美期待進行認同,而產生“共鳴”由此進一步導致審美期待的變形。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費斯汀格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認知失調”理論。在社會心理學中,有關環(huán)境、個人以及個人行為的,認知、觀念和信念的總和,是一個有結構的認知系統。各認知元素之間存在著相應的特殊聯系,它們之間一旦出現不協調,就會導致“認知失調”,主體會產生不適、不悅、緊張、焦慮和憂郁等不良情緒反應。認知失調和由之而產生的情緒的無序反應主要因為接受主體原先的接受容量、類型與接收對象之間的不匹配或沖突。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的異樣形式并伴隨通過發(fā)達的傳播工具,更使得接受個體無以應對。這種信息對特定的個體往往是過量的、突兀的,這已經超出了藝術接受的意義之外了。接受所構成的心理世界是一個充滿了各種可能性的世界。英國藝術心理學家柏西·布克也說:“美學方面,是一個情感和想象的領域,這個領域包括人類幸福的總和——有增進幸福的,也有減少幸福的”。[16]135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更多的是“減少幸福的”。書法被當作只有少數藝術家才能“理解”的“抽象表現”和孤芳自賞,則書法的真義也就蕩然無存。就像托爾斯泰所說,“當藝術不再是全體人民的藝術并且變成富人的少數階級的藝術的時候,它便不再是一項必需的、重要的事業(yè),而變成空洞的娛樂”。[9]40
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的市場意識、功利思想使得書法作品技術觀念強于藝術觀念,對形式敏感,對意境遲鈍。這既是由于創(chuàng)作者文化修養(yǎng)、哲學與美學修養(yǎng)欠缺,也是書法功底積累不足所致。書法家在面對書展而準備的作品,不可能以一種志氣平和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對之,功利心理上升到主導地位,由素質型創(chuàng)作向應試型創(chuàng)作心理轉換。“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雕疏”。[4]126乖合之間,天壤之別。如果書法創(chuàng)作的目標市場化、動機功利化,這樣的作品缺乏高雅純正的文化精神內涵的支撐,很難成為歌德所認為的培養(yǎng)“出我們所說的鑒賞力”的最好的作品。“這樣才能培養(yǎng)出我們所說的鑒賞力。鑒賞力不是靠觀賞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觀賞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所以我只讓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礎,你就有了用來衡量其他作品的標準,估價不致于過高,而是恰如其分”。[5]32
四
書法產業(yè)包括在文化產業(yè)范圍之內。文化產業(yè)化使得文化被更多地賦予了市場性。文化對社會是有教育教化作用的,過分強調了文化的經濟價值,就必然掩蓋了文化的教化作用,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就會忽視文化的精神內涵。書法藝術的文化價值就在于它是民族傳統文化最凝練的物化形態(tài),它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得以傳承和發(fā)揚的一種重要方式與途徑。只有承載時代文化精神和傳承傳統文化精神的書法才能在指向更廣范圍中彰顯價值力量。
需要承認書法產業(yè)化使得書法生存與表現形態(tài)有了新的信息傳遞方式,形成了書法的利益機制,促進了書法的流通,使書法的發(fā)展從此轉入多元化和向民主化發(fā)展的軌道。“孤立的、與生活不再發(fā)生關系的藝術作品,不管它如何迷人,總要成為一件無用的玩具,注定會失去它的人文價值”。[2]17藝術品創(chuàng)作一方面必須嚴格與現實世界相分離,在一種內在的操作之中孕育完美;但另一方面,藝術又在將對象材料轉化為一種內在的符號系統的同時,強調有效地把握現實事物的整體性特征。在找尋適合于新時代的新工具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位置,在并不放棄歷史的審美裁判與藝術的審美話語表達的同時,適應并接受文化市場規(guī)律的選擇。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藝術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現和揭示人的心靈”。[9]11書法創(chuàng)作應該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人格魅力的自然展示、人文精神的自然體現。這才應是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追求的終極目的。因此我們說書法產業(yè)化的目的不是“去書法化”,而書法創(chuàng)作的最終目的也不能在產業(yè)化中消解。
[1]丁亞平.藝術文化學[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
[2]朱狄.當代西方藝術哲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3][德]康德.實用人類學[M].鄧曉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上海書畫出版社.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5][德]愛克曼.歌德談話錄[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9][德]席勒.席勒文集(理論卷)[M].張佳玨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7][德]康德.論優(yōu)美感與崇高感[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8]伍蠡甫.西方古今文論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
[9][俄]列夫·托爾斯泰.論創(chuàng)作[M].戴啟篁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
[10]劉勰.文心雕龍[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1]林語堂.吾國與吾民[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
[12]王一川.大眾文化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3][德]格羅塞.藝術的起源[M].蔡慕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14][法]馬克·第亞尼.非物質社會[M].滕守堯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15]童慶炳.文藝心理學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6][英]柏西·布克.音樂家心理學[M].金士銘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2.
[17][匈牙利]阿諾德·豪澤爾.藝術社會學[M].居延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