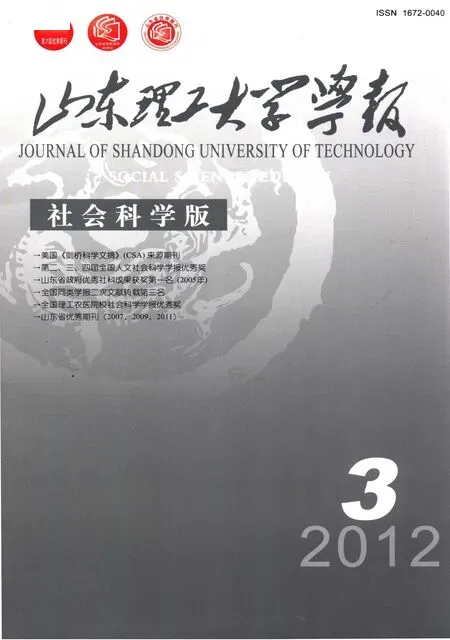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談?dòng)彤嬶L(fēng)景寫生教學(xué)
李雪松
(山東理工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山東淄博255049)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談?dòng)彤嬶L(fēng)景寫生教學(xué)
李雪松
(山東理工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山東淄博255049)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形象地反映了繪畫中寫生與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將這一中國(guó)古典畫論引入油畫風(fēng)景寫生教學(xué),既可以避免在教學(xué)中對(duì)西方繪畫語(yǔ)言樣式的生搬硬套,又可以克服在借鑒西方繪畫形式的過(guò)程中出現(xiàn)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進(jìn)而努力使教學(xué)方式更趨民族化和多元化。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風(fēng)景寫生;客體;主體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山水畫家張璪在其畫論《繪境》中提出的關(guān)于畫學(xué)的不朽名言,具有普遍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原理的意義,堪稱中國(guó)藝術(shù)理論的精髓。老子說(shu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79“道法自然”是生活在自然界中人的必然選擇,也是最終選擇。科學(xué)的發(fā)展就是人類不斷研究自然、探索自然、尋求自然內(nèi)在規(guī)律的最好印證。“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就是要了解自然,以自然為師,將自然孕育的天地之美與自己內(nèi)在的心靈感悟合而為一,以此作為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行動(dòng)指南。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八個(gè)字極為凝練地概括了繪畫創(chuàng)作中從客觀現(xiàn)象到藝術(shù)意象再到藝術(shù)形象的演變過(guò)程。“揚(yáng)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在論畫竹時(shí)也曾提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個(gè)階段,形象地闡述了繪畫中客體與本體的轉(zhuǎn)化、融合過(guò)程。這一過(guò)程不僅適用于中國(guó)畫的寫生與創(chuàng)作,對(duì)于油畫風(fēng)景寫生的訓(xùn)練和探索也具有普遍的指導(dǎo)意義。
早在古羅馬時(shí)期,著名的博物學(xué)家、作家老普林尼就在其筆記式著作《博物志》中指出:“自然是被模仿的,不是被抄襲的。”這里對(duì)自然的模仿不僅僅是指形象上簡(jiǎn)單再現(xiàn)描摹,而且要從本質(zhì)上去把握自然的造型規(guī)律,客觀的形象被賦予了創(chuàng)造的意義。縱覽西方繪畫中的風(fēng)景畫作品,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歷代畫家的創(chuàng)作大體上遵循了“客觀現(xiàn)象—藝術(shù)意象—藝術(shù)形象”這一繪畫創(chuàng)作過(guò)程。只不過(guò)是不同時(shí)期不同畫家的側(cè)重點(diǎn)有所不同罷了。
油畫藝術(shù)作為西方的舶來(lái)品傳入中國(guó)已有數(shù)百年之久,但作為一門獨(dú)立的專業(yè)學(xué)科,油畫教學(xué)的歷史卻非常短暫且很不系統(tǒng)。在具體的教學(xué)實(shí)踐中,很多教學(xué)理念和方式往往受制于個(gè)人喜好或局部環(huán)境的影響,多以“個(gè)體”或“風(fēng)潮”的特征存在,例如徐悲鴻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和林風(fēng)眠的現(xiàn)代繪畫風(fēng)格。而個(gè)體之間或風(fēng)格流派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由此造成了藝術(shù)理念上的差異甚至“敵對(duì)”情緒,這非常不利于學(xué)生對(duì)于知識(shí)的全面掌握與吸收,嚴(yán)重時(shí)甚至?xí)斐伞袄L畫黑幫”的產(chǎn)生。傳統(tǒng)的油畫教學(xué)就是在這種土壤中進(jìn)行的。教學(xué)理念的狹隘或缺失,教學(xué)內(nèi)容的偏執(zhí)與單一,會(huì)把學(xué)生培養(yǎng)為缺乏全面營(yíng)養(yǎng)的“豆芽菜”。因此,探索更加合理的教學(xué)模式,尋求更多的教學(xué)可能性,就成了所有藝術(shù)教育者面臨的一個(gè)公共的課題。經(jīng)過(guò)百年的發(fā)展,油畫教學(xué)不僅需要繼續(xù)吸收和借鑒西方油畫的精華,而且還應(yīng)該從本民族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中吸取營(yíng)養(yǎng)。“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就是以中國(guó)化的思維方式為油畫風(fēng)景寫生教學(xué)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轉(zhuǎn)變思維、更新理念、勇于創(chuàng)新、敢于嘗試,探求更加合理和多樣的教學(xué)模式,是形成積極、互動(dòng)的教學(xué)氛圍的必然選擇。因此,油畫風(fēng)景寫生教學(xué)有必要進(jìn)行改革和調(diào)整,以適應(yīng)當(dāng)前油畫發(fā)展的需要。
筆者認(rèn)為,油畫風(fēng)景寫生是實(shí)現(xiàn)繪畫思維多樣化的一塊良好的藝術(shù)教學(xué)試驗(yàn)田。因?yàn)轱L(fēng)景寫生的過(guò)程具有培養(yǎng)學(xué)生觀察和組織自然景物的能力、錘煉繪畫語(yǔ)言的能力、挖掘創(chuàng)造意味及想象能力的功能。這三種能力的培養(yǎng)分屬三個(gè)不同的階段,各個(gè)階段呈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遞進(jìn)關(guān)系,符合繪畫創(chuàng)作中“客觀現(xiàn)象—藝術(shù)意象—藝術(shù)形象”的演化過(guò)程。
一、直面自然,觀察自然
羅丹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生活中不缺乏美,而是缺少發(fā)現(xiàn)美的眼睛”。自然界豐富多變,不同的氣候、迥異的地貌,會(huì)帶給觀者不同的心理感受和審美體驗(yàn)。正所謂“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我們很難判斷是阿爾燦爛的陽(yáng)光造就了梵高,還是梵高驅(qū)散了阿爾的陰霾,但無(wú)可爭(zhēng)議的是梵高在阿爾的黃色陽(yáng)光中燃燒了自己最后的能量,為繪畫史留下了極富傳奇色彩而又輝煌的一筆重彩。大自然是一個(gè)巨大的信息庫(kù),繪畫者在面對(duì)它時(shí)總能夠找到打動(dòng)自己心靈的瞬間。自然界沒(méi)有風(fēng)格,沒(méi)有樣式,更沒(méi)有“門戶之見(jiàn)”,面對(duì)自然景物的寫生,是畫者觀察自然、了解自然、挖掘自然之美的必要手段和最佳途徑。在具體的教學(xué)中,由于學(xué)生初次涉獵風(fēng)景,心中沒(méi)有成見(jiàn),思維無(wú)定勢(shì),通過(guò)培養(yǎng)學(xué)生對(duì)于自然的觀察,克服室內(nèi)教學(xué)中易出現(xiàn)的概念化的觀察和僵化的思維模式,使學(xué)生具有在生活中發(fā)現(xiàn)美的能力。這一階段的教學(xué)重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對(duì)自然進(jìn)行深入細(xì)致的觀察和表現(xiàn)技法的訓(xùn)練。在構(gòu)圖上要學(xué)會(huì)對(duì)自然景物進(jìn)行“移景換形”式的裁剪和重組,對(duì)畫面的組織可以鍛煉學(xué)生的審美判斷能力。自然界中的美不是一個(gè)固定的、約定俗成的模式,不同的景物甚至相同景物在不同地域、不同國(guó)家、不同民族的人眼中往往是不同的,美的感受能力受到觀者的文化背景、知識(shí)儲(chǔ)備、個(gè)人喜好等主觀因素的制約。在表現(xiàn)上要通過(guò)對(duì)自然的模仿達(dá)到視覺(jué)上的真實(shí),這種真實(shí)更多的是“圖像”的真實(shí),以還原和再現(xiàn)自然景物為目的。要做到“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shí),取其實(shí)”,而“不可執(zhí)華為實(shí)”。[2]338此階段通常要求“以景帶人”,要求學(xué)生能對(duì)自然景物在“形似”的意義上進(jìn)行真實(shí)描繪,為下一步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打下基礎(chǔ)。
二、師法自然,尋找語(yǔ)言
“外師造化”不能只對(duì)景物表面的“形似”進(jìn)行觀察和塑造,而應(yīng)該在理解的基礎(chǔ)上抓住本質(zhì)特征去表現(xiàn)“心理的真實(shí)”,客觀物象“形似”只是審美的載體,要努力追求物象內(nèi)在的規(guī)律,這就要求觀察應(yīng)“明物象之源”。吳冠中先生每到一處寫生,并不會(huì)急于寫生,而是拿著速寫本到處走走看看,首先從整體上把握寫生地點(diǎn)的整體氣韻,提煉出對(duì)此地域抽象的印象,或秀雅,或質(zhì)樸,或蒼茫渾厚,藏造化于胸中,這樣在具體的寫生中才能把握畫面的整體感受,做到“形神兼?zhèn)洹焙汀扒榫敖蝗凇薄T诒憩F(xiàn)景物的過(guò)程中要拋開(kāi)自己固有的表現(xiàn)習(xí)慣和前人的語(yǔ)言的“規(guī)窠”,努力尋找、提煉與自然景物相符合、相對(duì)應(yīng)的表現(xiàn)語(yǔ)言,要做到“形質(zhì)皆異”。[3]61被譽(yù)為“森林的歌手”的俄羅斯風(fēng)景畫家希施金終其一生都在觀察、研究俄羅斯廣袤無(wú)垠的森林,他對(duì)植物細(xì)致入微的觀察連植物學(xué)家都自嘆弗如。也正因?yàn)槿绱耍P下的風(fēng)景畫才能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這片森林的靈魂。在他的代表作之一《松林的清晨》中,觀眾能從畫中感覺(jué)到松林中彌漫的雨露和浮動(dòng)的花香,甚至鳥(niǎo)兒清脆的歌聲和小熊幼稚而低沉的叫聲,這就是寫生的魅力和價(jià)值所在。無(wú)獨(dú)有偶,我國(guó)唐末畫家荊浩也有畫松“凡數(shù)萬(wàn)本,方如其真”的感嘆。可見(jiàn),寫生的過(guò)程不但要通過(guò)景物的“生”給人帶來(lái)刺激和新鮮感,還要提煉繪畫語(yǔ)言上的“生”,克服慣性思維模式和表現(xiàn)的概念程式,使繪畫保持新鮮的藝術(shù)生命力。
三、“心”“物”交融,“道”“技”合一
“心”“物”交融,“道”“技”合一是風(fēng)景寫生的最高境界。作為“客體”的自然萬(wàn)物與作為“主體”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者“情景交融”,“客體”不再是簡(jiǎn)單的客觀物象,而是一種來(lái)自現(xiàn)實(shí)生活又高于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在“主體”充分理解和把握客觀物象之后“內(nèi)化”了的藝術(shù)形象,它既有現(xiàn)實(shí)的烙印,又有創(chuàng)作者的想象和主觀感受,如同受孕的胚胎,孕育著一個(gè)嶄新的生命,“客體”和“主體”的基因深深地根植于這個(gè)新的藝術(shù)形象之中。在此階段,繪畫語(yǔ)言和繪畫技術(shù)的高度成熟,在“心”和“物”之間搭建了無(wú)阻礙的表現(xiàn)渠道,通過(guò)對(duì)自然的深入觀察和體驗(yàn)而得到的“道”不能離開(kāi)了“技”這個(gè)中介,否則無(wú)疑是抽掉了創(chuàng)作者溝通“客體”與“主體”之間的橋梁。“物我無(wú)間,道技為一,技進(jìn)乎道,道存于技”,“道”與“技”的完美融合使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guò)程真正成為了一種妙合無(wú)間的自由人生體驗(yàn)過(guò)程。縱覽西方歷代大師的經(jīng)典繪畫作品,我們發(fā)現(xiàn)它們無(wú)一不是“心”與“物”的交融之作,“道”與“技”的統(tǒng)一之作。例如塞尚為了追求畫面結(jié)構(gòu)的堅(jiān)實(shí)和穩(wěn)定,在觀察時(shí)果斷舍棄客觀物象的瑣碎的細(xì)節(jié)而執(zhí)著于自己“心中的形象”——大塊“形”與“形”之間的沖撞與咬合、對(duì)比與均衡。為了實(shí)現(xiàn)畫面的建筑物般的堅(jiān)實(shí),塞尚還發(fā)明了適合自己審美追求的、像磚頭一樣的楔形筆觸。達(dá)芬奇為繪制神秘微笑的《蒙娜麗莎》所使用的“漸隱法”,盧西恩·弗洛伊德為追求畫面的“物質(zhì)感”而堆砌的粗厚筆觸,都是為了實(shí)現(xiàn)“物象”與“心象”相統(tǒng)一的必然的技法選擇。
綜上所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一反映了寫生與創(chuàng)作關(guān)系的畫論,不僅體現(xiàn)了客觀物象與主體感受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轉(zhuǎn)化的過(guò)程,也符合教學(xué)應(yīng)由易到難、層層遞進(jìn)的一般規(guī)律。這一教學(xué)規(guī)律體現(xiàn)為:從觀察上,由對(duì)客觀形象的觀察逐漸“內(nèi)化”為符合自身審美的心理物象;從表現(xiàn)上,由對(duì)客觀景象的被動(dòng)描繪到對(duì)物象熟知后的主觀表現(xiàn);從作品面貌上,體現(xiàn)出形式語(yǔ)言和畫面內(nèi)容的高度融合。這種教學(xué)方法從本質(zhì)上把握了油畫風(fēng)景寫生應(yīng)遵循的規(guī)律,點(diǎn)明了寫生與創(chuàng)作的遞進(jìn)和轉(zhuǎn)化關(guān)系,從而有效地避免了在寫生教學(xué)中對(duì)于風(fēng)格或樣式的生搬硬套,使教學(xué)方式更趨民族化和多元化。
[1] 李耳.老子[M].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2002.
[2] 樊波.中國(guó)書畫美學(xué)史綱[M].長(zhǎng)春:吉林美術(shù)出版社,1998.
[3] 馬鴻增,馬曉剛.中國(guó)名畫家全集:荊浩·關(guān)仝[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J21
A
1672-0040(2012)03-0101-03
2012-03-26
李雪松(1978—),男,山東淄博人,山東理工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講師、文學(xué)碩士,主要從事油畫創(chuàng)作和研究。
(責(zé)任編輯 李逢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