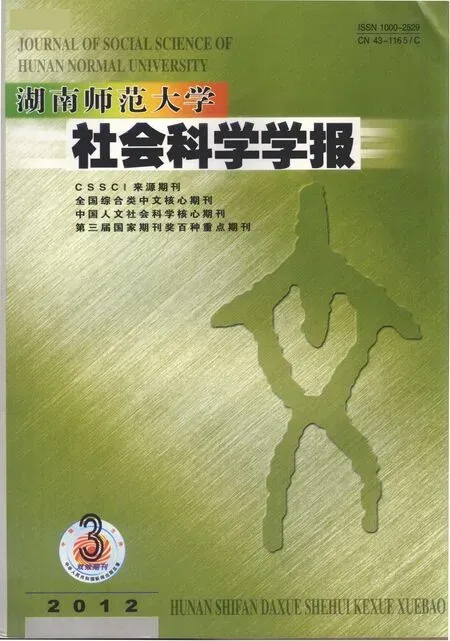“碳政治”與中國社會轉型
白春雨
“碳政治”與中國社會轉型
白春雨
“碳政治”的內涵包括遠景、中景、近景三個層次。遠景碳政治以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為基礎,表達人類對世界的終極關懷;中景碳政治是氣候協議意義上的“碳政治”;近景碳政治是發達國家在氣候分配方面的直接利益訴求。中國在積極尋找破解能源資本原則下的發展困境,“給能源注入文明”成為中國碳政治戰略的可能選擇,并從這里開始了中國社會新的轉型,為深入理解馬克思共產主義提供了實踐方向。
碳政治;現代性;生態文明;給能源注入文明
“碳”本是自然中的物質元素,構成了細胞和遺傳密碼,是生命循環系統必不可少的因素,循環系統的末端以碳廢物的形式排出。在科學理性和構建世界新秩序的主題下,“碳元素”一躍而成為“碳政治”,成為生態文明衡量的綠色指標,以氣候、綠色、安全、平等、自由、民主等為其話語系統,成為世界各國政治聚合、權力博弈的角逐場。為應對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風險,中國政府積極參與到“碳政治”的對話當中,并把它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素。
一、“碳政治”的內涵
“碳政治”這一概念應該是中國學者應對西方治理氣候變化,針對環境變化和權勢轉移的國際政治戰略而構建的具有生態文明高度的概念,是對西方氣候變化政治學的認識和反思。基于西方氣候變化政治學的三個層面的探討,我將“碳政治”的視角也劃分為:遠景“碳政治”、中景“碳政治”和近景“碳政治”。
1.遠景“碳政治”——生態文明與生態社會主義的主張
遠景“碳政治”不同于傳統能源政治,是新型國際政治,這種新型政治之所以“新”的蘊意在于其以生存和生態系統的和諧為基礎,在人與自然和諧的語境中表達人類對世界的終極關懷。“碳政治”的提出是對傳統能源政治所創造的個人主義哲學神話的顛覆,它要求在人與自然和諧的狀態中求取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這樣的理想訴求恰是與西方的民主制和自由主義所依賴的能源經濟的高速增長相背離的。傳統的能源政治以“利益”為主導,是構建在知識論體系下的科學技術的應用,它強調人類對資源的占有以及在人與自然相對抗的范式中表達人類積累財富的物質欲求,強調能源經濟帶來的高效社會,不僅滿足每個人的物質需要,而且形成國家經濟增長對能源的依賴。這種從能源經濟上控制世界的消費主義價值觀排斥了對世界未來的真實關懷,過分強調個人的行為自由、權利自由而忽視生存和生態系統的和諧。
遠景“碳政治”的高遠立意在于通過氣候變化實現社會關系的轉型,它力求突破現代性視域下“碳政治”發展的歷史局限,現代性是制約“碳政治”發展的意識形態,具體表現為:(1)“經濟人”模型的意識形態化。以個人本位為基礎的自由主義通過“經濟人”模型把對個人的行為自由、權利自由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表面上看來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其實在社會強制進步原則下加速了社會的不平等,通過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的方式肢解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生存的內在關聯。(2)技術的意識形態化。當我們以科學技術為媒介促進工業增長提高人民的生活福祉時,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引發的氣候變暖拷問科學技術給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關系帶來的緊張狀態。現代科學技術的負面因素正在被歷史的思維審問:現代科學技術已經成為一種人類難以駕馭的力量并且在主宰人類生活,人墮落為技術的玩偶。(3)消費意識形態化。在消費社會及其表面富裕的背后,增長著人際關系的空虛、滋長著物化社會生產力流通的空洞輪廓。以上三種現代性意識形態反映了工業文明危機,把經濟的增長建立在犧牲環境的籌劃上,必然要引起社會的轉型。
純粹環境問題不會引起人們的關注,也不會引起人們對環境問題的積極思考,因為任何與人類不相關的存在相對于人類是“無”。在現實生活中,“面對純粹環境氣候出現的人類安排,而這種人類安排又會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甚至社會意識。國際氣候談判進程和全球集體行動難題充分說明氣候問題的經濟性、政治性和社會性是造成氣候問題全球性和管理無序性矛盾的主因。”[1](1)今天針對氣候變化問題行動的不是為了更加有效解決環境本身的問題,而更多的是將注意力聚焦于環境外的利益分配,即氣候就是利益。“我們真正需要作出的回應是適當計算和承認全球變暖和現代帝國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系”[2](61)這是“碳政治”發展的歷史局限,由此我們了解目前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主要代表發達國家的利益訴求和意識形態,而環境本身的需求被擱淺。
生態社會主義的“碳政治”要求批判建立在追求利潤和資本積累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大量的能源消費和有害廢棄物的排放。資本文明的增長與氣候環境變化的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一方面說明被資本主義奉為圣杯的“利潤和生產之神”的衰落;另一方面說明在人與自然和諧的狀態中求取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這就引出了生態社會主義的主張,著名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家喬爾·科威爾說:“資本不只是一種經濟剝削的工具,而且是死亡天使。為了挽救人類,為了延續生命,我們必須明白‘根本的問題不是技術性的,而在于我們改造自然和消費我們勞動成果的方式。要合理地做到這一點,必須堅持生態社會主義的時代精神。’”[3](20)這就是說,生態文明與生態社會主義要成為破解工業文明出路的時代精神,使之作為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參與到民主的建構和社會轉型當中。
2.中景“碳政治”——氣候協議意義上的“碳政治”
氣候協議作為氣候分配正義的綱領性文件,它既是氣候變化政策制定的基礎,也是開展國際合作的有效條件。1992年6月4日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153個國家和歐共體簽署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這一公約是國際社會在對付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展開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框架。1997年將公約進一步變成可操作的法律文件《京都議定書》,并于2007年通過“巴厘島路線圖”。在這些法律文件中,環境問題轉化為氣候問題并在技術上轉化為二氧化碳的排放,從而在法律上產生圍繞“碳排放權”展開的全球政治博弈,形成全新的“碳政治”。為了與建立在自然—生態和諧基礎上遠景“碳政治”相區別,我把氣候協議意義上的“碳政治”界定為“中景碳政治”。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國際社會在對付氣候變化問題上展開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框架。該公約明確規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負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是一條絕對道德命令,體現了尊重歷史和現實,要求廣大國家公平承擔氣候變化責任的宗旨。美國學者埃里克·波斯納和戴維·韋斯巴赫對“富國承擔更多的減排義務”提出非議,認為:“富國是否有特殊的義務來應對氣候變化。”[4](89)這是有意排斥歷史,將發達國家遵守氣候協議的責任的強制履行弱化為根據財富多寡履行國際責任的原則,進而發難:讓富國承擔大部分減排成本,而讓較窮的國家繼續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這是不是公平?這種推諉歷史責任并把氣候責任與財富分配問題試圖做“天然”結合的想法,恰恰表達了美國等發達國家把氣候協議與貧富差距混同在一起,其目的是以貧富問題的復雜性和敏感性掩蓋氣候協議所規定的大國義務。
溫室氣體排放“外部性”特征決定了氣候協議意義上的“碳政治”提出的必要。在國際無政府主義和國家“經濟人”的假設下,現代性的困境表現為它缺乏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治理和國家有限性行為的約束,因此無法解決全球變暖給世界帶來的巨大災難。氣候協議基礎上的“碳政治”是現代國家的交往原則,它是服從主流經濟學原則下的運行。今天應對氣候變化的人類安排雖說有自然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重話語的關注,但是它還主要滿足國際帕累托主義原則,以合作共贏作為抵御全球變暖的策略。國際帕累托主義是一種利益性的制約因素,從現實的國家實際利益和有限道德觀出發,認為氣候變化的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合作的方式增加其國民的福祉,進而增加全人類的福利,并以社會財富的最大增進作為“碳政治”運行的最佳有效機制。
3.近景“碳政治”——發達國家在氣候分配正義上的直接利益訴求
近景“碳政治”是指以歐美發達國家在資本原則下,通過對減排工程的技術干預,運用廣泛理解的政策和技術擬定一個安全地球的愿景規劃假說來達到全球資本的重組,實現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新經濟壟斷。其政治哲學基礎是現代性視域下的自由民主,它一方面大肆宣揚氣候變化的嚴峻性超越恐怖主義對世界的威脅,另一方面在氣候就是利益的“真理”面前攫取碳交易帶來的豐厚利潤。近景“碳政治”大肆吹捧針對環境變化的技術創新,“將這個問題描繪成在綠色技術上打算勇奪第一的國家與可以拯救世界的市場之間的一場賽跑。”[3](432)這種以技術贏取市場的效率和經濟增長的原則迎合了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的口實,但卻將“地球生態系統的一系列迅速擴散的裂變”置于腦后,強化了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性。
1997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日本京都會議通過了《京都議定書》,議定書建立了旨在減排溫室氣體的三個合作機制——國際排放貿易機制、聯合履行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所謂“清潔發展機制”(CDM)是指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每減少一噸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國內就可相應多排放一噸二氧化碳,即多獲得一噸二氧化碳排放權。在這樣一個積極的機制上,歐美等發達國家理應利用成熟的清潔能源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氣候治理,為自己贏取更多的碳排放權。然而在巴厘島會議上,針對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減排技術問題上,歐盟表示愿意積極推進與發展中國家的低碳經濟合作,而美國一方面不支持以低價轉讓減排技術的“知識產權”,其真實目的是向發展中國家出售設備獲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他們還吸引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參與他們的碳金融市場,以低廉價格購買發展中國家的“核證減排量”,通過他們的金融機構包裝,開發成為價格更高的金融產品,賺取“剪刀差”利潤。因此說,環境資源和現代文明機制——知識、權力、資本等要素結合在一起,演繹的是一場利益角逐。
二、“碳政治”視域下中國能源文化的內涵與能源發展的困境
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轉型的時期,我把轉型的內涵界定為在“碳政治”的背景下,中國社會面臨著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產業轉型,而與產業轉型并進的能源轉型既是產業轉型的核心,更是“碳政治”的關注點。隨著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能源經濟和能源戰略的發展事關中國工業化的未來,因此積極探討有中國特色的能源文化,“給能源注入文明”是中國能源文化的內涵。
1.“給能源注入文明”是中國能源文化的內涵
中國能源文化內涵即“給能源注入文明”是不同于西方“給文明注入能源”的能源文化。西方“給文明注入能源”意識形態的確立,加速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旋轉的車輪,以驚人的能源消耗和經濟實力浸淫著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文明的價值形態,成為資本主義外部積極擴張的文化機制和發展模型,加速了制度機芯“本我沖動”的萌發,造成了歷史上不堪目睹的兩次世界大戰爆發并成為以后戰爭發動的內在能源文化機制。因此,把能源安全納入到國家戰略高度來統籌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導致了自然和人類本身的災難,把人類推向風險社會——極權的增長、經濟增長機制的崩潰、生態破壞和災難以及核沖突和大規模戰爭,反映了工業文明危機和資本主義文化危機。
“給能源注入文明”是筆者針對“給文明注入能源”的一個思考,以說明中國工業化進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的本質區別。首先,中國在工業化中探尋的是“自力更生”能源道路,“大慶精神”、“勝利精神”能源文化的形成確定了中國的能源文化內涵,就是“不稱霸”和“合理”地開發資源。中國社會工業化發展的模式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走與自然和社會合作共贏的發展道路,而非以能源擴張來改變政治格局。伴隨中國工業化進程而影響中國人民的是艱苦奮斗的精神、“鐵人精神”和今天被人們傳揚的中非友好往來的佳話,而非血雨腥風的經濟封鎖和政治高壓。其次,“給能源注入文明”的價值形態與中國國家戰略目標相符合。改善民生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一直是中國工業化推進的目標和方向。民生問題是中國發展目標的最大關注,因此中國有勇氣接受氣候變化的挑戰,在經濟轉軌和全球相互依賴的信任體制中建立、完善并傳播中國的能源文化。再次,與中國文化戰略目標相符合。面對西強我弱的文化格局,為能源文化注入以傳統文化為核心的愛國主義,并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規范能源文化,讓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中迸發出民族的生命力。最后與遠景“碳政治”的價值目標相符合,必然成為生態文明與生態社會主義的積極主張。“生態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是為了生命,致力于生命的延續和繁榮。這是生態社會主義的核心意義”[3](441)。致力于生命的延續和繁榮是人性之善的本真表征,也是中國能源文化的意義所在。
2.中國社會能源轉型的困境
現代性這個曾經拯救西方文明的諾亞方舟是否能承載中國文明并將中國文明向前推進一步?一些鼓吹“全盤西化”的國人把諾亞方舟看作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與令箭,然而它所暴露出來的卻是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的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這種發展—剝奪的困境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在對話中的強勢,諾亞方舟代表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模式,中國在能源發展道路上處于被劫持狀態;另一方面說明未來中國社會轉型的復雜性,國內改善民生的需求與沖擊全球“經濟人”意識形態價值觀、消費主義價值觀和技術意識形態化交織在一起,使中國社會的轉型又充滿世界性。中國社會已經被擠進現代性的高速列車,這就警示我們一方面必須服從現代性的規則,沒有脫離現代性高壓的純粹中國現象;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突破現代性的困境,堅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發展方向。因為現代性本身是一個病態的意識形態,是資本主義的文化宿命,已經影響現代世界文化安全與文明模式的轉換。因此中國社會轉型必須對現代性意識形態進行縝密思考。
美國及歐盟等發達國家“碳政治”的對話主要聚焦在中景“碳政治”和近景“碳政治”視域內,這是以利益和資本增殖為目的的國際能源交往,服從西方主流經濟學原則,“生態價值可以在市場中找到它們的自然空間,就像其他所有的消費者需求一樣。”[3](416)但是我們知道把環境納入到市場是對傳統經濟學的挑戰,因為傳統經濟學從市場機制完全排除了對資源逐步減少的必要性的關心、排除溫室氣體排放的外部性特征、排除了代際間環境分配等問題。新制度經濟學的貼現方法和邊際效用理論被氣候變化政治學者作為有關氣候變暖的經濟政策選擇,美國著名氣候變化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用DICE模型(即氣候與經濟動態綜合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ic),給未來的政策和道德判斷提供了啟示。它試圖超越古典經濟學投入—產出理論模型,將氣候的風險聚焦于財富、收入和消費來補償后代人的生存命運的貼現計算方法,運用“邊際效用原理”解釋未來環境商品服務的稀缺性,其目的是喚起人們的環境覺悟,但卻事與愿違:一方面人們意識到環境的稀缺性,還加大了對環境權利的消費;另一方面由社會貼現程度的降低只能說明當代人的道德水準的降低和社會道德的滑坡。DICE模型從“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出發沒有走出古典經濟學的投入—產出和帕累托最佳效益原則,它是傳統經濟學體制下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哀嘆。
中國能源轉型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對可見的“能源陷阱”的不可回避。能源意識形態即為能源陷阱,能源意識形態服從主流經濟學意識——資本原則,資本對增長的欲求和追求高利潤的心理不會因為工業、后工業、石油時代和后石油時代而發生改變,超額利潤才是目的。反之,中國能源轉型還只是為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和國內經濟增長發展的需求,是在“合作共贏”的生態文明的理念下解決中國石油市場的需求。中國沒有在國際石油市場中的定價權,“由此導致了一方面我國石油企業無法像跨國石油巨頭那樣在期貨市場大把‘吸金’,另一方面我國國內只能靠行政定價來面對國際油價的漲價”[5](135)。因此在能源資本吞噬能源資源的時代,中國能源轉型還處于對能源資源的索取,而不是對能源資本的攫取,因此在中國能源轉型的道路上很難走出“能源陷阱”。中國能源轉型就是盡快擺脫“能源陷阱”沖擊,適時搭上國際“碳政治”發展的快車,積極參與國際碳市場的構建,為中國能源經濟發展尋求“碳政治”規則的突破口。
三、“碳政治”與中國社會轉型
“碳政治”下的中國社會能源轉型以及伴隨能源轉型的生活理念的轉型是我們著力探討的內容,由能源轉型的內容延伸出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二次提出的社會轉型意義與第一次社會轉型意義的區別。在區別中透視出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與世界的交融程度不僅體現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逐步接近,還體現在市場化與技術化造成的趨同,更強烈的表現是現代性意識的認同。而現代性意識恰是現代社會危機的根本所在,所以說中國第二次社會轉型所肩負的責任既是中國人民自身的,更具有世界性意義。
1.中國社會轉型的必要性
中國社會轉型問題不斷地被提到思想者的筆端,這一次與上個世紀90年代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面臨的價值轉換不同,上一次人們主要將視野集中在經濟與倫理關系問題上,肯定追求物質利益活動的價值意義和個人經濟利益的合理性。經歷改革開放30多年,市場經濟的大力推進,伴隨著其積極進步的意義,消極意義也呈現于人們的眼前:社會進步與道德滑坡,經濟增長與資源短缺、消費主義與個人權利的膨脹以及技術意識形態化等社會問題一股腦兒地反映出來。
從問題的呈現我們看出這一次轉型要解決的問題一定是工業文明促成的社會危機,因此從解決方案上:其一是以生態文明為主軸,扼制住西方大力宣揚的個人主義及以個人權利為圣杯的民主自由。現代性發展維度褫奪了功利主義核心概念——個人幸福,用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填滿幸福的漩渦,把權利自我奉為圣杯。當人們沉浸于物質主義享樂狀態時,發現自己已經退化為欲望的奴隸。這也恰是西方自由主義文化危機所在,正是在這樣一層意義上,我們應該正視中國也已經面臨現代性意識的包圍,因此中國社會轉型的有效思考必然是對世界文化危機治理的有效回應。其二是隨著中國工業化的深入,已經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能源消耗國家,而且未來經濟的發展對能源的依賴還將繼續。“碳政治”對話層面的加入,讓我們考慮經濟增長與低碳減排在中國同等重要,經濟增長是保持社會穩定和解決溫飽的基礎,低碳減排是“碳政治”限制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面臨雙重壓力,“碳政治”的壓力更大。因此,中國參與構建世界碳市場的意義重大,它可以說是中國社會轉型亟需解決的問題。
2.遠景碳政治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現實思考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中的生態文明向度為中國社會轉型提供了有意義的價值思考。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針對國民經濟學批判而構想的共產主義愿景是建立在人與自然和諧基礎上的人類存在。共產主義是對國民經濟學的積極揚棄,國民經濟學是工業化的意識形態。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工業主義是國民經濟學意識形態在現代的集中反映。隨著中國社會轉型深入推進,今天中國已經不是經典里“無歷史的存在”的嘲笑,而是被納入到歷史的記錄之中,中國贏取了世界性的話語權,這一切恰被我們認為是中國社會轉型歷史進步的體現。但與社會進步相伴而生的道德滑坡的眩暈又遮蔽了中國歷史進步的光環,因此“社會進步與道德滑坡”是中國第二次社會轉型必須給予解釋和說明的重要命題。通過道德滑坡反映出現代性是一種虛假意識,因此它所表現的社會進步不是人類的整體進步,而只是現代性意識下描述。國民經濟學的方式就是資本的方式,它把自然界、自然科學、人以及人的存在方式勞動全部轉化為資本的要素,而這一生存模式就是就是非人性和物化,因此:“說生活還有別的什么基礎,科學還有別的什么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6](193)人的一切活動,科學的一切朝向只有資本、利潤和無限的社會增長。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出“社會進步與道德滑坡”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它是現代性視域下“碳政治”發展的歷史局限。它是資本無限增長的欲求所導致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分離。而現代性自身發展所導致“社會進步與道德滑坡”在國民經濟學體系中不會得到解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對國民經濟學的揚棄,“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則。”[6](197)共產主義原則與遠景“碳政治”這一實踐的歷史維度的結合必然會打破增長的價值的理念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訴求,在自然與社會和諧的基礎上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1]于宏源.環境變化和權勢轉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英]邁克爾·S.諾斯科特.氣候倫理(左高山譯)[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3]曹榮湘.全球大變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4][美]戴維·韋斯巴赫.氣候變化的正義(李 智譯)[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5]王國棟.低碳經濟[M].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0.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Carbon Politics and China Society Transformation
BAI Chun-yu
In this paper,the Carbon Political includes three levels that was the future,Med-shot and Close-range.The vision of future Carbon Politics is based on 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The Med-shot Carbon Politics means climate agreement of the“Carbon Politics”.The Close-range Carbon Politics is the direct appeal to the dimatic distribution of the developed country.China is actively looking for the 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energy capital.“To give the energy into civilization”may be selected as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arbon Politics,and the new Chines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will begin from here,so it well privides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understanding Marx communism.
carbon politics;modernity;ecological civilization;to give the energy into civilization
白春雨,中國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博士,博士后(山東 青島 266555)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人文社會科學基地建設項目“自主創新研究”(27R110911B)
(責任編校:彭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