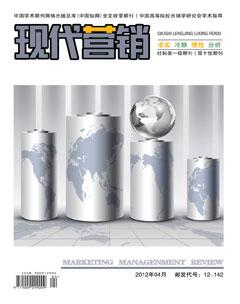近代女畫家潘玉良自我身份的認同與實現心理
林立榮
一、從青樓生涯到藝術殿堂——潘玉良不同尋常的身份形成與演變
在中國二十世紀初的美術史坐標中,潘玉良是一個不能繞開的名字。一方面,作為民國初年最早進行中西藝術合璧實踐并確立了自己獨特面貌的藝術家之一,潘玉良對于中國傳統繪畫在近現代的出路、油畫民族化的實踐乃至東西方美術交流和美術教育所做出的突出貢獻都是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面,由于潘玉良特殊的生平經歷和身份特征,她的影響和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單純的美術史意義而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文化承擔。因此,除了大量的關于潘玉良繪畫藝術及雕塑藝術的研究文章之外,潘玉良及其藝術也引起了文學界和電影界的關注,出現了一些相應的文學著作及影視作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潘玉良不但是一位具有典型特征和美術史意義的女性藝術家,更成為一種折射出民國時期中國的社會、思想、道德和觀念等方面演變的文化符號。
潘玉良,原名陳玉清(一說陳秀清),又名張玉良,字世秀,1899年出生于江蘇揚州。一歲喪父,兩歲時又失去了唯一的姐姐。潘玉良天生倔犟,從小就顯露出不服輸、不怕苦的性格。不堪生活重負的母親在玉良8歲那年終于也離她而去,臨終前將她托付給玉良的舅舅,一個不務正業的癮君子。14歲時,玉良被舅舅賣入安徽蕪湖的一家青樓成為一名雛妓,直到被時任蕪湖海關監督的潘贊化所遇,贖身納為妾。少女時代的幾次大的人生轉折和身份變化,都不幸地降臨在玉良的身上。張玉良的青樓經歷是其一生揮之不去的傷痛和陰影,“雛妓”的恥辱經歷和“小妾”的身份是潘玉良一生在生活和藝術道路上備受歧視和阻撓的主要原因,正因為如此,也形成了潘玉良藝術創作中濃重的身份重建的內在心理動機。
婚后的潘玉良隨丈夫寓居上海,在國畫大師和美術教育家劉海粟先生的建議下,改姓潘。家務之余,潘玉良開始讀書識字,并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色彩學教授洪野先生學習繪畫。潘玉良天資聰慧,毅力過人,進步飛速。民國七年(1918),潘玉良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優異成績考入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師從朱屺瞻、王濟遠學畫。張榜時卻險些由于教務處官員的世俗偏見而未被錄取。劉海粟聞聽后力排眾議,用毛筆在榜文上第一名的右邊空隙處鄭重寫下“潘玉良”三個字。即便如此,由于自己特殊的身世和經歷,潘玉良在學習的過程中仍然困難重重,不斷受到各方面的冷嘲熱諷和阻撓。無奈之下,1921年從上海美專畢業后,在劉海粟的建議和幫助下,潘玉良考取安徽省公費津貼留法的資格,踏上了赴法留學的道路,成為里昂中法大學的第一批學生。潘玉良到達法國1個月后,就投考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師從德卡教授。兩年后成為巴黎國立美術專門學校油畫班的插班生,師從達仰、西蒙學畫,與徐悲鴻同窗。當時的巴黎,是歐洲各種藝術思潮融匯的殿堂,從古希臘、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從法國古典主義、寫實主義、浪漫主義到現代繪畫,各種流派的思想在這里激蕩、交融,紛呈在潘玉良的眼前,這在她早期作品中都有所反映。良好的師資條件和自由的藝術氛圍給了潘玉良汲取營養、施展才華的機會和舞臺。潘玉良如饑似渴地投入到學習和創作當中。很快就在巴黎藝術界嶄露頭角,漸漸為法國乃至歐洲所認可。1925年她以畢業第一名的成績獲取羅馬獎學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進入羅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學習油畫,其繪畫天賦得到繪畫系主任康洛馬蒂教授的賞識,直接升入該系三年級學習,成為該院的第一位中國女畫家。同時,她又在該院雕塑系進修了兩年。1926年她的作品在羅馬國際藝術展覽會上榮獲金質獎,打破了該院歷史上沒有中國人獲獎的記錄。
1928年,受劉海粟邀請,學成后的潘玉良回國任教,出任上海美專教授、繪畫研究所主任兼導師。雖然得到劉海粟及一些同事同仁的信任和支持,潘玉良仍然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和詆毀。正如作家石楠所說:潘玉良雖然血性,但她畢竟是個女人。她不怕別人當面指責過錯,但她怕同行疏遠她、冷落她。她最難忍受的是那種鄙夷的目光和不屑一顧的神情,甚至有時還聽到那種指桑罵槐的諷刺和挖苦。如果說早年一些人的成見還僅僅是出于世俗的保守思想,那么隨著潘玉良藝術聲望的鵲起,潘玉良回國后所遭受的蓄意的侮辱和攻擊則包含了更多的嫉妒色彩。無奈之下,潘玉良接受了當時任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的徐悲鴻的邀請,赴南京出任油畫教授。然而各種阻撓和冷嘲熱諷并沒有因此而消失甚至減少,少數同仁的精神慰藉和鼓勵并不能改變潘玉良窘迫的社會空間,也不能消弭潘贊化的原配夫人的敵視和排擠。潘玉良無法忍受這樣窒息的生活和藝術環境,只好再次踏上加拿大皇后號郵輪遠赴法國,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二、潘玉良——作為自我慰藉和身份認同的藝術
潘玉良的一生,是與命運不懈抗爭的一生,是為了自由、愛情和藝術執著奮斗的一生,從深層的心理動機分析,也是她不斷地尋求自我身份的認同與實現的一生。潘玉良坎坷的一生中擁有比別人復雜得多的身份特征:孤兒、雛妓、小妾、西畫學生、教授……雖然潘玉良最終贏得了大多數人的尊重和認可,在藝術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她心理深處的那份“身份情結”卻是一生也揮之不去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潘玉良是通過藝術的方式來實現她在現實中被無情地剝奪了的身份特征和生命尊嚴。作為一位有血有肉、對于生活、愛情和藝術有著正常而合理追求的女性,潘玉良在當時卻無法像其他普通的女性一樣享受她本應得到的東西。在世俗偏見的重壓面前,潘玉良只有通過她所鐘情的藝術來給自己撫慰傷口,并獲得直面命運的勇氣和力量。潘玉良的藝術是她尋求身份認同與實現的途徑和載體,是她那顆孤獨、憂傷而又滿懷對生活、愛情和藝術熱望的心靈尋求歸屬感和價值實現的語言形式。
心理學的研究表明,藝術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是藝術家尋求自我身份認同與實現的途徑。曲折坎坷的生活經歷和學藝過程造就了潘玉良特殊的心理特征。動蕩的時局,世俗的偏見和學藝過程中受到的阻撓,對生活、愛情和藝術的執著和熱望,以及東西方思想文化藝術的沖突碰撞,等等,必然在潘玉良的內心世界造成巨大的影響,進而形成了其極具個性的心理特征和藝術動機,也使得潘玉良有著比一般人更加迫切的身份認同和實現的需求與沖動。在具體創作上,潘玉良將東方式的內斂和韻味揉入到西方的色彩和造型之中,形成了含蓄、傷感、堅強、執著而又熱烈的藝術面貌,充分表現出畫家以及既矛盾又統一的復雜的心理情感。
特殊的心理情感表達動機必然選擇個性的畫面語言。題材的選擇和偏好,用線、用筆、色彩、構圖的特點等等,都不同程度地透露出潘玉良的身份意識,這種身份意識包含了作為女性藝術家和作為東方藝術家身份的自我確認和實現。比如潘玉良大量的人體畫和自畫像反映了她的一種女性身份情結,是對自己特殊的人生經歷與記憶的和時人對于女性、女性藝術家和女性美的保守、狹隘認識的反撥。從繪畫題材上來看,潘玉良描繪了大量不同姿態、不同國籍的年輕女性的優美動人的人體畫,包括油畫、國畫和素描等。在民國初期的中國,封建保守思想根深蒂固,人們對于女子從事繪畫已經沒有多少包容心,更何況是直接表現女性身體的人體畫?而對于潘玉良來說,這樣直白、大量地表現女人體無疑是把自己放在了世俗偏見的風口浪尖之上。對于人體畫的偏愛,固然是因為西方繪畫的影響,但更深刻的動機是潘玉良要以這種描繪健康、優美的人體的方式來迎接世俗偏見的挑戰,揭露那些虛偽的衛道士的丑惡嘴臉和陰暗心理,真正實現自己作為一位女性藝術家的身份和尊嚴的重建。這些女人體線條細膩流暢,典雅寧靜,姿態優美,散發著濃郁的東方女性溫柔的性格特征和含蓄的精神氣質,體現了潘玉良對于女性美的偏執、自信和追求,也表達出畫家對自身的肯定以及渴望得到認可的內在動因。相比于人體畫,潘玉良的自畫像是畫家與自己更為直接的觀照和對話。這些創作于不同時期的、姿態各異的自畫像則真實地表現出了畫家不同階段的心理和精神面貌。這些自畫像大都面向觀眾,嘴唇緊閉,眼睛里透露出掩飾不住的哀愁,讓人看了心里有種隱隱的痛。雖然畫面因為受到野獸派的影響而色彩鮮艷濃重,但仍然讓人清晰地感受到畫家一生也揮之不去的凄涼和孤獨,流露出潘玉良對晚年仍客居異鄉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惆悵。
除了作為女性和女性藝術家的身份自我認同與實現的動機之外,作為一位中國藝術家,在民國時期東西方文化和藝術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潘玉良同樣面臨著如何既從西方藝術那里汲取有益因素,又要保持東方藝術精神特質,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面貌的時代課題。要想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創新,離開本民族傳統藝術中的優秀遺產而空談中西合璧或者中西融合等等都是不切實際的。在藝術大師劉海粟、徐悲鴻等先生的悉心指導下,潘玉良潛心研究了宋、元、明、清的一些中國畫的優秀作品,悉心加以臨摹,對于傳統白描在技法和精神兩個層面上進行了認真的學習和體悟。潘玉良采擷融匯中西繪畫語言之所長,加以改造和創新,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繪畫語言形式,形成了美術史上引人注目的“新白描體”。陳獨秀在她的作品上題跋曰:“余識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今見此新白描體,知其進猶未已也。”潘玉良以歐洲油畫雕塑之神味入中國之白描是符合陳獨秀所強調的“畫家必須用寫實主義才能發揮自己的天才,畫自己的畫,不落古人的巢臼”的主張的,契合了陳獨秀用西畫精神改造中國畫的觀點。這種運用中國畫的線描形式,西方繪畫的造型方法的“新白描體”實際上是對中國繪畫結合的一個初次探索和嘗試,是借鑒了中國畫的筆墨特點,來表現西畫的立體感和透視感,是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最早進行中西融合的藝術家之一。
三、結語
潘玉良的作品合中西畫之長,又富于個性色彩。她的油畫含有中國傳統水墨畫技法,用清雅的色調點染畫面,色彩的深淺疏密與線體互相依存,很自然地顯露出遠近明暗、虛實、氣韻生動。同時,又大膽地將西方油畫特有的體積感和色彩表現力同中國傳統藝術元素相結合,終于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面貌,成為民國時期中國畫壇一道獨特的風景。潘玉良的藝術不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繪畫僵化的模仿和延續,也不是西方油畫的簡單借用,而是通過自己的才情和努力,使得兩者相互融合,取長補短,創造出的一種新的藝術樣式。潘玉良的藝術,對于中國傳統繪畫在新時期的延續和發展,以及油畫民族化的探索,提出了具有鮮明個性特點的解決方案和啟示,直到今天,仍然有著其鮮活的生命力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