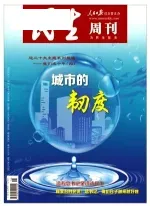誰揭開了1942大饑荒內幕
□ 鄧凌原
誰揭開了1942大饑荒內幕
□ 鄧凌原

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期真實照片
電影《一九四二》將站在2012尾巴上的國人的目光瞬間拉回到70年前。同樣是雪花飄飛的十二月,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還未從年復一年的抗戰中贏得絲毫喘息之機,又將眼睜睜地看著她的子民在饑寒交迫中流離失所,坐以待斃。
中原大地“赤地千里”,“哀鴻遍地”,災民“嗷嗷待哺”,這是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發出的十萬火急的電報中所描述的災區真相。然而,官方卻寧愿相信這是地方政府慣用的陳詞濫調,并嚴令向這個地區所征的實物稅和軍糧任務不變。
戰亂,天災,人禍,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蔓延。直到有一天,一位年僅24歲的大學畢業生走進河南,用淌著血淚的文字揭開了河南大饑荒的內幕。
事實真相
1942年12月,由四川途徑陜西前往河南的官道上,殘陽如血。一個身背簡單行囊的年輕人正在匆匆前行,他叫張高峰,武漢大學政治系本科畢業生,《大公報》派駐河南的戰地記者。
這是一條有著上千年歷史的古道,因崎嶇難行而被一個豁達不羈的詩人寫入詩歌而名揚天下。“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此刻,腳步匆匆的張高峰無心去吟詠《蜀道難》中的千古名句,但眼前這兩句詩,總是不由自主地浮現在腦海中,揮之不去。
一路走來,眼前的一幕幕景象早已讓他目瞪口呆:在西安城內,沿街乞討的河南災民“個個鳩形鵠面”,呼救之聲不絕于耳;由陜西進入河南時,“隴海路上河南災民成千成萬逃亡陜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
到了昔日繁華的洛陽街頭,眼前的景象更加讓人觸目驚心:到處都是“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他們伸出來的手,盡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們全身,會誤以為是一張生理骨干掛圖”,這些蒼老的乞丐“一個個邁著踉蹌步子,叫不應,哭無淚,無聲無響的餓斃街頭”。
在洛陽火車站,災民們紛紛扒火車逃往西安方向。一位年輕人對張高峰哭訴:“先生,我娘與老婆都上了車,我在后面推這獨輪小車,巡警不準我進站,眼看那火車要開了,誰領著她們要飯哪!老爺,請你給我說說情吧!叫我上車。”出于同情,張高峰領著他到“難民登記站”去向負責人交涉,誰知背后卻跟來了同樣情形的三十幾人。
在“難民登記站”,張高峰看到幾百人圍著兩張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罵一面蓋圖章,警察的一根柳條不停地敲打災民。最終,由于“擠不進那重重的人群,無法回答那三十位災胞”,張高峰只好“從另一條路慚愧地溜走了”。
從洛陽開始,張高峰的足跡遍及豫西、豫東和臨汝、寶豐、葉縣、魯山、許昌、西華、淮陽等地。在葉縣,由于樹葉已經吃完,村民每天都在村口用杵臼搗花生皮和榆樹皮,然后蒸著吃。一個孩子問張高峰:“先生!這家伙刺嗓子,什么時候官家放糧呢?”“月內就放。”張高峰只好用謊話來安慰他。所有人的臉都是浮腫的,鼻孔與眼角發黑,手腳麻痛。物價已經漲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許多人被迫賣掉自己的年輕妻子或女兒去做娼妓,而賣一口人,還換不回四斗糧食……
秉筆直書
出于記者的良知和責任感,被事實真相所震撼張高峰決定將此次采訪行程的重點,從報道戰事轉為報道河南災情。
1943年1月17日,張高峰從葉縣寄出6000多字的長篇通訊《饑餓的河南》,并用犀利的文筆詳盡記述了水、旱、蝗等天災給河南百姓帶來的苦難,披露了當局不顧人民死活橫征暴斂的人禍加劇災情的事實,批評政府的不作為。
不久,《大公報》主編王蕓生便收到了這份沉甸甸的現場報道。一口氣讀完全文后,滿眼淚花的王蕓生深感事體重大,為了通過當時的新聞檢查,他將《饑餓的河南》改題為《豫災實錄》,并未經任何刪改發表于2月1日《大公報》。這一天正好是臘月二十七,距離農歷新年僅3天。
盡管事后張高峰對標題的更改并不滿意,認為“純客觀,平淡無力”,但報社“敢于把一個24歲年輕記者如此尖銳披露災情、批評政府的報道一字不改地刊登出來”,還是讓他十分感動。
其實,慧眼獨具的王蕓生采用的是與《大公報》前任總編輯張秀鸞一脈相承的做法:凡是平淡的內容,無妨將題標得耀眼些;如果內容充實,有顯然的刺激性,標題反倒可以平淡些。
在迎接農歷新年的鞭炮聲中,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代悲劇里,《豫災實錄》使被遮掩的河南大饑荒最終大白于天下,并瞬間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
第二天,王蕓生在《大公報》發表社論《看重慶,念中原》。他在文中寫道:“讀了這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見于今日的事實。”“誰知道那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在饑饉死亡的地獄。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干樹皮的忍不住剌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換到幾斗糧食……”
此外,文章還將重慶的燈紅酒綠與河南的赤地千里作對比,并詰問道:“災民賣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發豪商巨富的資產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張高峰事件”
這是王蕓生一生中最著名的一篇評論,像一篇討伐當局的檄文,讓人拍案叫絕。然而等待他的,是《大公報》停刊3天的處罰。
《大公報》的報道和社論,讓蔣介石勃然大怒。他認為《大公報》“危言聳聽,有礙抗戰”,當天即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勒令《大公報》停刊三天以示懲誡。《大公報》被迫“遵命”于 2 月3、4、5 日停刊。王蕓生后來回憶說:“這篇文章不足寫盡任務之萬一,竟如此觸怒蔣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壓迫輿論。”
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停刊事件卻給《大公報》帶來了意外的收獲。當時,《大公報》的發行數是每天6萬份。重慶市民聽說《大公報》因發表社評被罰,都想看看這篇文章,到處去買報紙,結果報紙銷路大漲。停刊3天后,《大公報》的發行量由6萬份增至10萬份。
與此同時,由于《豫災實錄》觸及到在河南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湯恩伯的利益,蔣介石下令嚴查其縱兵殃民的事實真相,湯恩伯惱羞成怒,遷怒于張高峰,以編造虛構的罪名將他逮捕,關押在漯河警備司令部看守所。這在當時被稱為“張高峰事件”。
警備司令李銑和張高峰原很熟識,他便借口漯河距前線太近,以不安全為托詞,經湯恩伯批準,將張高峰轉押于78 軍軍法處看守所。
由于《大公報》時時催問蔣介石,要求恢復張高峰的自由,1943 年8月,78 軍軍長賴汝雄向湯恩伯匯報說,經多次審訊和調查,沒有發現“張高峰有任何政治背景”,湯恩伯最終決定將張高峰釋放。
從來盛氣凌人的湯恩伯,不僅向張高峰道歉,要張高峰勿計前嫌,還希望他繼續留在河南。但張高峰答道:“我在河南已很難工作。總司令如果放我,保證三天之內離開河南地采訪。”湯恩伯見張高峰不給面子,勃然大怒,將張高峰軟禁于毗鄰河南的安徽界首,準許發稿,但不能擅離駐地。直到日軍大舉進攻中原,湯部潰不成軍,張高峰才得以趁機脫逃,經陜西回到重慶。
回到重慶后,《大公報》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歡迎茶話會,對張高峰發揚正氣、不畏權勢,在河南猛拔虎須、大膽揭露湯恩伯倒行逆施的做法,給予很高的評價。至此,轟動河南的“張高峰事件”才劃上了句號。
□ 編輯 張子琦 □ 美編 徐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