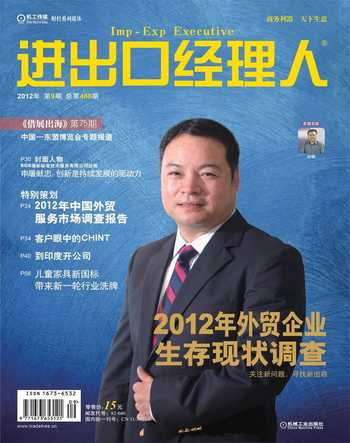船舶滯期爭議大,合同證據是關鍵
牛紅巖
2011年3月,H公司與G公司簽訂一份航次租船合同,約定由H公司提供J輪給G公司用于進口運輸一票煤炭貨物,起運港為國外Q港,到達港為青島港。合同約定,裝48小時,卸48小時,滯期費率為人民幣2萬元/天。
J輪于2011年3月4日17:30時抵達Q港錨地拋錨等候靠泊,3月11日16:25時靠泊,3月12日07:00時裝貨完畢后發現煤炭自燃,當日19:00時移泊至另一碼頭卸貨處理后再裝貨,14日23:21時開航。3月17日抵達青島錨地,20日中午靠泊卸貨,3月21日14:00時離開碼頭。裝卸時間合計為14天半,扣除合同約定的4天裝卸貨時間,按照約定,滯期費為人民幣21萬元。
據此,H公司在青島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要求G公司支付上述滯期費。
抗辯意見
我們作為國內G公司的法律顧問,首先在應訴前向G公司客觀分析了本案的基本事實和不利局面,認為租船合同約定的裝卸貨時間明確,在裝貨港移泊處理貨物著火事故時,H公司客觀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對貨物進行了先卸后裝、澆水滅火等施救措施。雖然本案敗訴是必然的,但我們可以從計算裝卸貨時間的細節上尋找對方證據的不完善之處,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G公司承擔的滯期費數額。
因此,我們作為G公司的代理人,主要提出了以下抗辯觀點:涉案租船合同履行過程中,并未發生滯期,H公司無權索要滯期費。
一、H公司只能以裝卸作業實際開始的時間為準計算裝卸時間。
合同約定的出租方以“錨地起算”方式計算裝卸時間的前提義務是“船舶到達錨地,并做好裝卸準備;出租人履行通知義務,向承運方遞交《裝卸準備就緒通知書》。”庭審中,H公司僅通過航海日志證明了船舶到達錨地并申請靠泊,但沒有證明其履行了通知義務,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
二、涉案裝卸時間的計算方式應當是“正常工作小時+加班的工作小時”。
租船合同約定裝船期限48小時、卸船期限48小時,兩港合并計算。根據《合同法》第41條的規定“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因此,涉案裝卸時間的計算單位“小時”,應當解釋為“工作小時”。法定工作小時為40個工作小時(每周有5天工作日、每個工作日有8個小時)。因此,裝貨時間為11小時,卸貨時間為16小時,合并為27小時。
三、煤炭貨物于2011年3月12日0630時已經裝貨完畢,之后船舶移泊先卸貨后又重新裝貨的時間是H公司采取滅火措施的時間,該段時間與法律意義上貨物交接的“裝卸”無關,不應計入裝卸時間。
我們作為被告G公司律師提出的上述三個觀點,實際上涉及了司法實踐中關于船舶滯期費問題的幾個焦點問題:
(1)起算裝卸時間的標準。
(2)裝卸時間以工作小時還是以實際小時來計算。
(3)裝貨完畢后,對貨物采取施救措施的時間,是否算是裝卸時間。
我們的訴訟策略是,只要我們的上述三個抗辯理由能夠得到法院的部分支持,我方就可能勝訴大部分。
案情解析
本案歷經多次開庭,對大量紛繁復雜的證據進行舉證、質證,又經過多輪法庭辯論,法院最終在尊重事實、公平公正的基礎上,依法做出以下判定:
關于起算時間
按照航次租船合同的約定,裝貨時間從船舶到達錨地起算。本院認為,我國的海商法并沒有規定在租船合同中必須訂立發出《裝卸準備就緒通知書》作為計算滯期費的前提,雙方在運輸合同中約定以船舶到達錨地開始計算裝卸時間,系合同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與法無悖,應予支持。J輪到達錨地后,及時報告交管部門,應視為通知的一種方式。而且租船合同約定船舶的受載期為3月4日,J輪確于改日到達錨地,G公司可以查詢交管獲知該日船舶已經到達。因此,G公司關于未發送《裝卸準備就緒通知書》則不能計算滯期費的抗辯理由不予支持,裝船時間應當從船舶到達錨地時起算。
關于工作小時問題
G公司不能證明裝貨港Q港裝卸作業部門的工作時間是8小時,不排除該港裝卸作業部門連續24小時進行裝卸作業的可能性,實際上通過航海日志的記載可以看出Q港是連續24小時進行的裝船作業,因此,G公司的該抗辯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裝港采取滅火排險措施的時間
根據航海日志記載,其滅火措施占用的時間為:2011年3月12日15:15被港調通知移泊,22:25時卸貨,3月13日19:07時卸貨完畢;3月14日11:55時裝貨,18:30時裝貨完畢。滅火措施的時間為53.5小時。
對此,法院認為,《國內水路貨物運輸規則》第三十二條規定“承運人應當妥善地裝載、搬移、積載、運輸、保管、照料和卸載所運貨物,即承運人的管貨義務”,第三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承運人知道危險貨物的性質并同意裝運的,仍然可以在該項貨物對于船舶、人員或者其他貨物構成實際危險時,將貨物卸下、銷毀或者使之不能為害,而承運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因此,在3月12日06:30時裝貨完畢后,就應開始H公司的管貨期間。H公司在管貨期間就發生自燃的已裝船的部分貨物采取“使之不能為害”的措施,即對發生自燃的貨物進行澆水滅火,但由于船舶滿載,不得不先將貨物卸到岸上進行澆水滅火,而后裝回船上。因此,在裝港發生的卸船而后裝船的措施,是H公司在履行管貨義務期間的合法處理危險貨物的滅火措施的組成部分,不是裝卸作業的組成部分。裝卸時間是特指貨物交接過程中所使用的時間,而涉案施救措施僅是H公司接收貨物之后的行為,是單方面采取的,而不是G公司與H公司交接貨物的行為過程。因此,該滅火措施所花費的時間,不屬于裝貨作業的范疇,不應計入裝卸時間。
同時,涉案航次租船合同第一條約定“承租方必須保證裝卸港各一個安全泊位,航線原則上不得更改,若需改港、移泊,須經出租方同意,所產生的所有費用由承租方負責(影響時間計入裝卸時間),否則出租方有權拒絕要求,并視為承租方違約”。如果G公司要求移泊的,須經H公司同意,并由G公司承擔所有費用,并列入裝卸時間。但涉案裝港發生的移泊并不是G公司要求的,而是H公司在履行管貨義務過程中采取處理危險貨物的滅火措施的組成部分,因此該移泊所產生的費用和時間不屬于上述合同條款的范疇,不能根據該條款的約定進行責任歸屬。因此,G公司關于該段時間與裝卸作業無關,不應計入裝船時間的主張,本院予以支持。
綜合以上因素,計算得出滯期時間為63.54小時,因此判令G公司向H公司支付的滯期費數額為52949元。本案一審判決后,雙方服判,現已履行完畢。
律師建議
本案的判決結果,雖然對G公司來說,已減少了大部分損失,但我們從防范法律風險的角度來講,對于船舶出租人、承租人來說,還需在合同簽訂、證據保留等方面加強法律風險的防范:
明確租船合同中起算時間的標準。關于如何開始起算裝卸貨時間,需明確選定以提交《裝卸準備就緒通知書》或者以到達錨地、裝卸碼頭或者報告交管部門等標準,以免發生糾紛時,雙方對如何界定裝卸時間產生起算標準上的爭議。
工作小時、實際裝卸小時的約定。出租人、承租人應當對計劃前往的裝卸港口的工作時間(8小時工作制,還是24小時連續作業)有充分的了解,在租船合同中予以明確。
在進行貨物裝卸、裝貨完畢后的管貨過程中,出租人在采取措施前,要取得承租人對各項措施的書面認可;即使當時情況緊急的,也應在事后由承租人對措施進行書面追認,只有這樣,才能保留好證據,最大限度的保護出租人的權益。
無論對于裝卸貨時間、采取事故處理措施的時間,出租人必須要在航海日志中明確記載其過程、時間、人工、花費,并留存好費用單據等必要的證據,以免向承租人主張滯期費時,出現舉證不能的尷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