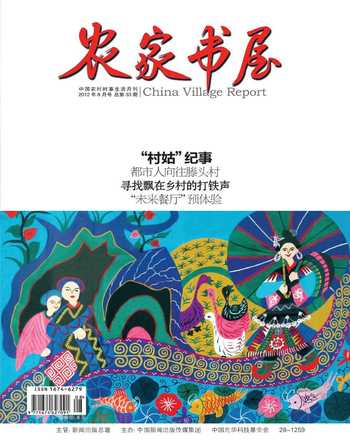消失中的鄉村詞匯
蘇姝
近年來,都市農業蓬勃興起,“社區菜園”、“陽臺種菜”、“屋頂農業”、“都市農民”……這些新詞悄悄融入我們的生活,讓因為城鎮化而逐漸遠去的鄉村再次走進我們的視野。但是我們逐漸發現田園風光可以復制,但鄉村味道卻無處可尋,因為每一段鄉村記憶背后都隱藏著一個時代,當新時代取而代之后,記憶中的那個鄉村自然也悄然遠去,只是那個時代留下的許多特定詞語,有時會讓人忍不住回憶過往。
1958年到1978年,在中國有一個風行一時的政經合一的鄉級組織,叫作“人民公社”。公社有糧庫,四周是青磚刷著白石灰的矮墻頭,墻體上寫著朱紅色的大字,不外乎“保障糧食供給”或“綱舉目張”之類的語錄。那些戴著大白帽子的糧倉,比幾間房占的面積都大。每逢交公糧時候,糧庫外面的馬路上都會排著一溜兒長長的馬車,周圍的村莊,都來一個糧庫交公糧,所以那個時段的熱鬧可想而知。糧庫收糧食,不是來者必收,必須經過驗收,符合要求才能把自家麻袋里的糧食倒進糧庫的糧倉里。交不成公糧,只有一個原因,水分大。水分大的糧食不但自己容易發霉,而且會“傳染”。一般來講,糧食在場院中曬干,揚到空中彼此能碰出聲響,放到牙齒間,“咯崩”一聲能被咬碎,就表示基本達到交公糧的標準了。糧食入庫把關很嚴,許多人都有把糧食拉回去重新晾曬的痛苦經歷。后來,考慮到糧食運輸得不易,許多糧庫改進了措施,對不符合交征條件的糧食,不再強迫農民拉回去,而是在院子里提供場地,讓各個生產隊派人來就地晾曬。
作為計劃經濟下的產物,“工分”可說是當時農民的命根子。鄉下村村都有生產隊,生產隊分口糧是按人頭分,口糧以外的雜糧或農副產品有時會按勞力分,而年底分紅則一定是按工分分,工分掙得多的人家到年底能分到百八十塊錢。每年的年假過去以后,生產隊第一件事就是開評分會。會計一個接一個地念社員名字,每念一個,隊長就征求大家的意見,那些公認的好勞力就不用說了,一天掙十分。而那些未婚姑娘或家庭婦女,力氣小,身體孱弱,能得多少工分就難說了,第一個喊出分值的人很關鍵,因為很多時候就是一錘定音。同樣是干一天活兒,有人掙十分,有人掙八分,有人卻只能掙五分六分,評分會是很殘酷的。
生產隊里最值錢的家當,當數那掛馬車了。當然不單指車,還有拉車的那三匹馬。老馬駕轅,兩匹二青子馬拉套。車當然不止一掛,還有驢車和牛車,但驢車和牛車都只能干些零碎活,所以趕驢車和牛車的人都不能稱“把式”,他們只能叫趕車的。趕馬車的人就不同了,“一等人跑外交,恒大煙卷嘴里叼;二等人趕大車,小鞭兒一搖一塊多……”這是20世紀70年代民間流傳的順口溜。車把式每天除了掙工分,還有一塊多的補助,地位甚至高過隊長,是一個“上等”職業。車把式對大牲口的感情,就跟對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摸摸馬的臉,捏捏它們的耳朵,或捂住它們的鼻子,讓它們把熱氣噴到自己的手上。偶爾用眼睛和馬“交流”,馬的眼神中充滿情愫。不拉腳的時候,大車顯眼地停在隊部的場院里,駕轅的馬和拉套的馬在一個槽子里吃料。它們吃的草料也與別的牲口不同,是精飼料,里面有豆餅。趕集的日子,不管有多少人,統統都擠到一輛車上,車幫、車轅上都坐著人,不管車上坐了多少人,三匹馬都能步調一致地往前跑。馬騰著小碎步,蹄聲清脆,馬鈴兒悠揚,車廂有節奏地顛簸,把一車人晃得心曠神怡。
的確,當我們向老人們提及關于公社、工分這些詞語的時候,他們都可以滔滔不絕地聊上好幾個小時,情緒激昂,因為那些都是他們曾經經歷的、與他們的榮辱密切相關的東西。每一個詞語背后承載的不僅僅是那個時代的印記,還有那個時代人們的青春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