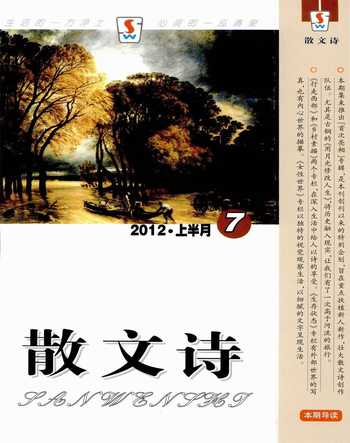賞析
許淇
當(dāng)今世界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由于突破思想和創(chuàng)作方法的樊籬。完成的文本,往往是跨文體寫作,散文詩尤其如此。其創(chuàng)作方法不僅沖破分行的詩和不分行的散文的界限,沖破平仄、頓數(shù)、無韻甚至自然韻甚至拗口艱澀的規(guī)律,還可以廣泛吸取姊妹藝術(shù)體裁的優(yōu)點,融會貫通,獨立成章。如借鑒影視的蒙太奇鏡頭分割法,并不必須具有嚴(yán)密的邏輯性,每一畫面只須服務(wù)于主題。那是一種線性思維狀態(tài)。潛在意識的流動有時是反邏輯的,但人性的深處有某種暗示偶然的必然。當(dāng)今的詩和散文詩必須寫出這種暗示,方為真實。
此處選賞的埃斯普馬克的后一章:《83》。除第一、二句有關(guān)聯(lián)外,以下一句一個鏡頭,互相獨立,組合在一起,形成互為作用的內(nèi)在的意象的鏈。即“花園”作為契機(jī)。和“你”邂逅。心靈的震波,使外在世界共鳴。正如特朗斯特羅姆所說:“……試圖在被常規(guī)語言分隔的現(xiàn)實的不同領(lǐng)域之間建立一種突然的聯(lián)系:風(fēng)景中的大小細(xì)節(jié)的匯集,不同的人文相遇,自然和工業(yè)交錯等等,就像對立物揭示彼此的聯(lián)系一樣。”(北島譯)本期所選出自翻譯家李笠新出版的《黑銀河》詩集中。卷首有埃斯普馬克為中譯本出版寫的前言。前言開頭說,對豐富的中國文學(xué),“遠(yuǎn)自《道德經(jīng)》、唐代大師乃至當(dāng)代詩人,一直懷有敬慕之意”,“我覺得我的詩與中國大師所追求的言簡意賅、用象表意為最高境界的詩藝是一致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賞析他的詩和散文詩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但埃斯普馬克比較新得“諾獎”的特朗斯特羅姆要貼近社會、介入政治,特朗斯特羅姆作為詩人更深邃、更清脫、更接近中國的“大言無聲”。埃斯普馬克常常借助歷史事件影射和抨擊當(dāng)今社會,具有詩人的責(zé)任感和歷史擔(dān)當(dāng),如《我永遠(yuǎn)叫曼德斯坦姆》,用曼德斯坦姆在集中營的思想感受為第一人稱,抨擊迫害他的獨裁者,他寫道:“國父(指斯大林)清楚地知道陰間怎樣構(gòu)成,他活著,國家卻好像早已消亡。”他當(dāng)評委,將“諾獎”授予被前蘇聯(lián)驅(qū)逐出境的詩人布羅茨基,就一點也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