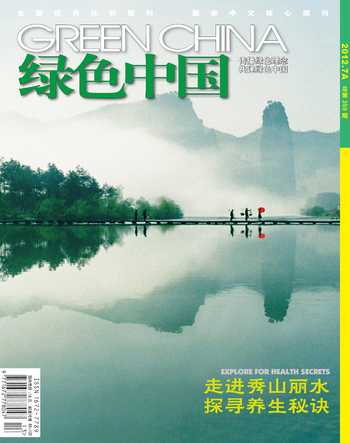中國人的幸福與吃(外一篇)
宗仁發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云:“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漢書·酈食其傳》中將此觀點抄改為:“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由此可見吃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對吃的重視是分為若干層次的,第一個層次是解決饑餓的問題,即達到溫飽中的“飽”的指標。歷史的政治經驗中有一條叫無糧不穩,要是糧食缺了,餓死人的話,國家的穩定勢必受到影響。
第二個層次則是如何吃得好的問題,東北人講:“舒服不如躺著,好吃不如餃子。”這后半句是“初級階段”吃得好的標準。吃得好的標準會因時地的不同而千差萬別。符中士在《吃的自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9月)一書中談到中國人吃得范圍之廣是:“有腿的板凳不吃,有翅膀的飛機不吃,其他什么都吃。”“山珍海味,飛禽走獸,螟蟲蛆蛹,植物根、莖、葉、花、果,甚至有毒的蛇蟒、蜈蚣、蝎子、河豚,無所不吃。”這吃得好的廣度可見一斑。不僅如此,吃得好中還包含吃得奇特,符先生認為,“令西方人難以理解的,是把動物的生殖器官和排泄器官也拿來吃。幸好他還不知道中國人吃嬰兒的胎衣,否則他們不嚇個半死才怪!”對中國飯菜的贊譽莫過于符先生所引用的東南亞地區流行的說法:“住英國房子,坐德國車子,穿法國衣服,娶日本太太,吃中國飯菜。”顯然國際上吃的標準應以中國為最高。
然而吃無止境,吃海無涯。吃還要不斷延伸,不斷拓展。吃與政治結緣,便有了:吃透精神、吃不準、不要吃老本之類;吃與經濟相關,便有了:吃大鍋飯,分灶吃飯,吃進,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等等;吃與法律為吃官司;吃與軍事為吃緊;吃與勞動為吃力、吃苦;吃與環境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與美人叫秀色可餐。吃中的酸甜苦辣便也是人生的全部滋味,說某某的一段經歷坎坷叫令人感到辛酸,說某某的愛情生活美滿叫甜甜蜜蜜,說某某的性格有棱有角叫十分潑辣,說某某的一生歷盡艱辛是苦了一輩子。辦喜事要吃,以示喜慶;辦喪事也要吃,以寄哀思。簽合同要吃,吃了便算敲定;鬧了糾紛調解了也要吃,吃的就是講和飯。天天都吃的飯叫家常飯,年年節節吃的是團圓飯。更為有意思的是符先生把吃辣椒與出人才聯系在一起,他認為清代以前,湖南幾乎沒有出過歷史名人,自晚清以來,湖南人開始吃辣椒,吃得成熟后,曾國藩、左宗棠、譚嗣同、黃興、蔡鍔、程潛、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胡耀邦等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就冒出來了,這里辣椒之功是不可沒的。怪不得毛澤東同志說,“不吃辣椒不革命”,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
移民與東北
移民一般來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主動型,即由甲地遷往乙地是移民者自愿自由選擇的;另一種是被動型,即由甲地遷往乙地是由他者(如官方)決定的。東北地區遼金以來的移民主要是被動型的,這其中在遼金時期大多為戰俘。契丹人和女真人在進攻中原時,每摧城拔寨后,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盡徒其民以歸”(見《遼史》卷1《太祖紀》,第1?2頁)。金兵當年從開封北撒時,“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余萬。”(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中華書局,第92頁)遼金時期通過戰爭大規模掠奪中原人口移民東北,其目的是為我所用。因為東北土著人口數量有限,人力資源匱乏,被強制遷移到東北的中原人,主要是從事農耕活動。據史料記載,遼金時期東北地區人口總量約有三分之二為中原人,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講,正是大量的移民,使東北地區生產方式由游牧漁獵轉變為農耕冶煉。從文化發展角度講,中原文化自然以強勢封建文化改變著弱勢的東北土著原始文化。到了清代,起初曾采取了一些鼓勵關(山海關)里人移民東北墾荒的政策,順治八年(1651年)朝廷首次下達允許百姓出關墾荒的命令:“以山海關外荒地甚多,民人愿出關墾荒者,令山海道造冊報部,分地居住。”(見《皇朝文獻通考》卷1)。順治十年,還頒布了“遼東招民墾荒授官條例”,具體規定,以招民之多少,來決定所授官職。被招來的百姓,朝廷發給口糧、種子和耕牛。康熙七年(1668年)朝廷政策陡變,取消了開墾條例,開始了長達二百余年的封禁政策,直至光緒三十年(1904年)才開禁。在封禁期間,也有一批特殊的移民,即被朝廷流放到東北的“流人”。
“流人”中多是由于清代大興“文字獄”而獲罪的漢族士大夫,他們在被流放東北期間,帶來了東北地區文化發展的活躍狀態。
一言以蔽之,東北地區的發展史即是一部難以寫盡的移民史。二十世紀以來,東北地區移民除了百姓主動遷入以外,還有殖民地期間的勞工移民,也有解放戰爭期間的軍人移民。如今生活在東北地區的漢族人中,最多的一支應屬山東人。東北人中如果不是少數民族,十有八九祖籍便是山東,“老家在山東”幾乎是相互陌生的東北人的口頭禪。
當代的山東移民現象被人們稱之為“闖關東”,之所以要闖關東,是因為關東地廣人稀,沃野無限,“棒打野雞瓢舀魚”,而山東人口相對稠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每遇荒災,生存便面臨嚴峻的考驗。新移民和已經定居東北的舊移民之間有兩類關系,一類是如有家族淵源或村屯同鄉,呈現為吸引關系;另一類則是與新移民不相識的定居者,則呈現出排斥關系,他們甚至是以“盲流”來稱謂那些后來者,這也透露出那個年代戶籍制度造成的等級差別,所謂“黑戶”就是指這些上不了戶口的移民家庭。由于時間的推移,慢慢地這些新移民終于被接納,融入正常的生活秩序當中,只是晚來者的鄉音難改,總會讓人識別出是山東人。
(責編:耿國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