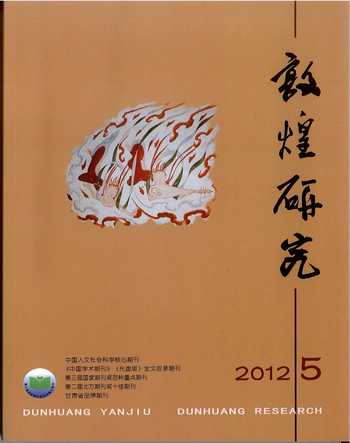石窟藝術筆記
久野美樹 賀小萍
內容摘要:本文探討敦煌莫高窟與龍門石窟造像的思想背景,列舉了基于“一即多,多即一”法則的“諸佛”概念、“本跡思想”作用的事實。盡管初唐莫高窟出現了大幅式的阿彌陀凈土變,但正壁多為釋迦系造像,信仰中心仍然以法身與釋迦為主。初盛唐時期莫高窟與龍門石窟的造像主題、形式迥然不同,是由于兩處石窟的功能、作用異同所致。
關鍵詞: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隋唐時期;造像思想
中圖分類號:G879.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2)05-0001-08
研究石窟藝術時,對所表現的圖像、主題一一作比較、考證固然很重要,但偶爾體驗一下“中國造型思想的背景、思想的潛在趨勢”或“每個石窟的作用、功能”,以俯瞰之目光觀察石窟藝術也極其重要。
本稿首先從“造型思想背景”、“造型形式”上,對敦煌莫高窟北朝到隋唐時期石窟中所見的“傳統”以及初唐時期窟中表現的“革新”作一考慮。
另外,位于洛陽郊外的龍門石窟也有許多初唐的造像,但是,其主題與同時期的敦煌莫高窟迥然不同。因此,將在問題二中,對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試作分析。
一
雖然在莫高窟現存最早的5世紀圖像中可看到本生圖、因緣圖這種小乘佛教的傾向,但正如北魏窟中基于《法華經·見寶塔品》表現二佛并坐像那樣,初期洞窟已經出現了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中的關鍵概念可舉“諸佛”、“十方諸佛”[1]。佛教本來講“一世界,一佛論”,一個世界只出現一個佛,可是,大乘佛教認為這個世界并非唯一的世界,另外還有世界,同時誕生了復數佛俱立的“多佛思想”、“他方佛的想法”[2,3]。有關北朝時期莫高窟所造的許多千佛、十方諸佛,賀世哲先生等已有詳細研究[2][4-6],賀世哲先生認為,造千佛的目的是修行者為了坐禪觀佛,一般信徒為了祈禱消災滅難,來世往生佛國凈土[2]139。另外,吉藏(549—623)撰《觀無量壽經義疏》中對三世佛與十方佛的關系作了明確闡述:(文中劃橫線處為重點)①“如來出世,欲使眾生同悟一道,但眾生根性非一。故有教門殊致。”“《無量觀》辨十方佛化、《彌勒經》明三世佛化。十方佛化即是橫化,三世佛化即是豎化。”又,中國南北朝造像記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現象,有“凈土,生于天,遇諸佛,信奉諸佛”的愿文[7]。
在南北朝佛教信徒心中“諸佛”存在的基礎,是整個大乘佛教以《華嚴經》為中心講的“一即多,多即一”之義理②。正如前述吉藏所言,稱作千佛、十方諸佛的“諸佛造型”中包含著一佛與千佛同悟的內容。例如,《法華經·方便品》中強調,世尊說法與諸佛說法完全屬相同內容等,也是以上“一即多,多即一”義理的表現[8]。首先必須依此義理為信念觀察千佛、諸佛的造型。大乘佛教的造型,無論哪個造型思想背景都有“一即多,多即一”的義理,當然莫高窟南北朝至隋唐造型的思想中也潛在著這種傳統。
莫高窟北朝時期千佛像分別坐蓮花座,蓮花座的出現,已經有了凈土“場”的意味。然而,像北魏窟人字披天井下畫蓮池中表現一佛二菩薩像等,應表現了“諸佛中的一佛凈土”(圖版1)。這種表現與后來初唐盛行的凈土表現之關聯,東山健吾先生已有指出[9]。作為造型表現,只要有蓮池就可稱作“諸佛中的一佛凈土”,然而,譯經史上鳩摩羅什譯的“凈土”就有“諸佛凈土”之意[10,11],這與莫高窟北朝時期的大部分凈土,表現何佛之凈土的狀況一致。即使不能確定北朝時期所畫凈土為表現何佛之凈土,只要按如前所述的大乘佛教解釋,以“諸佛,諸佛凈土”莊嚴空間,作為“表示布滿三千世界的諸佛之存在”也相當重要。
中國佛教之特征可舉“本跡思想”。“本跡”一詞,出自中國的教相判釋,由來于《法華經》的教說,“絕對真實之佛=本地”,作為“具體的形態=跡”,現身于此世——再具體說,就是人之釋迦作為所謂的垂跡身現于此世——這才是原意。當轉變為諸佛、諸菩薩為救度眾生時,依不同的風土、社會而現身,或稱作其顯現的身形。本跡思想之始,可追溯到羅什諸弟子③。
大乘佛教之重要概念,有將佛之教誨為體的“法身”,也就是“絕對真實的佛”。由此作為垂跡身,顯現了具體身形的是人之釋迦。作為北朝時期莫高窟明顯的例證,可舉佛傳圖或中心柱龕的苦行像。
“本跡思想”又可作為波及隋唐造型思想背景之傳統,與“諸佛”概念同時例舉。
眾所周知,莫高窟北朝晚期,本生圖、因緣圖似乎被搬到天井,到了隋代,開始出現繪制簡單的藥師經變、阿彌陀凈土變這種經變畫。當然這里也活躍著“一即多,多即一”的“諸佛”概念。如繪于第393窟正壁的阿彌陀西方凈土變(圖1),雖然在本圖的阿彌陀佛周圍繪4組一佛二菩薩像,但每個佛像的成道樹形迥異,據此推想表現了不同尊格的諸佛。《觀無量壽經》第四觀樹觀“由寶樹的果實化成的寶蓋中,映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國亦于中現”[12],第八觀像觀“在觀想的阿彌陀、觀音、勢至空間遍滿一佛二菩薩像”[12]54-55,第九觀正觀“見無量壽佛身相與光明者,即見十方一切諸佛,作是觀者,名觀一切佛身”[12]56。
這就是“一即多,多即一”的“諸佛”概念之效應、造型所見的現象。
作為隋末唐初具有特征的壁畫,有繪于第390窟、第244窟四壁的一佛二菩薩像,一佛二比丘二菩薩像的樹下說法圖群像(圖版2)。這些圖像中如來像大衣的色、形、成道樹有所變化,可以認為分別表現不同的佛陀,每個臺座下有蓮花,表現各佛的凈土。可以說這是表現極其簡單的“諸佛凈土”。
正如隋代第276窟、第394窟左右壁所見,似乎隋代開始利用正壁放大描繪一佛二比丘二菩薩像。然而,在莫高窟的壁畫形式上,或在思想史上,亦有革新變故的,應是眾所周知的有唐貞觀十六年(642)墨書題記的第220窟南壁阿彌陀凈土變的出現。作為壁畫,在西方三圣像周圍,華麗地描繪出宏偉而壯觀的樓閣、寶池、往生的化生童子像、歌舞、樂器演奏等場景,這在莫高窟也是前所未有的情景。一直以來人們認為,大畫面表現西方阿彌陀凈土變這種美術史上新的形式,是受來自都城的直接影響。又在思想史上,以往也有高僧將“凈土”領會為“諸佛凈土”,并沒有特別視為只是阿彌陀凈土[10,11]。大西磨希子提出,道綽強調應該以只往生西方凈土為目標的影響也波及第220窟[13]。
的確敦煌莫高窟初盛唐時期有許多西方凈土變,看來道綽、善導倡導的凈土教傳入敦煌是確鑿的事實。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被視為每個窟主尊的正壁中的尊像,在初唐50個窟中,釋迦系統的像約占60%,阿彌陀凈土變、彌勒凈土變繪于左右側壁,這點筆者已在2004年敦煌召開的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有所指出①。
首先,莫高窟初唐時期窟中所見明顯的現象,正壁壁畫加塑像“十大弟子像15例”,“表現在假設為虛空處的見寶塔品中的二佛并坐像7例(加上正壁以外的為11例)”,還有許多“十大弟子像”、“見寶塔品中的二佛并坐像”。十大弟子像圍繞的佛像,可考慮為人身之釋迦的形象,在緣自《法華經·見寶塔品》周圍的佛像,使人想起常住法身垂跡的釋迦。這說明前述北朝期莫高窟所見的本跡思想,作為一種傳統根深蒂固于莫高窟。初唐時期的莫高窟,是法身垂跡之身,也是應身的釋迦作為許多石窟的主尊而出現②。
表現在莫高窟初唐窟側壁的20例①阿彌陀凈土變中的阿彌陀佛,也是由法身顯現出的報身或應身,是諸佛中之一佛。“法身”指佛本身的法,是無形的。“應身”是佛為救濟眾生,顯現出適應對方的形姿,這樣的佛之身體。“法身”即使永遠不滅,也缺乏人格性、具體性,“應身”富有人格性、具體性,但是一時的、無常的東西。由此想出的是兼備了法身之永遠性與應身之具體性的“報身”[14]。隋唐高僧之間盛行如何定義佛之身的爭論,不過,主要高僧間一致的見解是“雖然佛有法身、應身、報身三身,但三身覺悟的內容相同,即三身同證”,“佛之教源相同”②。
這種觀念第332窟出土的武周圣歷元年(698)銘的《武周圣歷李君莫高窟佛龕碑》上也有明顯的記載。
①原文第3行、第4行“一乘絕有為而□無為獨尊三界若乃非相示相揔權實以運慈悲非身是身苞真應而開方便”。②第7行“異派同源是知法有千門咸歸一性”。③碑背面第11行“法身常住佛性難原形包化應跡顯真權”③。應該認識阿彌陀的存在原來也是出自“永遠性的釋迦形象”之假設。
莫高窟壁畫觀經變中韋提希夫人從十方諸佛中參拜阿彌陀凈土,也可說明阿彌陀為“諸佛中之一佛”④。
這種認識的普遍存在,在初唐永徽元年(650)刻于龍門石窟的阿彌陀像龕的造像記上也可窺見一斑。清信女劉氏做夢愿造千佛像,睡醒后擔心千佛像日后磨滅,便造阿彌陀像,實現了夢中之愿。劉氏將千佛變更為阿彌陀像,所認可的理由,可舉經典中的語句“佛一身為多,多身為一”。劉氏大概從僧侶受教了前述《法華經》、《觀無量壽經》的內容。這說明初唐的信徒具有“千佛與阿彌陀佛力相同”的概念⑤。
再來分析初唐的凈土觀。以往初唐造像記等處所見“凈土”一語,全都含混解釋為只指西方凈土。在考察西方凈土觀時,應參考柴田泰先生的《中國佛教史上有關凈土翻譯語的研究》[10]。主要從事凈土教研究的柴田泰先生,對中國漢譯佛教經典中漢魏以后至唐末、宋代的“凈土”用語作過調查,其見解如下。首先介紹佛教學家平川彰先生的研究成果,“凈土”一詞的翻譯始于5世紀的鳩摩羅什,但是,羅什將凈土一詞作為“諸佛凈土”使用。被稱作凈土教祖師的僧侶——曇鸞、道綽、善導把“凈土”一視同仁為“阿彌陀佛凈土”。在他們活躍的六七世紀整個中國佛教界來看,對“凈土”的這個解釋很特別。玄奘(602—664)漢譯了同時期的《陀羅尼集經》的阿地瞿多,約50年后的義凈、菩提流志等,當時都并記、混合為“西方凈土”、“凈土(諸佛凈土)”、“十方凈土”,這個時代“凈土”尚未特定為“阿彌陀凈土”。“凈土”明確地譯為“阿彌陀佛凈土”始于746年在長安漢譯了中期密教經典的不空,在譯經史上,“凈土”專指“阿彌陀佛凈土”已到了唐末。看來七八世紀前半中國的經典漢譯者,并未將“凈土”一詞限定用于“西方阿彌陀凈土”。
這種凈土觀在有初唐造像的唐代龍門石窟也是相同的。龍門西山第1896窟的造像明顯出自于《觀經》。該窟北市彩帛行凈土堂后室里壁刻“佛國混同”語句。由此可知,在想要將阿彌陀凈土造型化的信徒腦海里,也認識到了阿彌陀凈土為“諸佛凈土中之一”[15]。
以往中國美術研究者抱有這樣的成見,提到初唐美術的背景思想,在莫高窟就被華麗的西方凈土變所吸引,只有道綽、善導主導的凈土教昌盛;說到初唐的“凈土”、“凈土變”,就只指阿彌陀的西方凈土。實際上莫高窟初唐時期各窟的主尊“法身垂跡的釋迦性格”強勢,而阿彌陀的西方凈土變被描繪于側壁。石窟內的構成意圖是對“釋迦佛”在王舍城的耆阇崛山說的“作為報身、應身的阿彌陀佛、彌勒佛”的認知[12]39。對阿彌陀佛的這種領悟法,早在1941年的《龍門石窟研究》中塚本善隆先生就指出“唐代普遍信仰的阿彌陀、地藏都是作為釋迦佛說法顯現的諸神,被中國佛教徒所吸收”[16]。看來我們始終不忘記初唐莫高窟的信仰中心是“釋迦、釋迦之教為體的法身”。
二
筆者最近對7世紀中到8世紀中盛行造像活動的唐代龍門石窟作過研究。注意到同樣為初唐佛教石窟,其表現的主題相差甚遠。如本稿第一部所述,在初唐的敦煌莫高窟多表現緣于《法華經·見寶塔品》的二佛并坐像、經變以及十大弟子像。可是,在唐代的龍門石窟,出自《法華經·見寶塔品》的二佛并坐像,除藥方洞內側前壁門口上方,可推論為是初唐之作外,再看不到引人注目的初唐二佛并坐像例[15]181-183。雖然龍門整體表現諸佛凈土[15]201-204,但是,像莫高窟那種表現伴隨有往生者的西方凈土變,能夠斷定的只有3例,而經變類幾乎不見①。再就是唐代龍門造像記中有許多愿往生垂跡的釋迦佛的記載,但幾乎沒有十大弟子像。而龍門卻有許多老年相、年輕相的比丘像,其中附有佛弟子“迦葉、阿難”尊名的像,只限于唐代龍門中的2例②。唐代龍門幾乎是略微類型化的一佛二比丘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造像。另外,唐代龍門石窟中,680年以后的近600例如來坐像幾乎都為觸地印,其中觸地印的阿彌陀像也有52例[15]310-311。然而,莫高窟明顯的觸地印阿彌陀像只有第335窟南壁阿彌陀凈土變中的主尊阿彌陀佛像1例[17]。
由此可知,同為初唐時期的佛教石窟,敦煌莫高窟與龍門石窟在圖像表現上有相當差異。筆者全面解讀、研究唐代龍門石窟所有造像記的結論:“本跡思想”、“諸佛存在的大小”、“一即多,多即一”、“阿彌陀也為諸佛中之一的概念”,《法華經》、《觀無量壽經》、《涅槃經》、《彌勒下生經》、《華嚴經》等,在造型思想背景上所潛在的觀念、意識上沒有什么變化。
那么,莫高窟與龍門石窟的圖像異同出自何處?筆者認為其原因在于“造型場所的功能、作用”之不同。
莫高窟的功能、作用已有諸多研究,最近出版了有關北區的極其詳細的報告,在初盛唐時期北區明顯存在禪窟、僧房窟、瘞窟等[18]。
對于南區經變的功能,李永寧、蔡偉堂、巫鴻等先生發表過見解,主要對晚唐勞度叉斗圣變與變文的關系作了論考,其結論認為,在畫有經變的后室(主室)前,有開窟時造的前室,大概由于窟中光線暗,難以開展邊圖解邊俗講、講經的活動,為了莊嚴、奉獻經變等,就將其繪于壁面[19,20]。筆者也贊同此種觀點。
最近,有學者對南區西魏第285窟作為禪定修行之場所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指出此窟作為修行場所裝飾過于華麗,有礙于修行者的潛心禪修,在觀佛經典中記載,先在心中確立佛像的意念,之后退至靜處繼續觀想。北區確認出很多禪窟,是對此種觀點的有力支持[21-23]。對于南區壁畫的作用,即使繪了許多作為觀經變這樣的壁畫,其目的是否作為修行時的觀想對象而繪,尚存疑問。
因此,在考慮初盛唐時期莫高窟南區功能時,值得注意的是“家窟”之存在。關于“家窟”,馬德先生等有過論證[24],有名的是第285窟、第220窟墨書題記中的陰家窟、翟家窟、第332窟《武周圣歷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出現的李家窟等。其中李家碑“碑背面第2行:每年盛夏奉謁尊容就窟設齋燔香作禮”,可知由于參拜石窟為每年盛夏,所以參訪石窟只限于舉行儀式那幾天。如果作為世代相傳的家族窟保護,只限于儀式日子才使用的話,完全可以理解莫高窟南區各窟遺留至今的完美狀態。雖說莫高窟南區,初期營造的石窟極有可能用于禪觀修行[25],但初唐時莫高窟南區的功能有可能用于限定的儀式等。隋代第276窟盡管沒有表現樓閣等,但是以大畫面形式表現如來、比丘、菩薩像的初期石窟。其正壁龕外左右壁繪較大型的維摩、文殊立像,維摩像左側有與行香相關的土紅色的題記,與敦煌文書等所見的“行香禮懺儀式上的唱偈文”相近,也有觀點認為該窟用作禮拜儀式(圖版3)①。
提到莫高窟南區的功能,就想起造在初唐南區石窟正壁的出自于“見寶塔品”的“二佛并坐像”與“十大弟子”像。如前所述,供奉于石窟正壁龕的主尊像多為“法身垂跡的釋迦”。而且有一點值得注意,正壁龕內的主尊如來坐像多表現說法印,對參拜石窟者營造出說法空間。
總之,莫高窟南區有初唐經變的石窟,是各個有財力的家族為了莊嚴佛之空間所營造,之后由這些家族世代后人每年舉行數次參拜儀式等所用。因為利用莫高窟南區的是生者,所以,在進入每個窟時,參拜者可能有蒞臨儀式感,以視覺性的真實感禮拜法身垂跡的釋迦所說阿彌陀、彌勒世界、十方諸佛。
另外,若結合造像記觀察以初盛唐時期為中心開鑿了許多佛龕的整個唐代龍門石窟,就明確了那里“也稱作洛陽郊外,是顯示以賓陽南洞像、奉先寺洞像等為代表的世俗王權之威信的場所”,“通過造像求功德之場所”,“不論僧侶、俗人均可造瘞窟之場所”,“愿往生包括西方凈土的諸佛凈土、忉利天、兜率天的亡者來世安寧之場所”。
唐代龍門造像記中,大多為“祈禱亡者有更好來世的愿文”,不過,對瘞窟多,作為亡者長眠之地的龍門充滿強烈的向往這一點也值得特書。
首先,舉瘞窟之例,包括敬善寺洞南側第440窟的瘞窟群。在殘留有所謂優填王像痕跡的高145厘米、寬143厘米、進深92厘米的龕門口甬道南壁刻有文林郎(從九品上)沈裒按尸陀林法禮將亡妻葬于本龕的題記。以下引用該題記有關葬送部分。“顯慶五年(660)十二月寢疾于思慕之第而謂曩曰笄冠之初契期偕老豈意非福痼瘵纏躬不諱之后愿從所志其月廿八日薨于內室遂延僧請佛庭建法壇設供陳香累七不絕筮辰卜日休兆葉從寶幡香車送歸伊嶺尸陳戢崖魂藏孤巖實日尸陀林法禮。”②顯慶五年(660)十二月,久病的妻子在家去世,大概是按夫婦以前的愿望,12月28日亡后,招僧人到家,在庭院設法壇,行供養儀式焚香,這種儀式連續7天不斷,后經占卜選定日子,將遺體放置裝飾車運出。然后按尸陀林法禮陳尸于崖,亡妻靈魂收藏于巖(龍門山)。第440窟左右并列著同規模、同形式的龕,從第437龕到第442龕。由題記推測,當時各龕均收藏有尸體(圖版4)。尸陀林法禮是古代印度的一種葬法,按古代印度的風俗,將尸拋出任禽獸食之,尸陀林為印度王舍城附近的Slta-vana的漢譯語。從此題記分析,妻子去世之前就希望死后將尸體原封不動葬于龍門山,據此可知,龍門山是“收納亡者之魂的特別場所”。
再舉相同一例③。賓陽南洞內貞觀二十二年(648)的阿彌陀二菩薩像龕,是依照亡子生前夙愿造像,愿亡后往生無量壽國。據記載該亡子安葬于龍門東山。饒有趣味的是,可能造像主——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徒,連孩子都將龍門指定為自己死后完成往生凈土的通過之地。另外,關于龍門為僧人、俗人瘞窟的報道有許多①。
在唐代龍門石窟可見許多“愿亡者菩提的造像”宗旨的題記,由此可知龍門之地的重要性,應是讓死者靈魂升天、往生凈土②的場所。盡管莫高窟北區也為瘞窟,但是僅從發掘報告來看,好像幾乎沒有佛像,位置也限制在北區。唐代龍門也有只收納骨灰,沒有佛像的葬灰瘞窟,也有葬灰瘞窟殘留佛像痕跡的。總之,唐代龍門有在瘞窟造佛像的可能,因為,為了亡者升天、往生凈土之際,有“似乎看見佛”的意念。
在記載龍門石窟貞觀十五年(641)造賓陽南洞像的《伊闕佛龕之碑》中,記有造像主魏王李泰愿亡母文德皇后升天、往生凈土一事。
原文21—22行:“思欲弭節鷲岳申陟屺之悲鼓龍池寄寒泉之思方愿舍白亭而遐舉瑩明珠于兜率度黃陵而撫運蔭寶樹于安養博求恩之津歷選集靈之域。”也就是說,因魏王李泰造像愿亡母升天、往生凈土,稱龍門為所選的“集靈之域”③。由此,可知當時人們認為龍門是亡者靈魂聚集地,是亡者靈魂安然無恙升天、往生凈土之場所。
唐代龍門石窟,祈禱亡者菩提造像后,生者再不可能定期往來于龍門,在石窟內、龕內舉行儀式。其證據就是現在不易攀登進入的龕內處開鑿著許多窟龕。與其說這些是生者造訪禮拜佛像,不如看作是后人為了亡者,在“龍門之地”造窟龕更有價值。若在龍門崖造了窟龕佛像,就沒必要直接進入那個窟龕,只是在窟龕造像當時,于下邊舉行一定的儀式即可。
如此看來,莫高窟南區與龍門石窟,同為有初唐造像的佛教寺院,由于其功能、作用迥異,即使蘊藏的思想相近,造像主題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差異。
莫高窟南區石窟,可能是“生者”每年來訪數次中,在依據法身垂跡的釋迦之法展開的阿彌陀經變、彌勒經變前舉行儀式之場所。
龍門石窟大概在魏王李泰營造的賓陽南洞像和高宗、武則天造的奉先寺洞像等完工時,舉行了顯示世俗王權之權威的盛大儀式。而通常在龍門開鑿瘞窟,為了亡者舉行一時的吊唁儀式,或開龕造像,舉行儀式愿亡者升天、往生凈土,之后就成了寂靜之地。雖然認為周圍建佛教寺院,天天有僧人活動,但是,龍門之地的性質之一,就是讓亡者之魂平安升天、往生凈土的特別場所。
今后,我將從歷史上、文化史上,研究、探索龍門為何作為這樣的場所,被皇帝、僧人、庶民所接受的。
參考文獻:
[1]頼富本宏.密教仏の研究[M].東京:法蔵館,1990:65.
[2]賀世哲.敦煌圖像研究——十六國北朝卷[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6:112-113.
[3]平岡聡.シリズ大乗仏教:第二巻(大乗仏教の誕生)[M].東京:春秋社,2011:126-127.
[4]寧強,胡同慶.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千佛畫研究[J].敦煌研究,1986(4).
[5]賀世哲.關于北朝石窟千佛圖像諸問題[J].敦煌研究,1989(3、4).
[6]劉永増.“千佛圍繞式說法圖”與《觀佛三昧海經》[J].敦煌研究,1998(1).
[7]久野美樹.造像背景としての生天、託生西方願望——中國南北朝期を中心として——[J].佛教藝術(187),1989:表1.
[8]鎌田茂雄.華厳の思想[M].東京:講談社學術文庫,1988:147.
[9]東山健吾.敦煌莫高窟における佛樹下說法図形式の受容とその展開[C]//成城大學文藝學部創立三十五周年紀念論文集.成城大學文藝學部.1989:215.
[10]柴田泰.訳語としての浄彌陀仏の“浄土”[J].印度哲學佛教學(7),1992.
[11]柴田泰.中國仏教における“浄土”の用語再說[J].印度哲學仏教學(9),1994.
[12]觀無量壽經凈土三部經:下[M].東京:巖波書店,1964:48.
[13]大西磨希子.西方浄土変の研究[M].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07:63-94.
[14]中村元.佛教語大辭典:下卷[M].東京:東京書籍,1975:1242.
[15]久野美樹.唐代龍門石窟の研究——造形の思想的背景について——[M].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1:101.
[16]塚本善隆.龍門石窟に現れたる北魏佛教[C]//龍門石窟の研究.座右寶刊行會,1941:155.
[17]敦煌石窟藝術:第321、329、335窟(初唐)[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6:圖170.
[18]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1—3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004.
[19]李永寧,蔡偉堂.《降魔変文》與敦煌壁畫中的勞度叉斗圣變[C]//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經變篇.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350頁-351.
[20]巫鴻.禮儀中的美術: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364.
[21]趙聲良.敦煌北朝石窟形制諸問題[J].敦煌研究(99),2006.
[22]沖本克己.敦煌莫高窟北區之課題[C]//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3]山部能宜.新アジア仏教史05 中央アジア文明·文化の交差點[M].佼成出版社,2010:313-315.
[24]馬徳.敦煌莫高窟史研究[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6.
[25]濱田瑞美.新アジア仏教史05中央アジア文明·文化の交差點[M].374-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