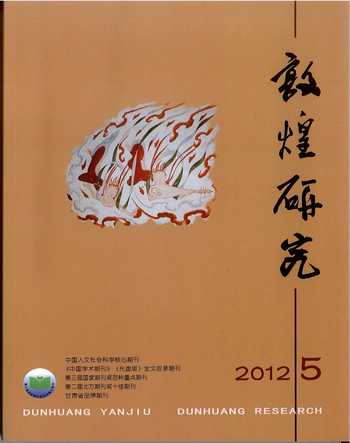敦煌變文詞尾“即”考辨
劉傳鴻
內容摘要:有學者認為敦煌變文中“遂即、便即、乃即、雖即、或即、忽即、實即”七個組合,“即”為詞尾。然而綜合比較“即”的固有功能與上述組合在文獻中的用法,結合與之相關的其他組合的類比分析,我們認為:“即”在上述組合中主要發揮了其副詞和連詞的連接和強調功能,并非用以湊足音節的詞尾。
關鍵詞:敦煌變文;即;非詞尾
中圖分類號:G256.1;H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2)05-0104-09
蔣宗許先生指出:敦煌變文中“即”有一種特殊用法,它常常附著于虛詞之后,湊足雙音節,不再具有詞匯意義,其特點跟詞尾“自”和“復”大略相同。蔣先生在文中列舉了“遂即、便即、乃即、雖即、或即、忽即、實即”七個組合,并進行了分析論證[1]。2009年,他在《漢語詞綴研究》一書中重新闡述了這種觀點[2],并以“即”為例探討詞綴的確定方法[2]60。
筆者仔細研讀了蔣先生的文章,并考察了敦煌變文及其他文獻中“即”的用法,認為:“即”在各組合中使用了其作為副詞、連詞的固有功能,而非附加于副詞或連詞之后充當詞尾;以確定“即”為詞尾的方法確定其他詞綴,將會帶來諸多問題。以下我們根據各組合中“即”的功能并結合蔣文的論證試加分析。
一 “即”用于連接前后相承的兩件事,
“遂即、便即、乃即、忽即”屬于此類
“即”用以連接前后相承的兩件事,相當于便、就,為其常義,《漢書·高帝紀上》:“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3]《后漢書·任延傳》:“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4]“遂”、“便”、“乃”在這一義項上與“即”同義,如《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5]288《莊子·達生》“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者也”,劉淇《助字辨略》卷4引此文曰:“便,即也。”[6]《史記·項羽本紀》:“度我至軍中,公乃入。”[7]
變文中這樣的用法亦非常多,此各舉其一:《伍子胥變文》:“王聞魏陵之語,喜不自升(勝),即納秦女為妃,在內不朝三日。”①[8]《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王見聰惠,博達多心,遂封賞一邑,充為捧(俸)祿。”[8]669《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懺悔已了,此(次)受三歸,后持五戒,便得行愿相扶,福智圓滿,將求佛果,永曉輪回。”[8]681《維摩詰經講經文》:“臨辭華弟,乃命家童,捧數合之香花,擎幾般之幡蓋。”[8]864
“遂即”、“便即”、“乃即”三詞正是表此功能的“遂、便、乃”與“即”組合而成的同義復合結構。
遂即*② 蔣文舉有六個用例,此舉其一,《伍子胥變文》:“龍蛇塞路,拔劍蕩前;虎狼滿道,遂即張弦。”他同時指出:“先秦兩漢,未見類似的‘遂后綴有‘即字者,六朝也似沒有。”[1]81
考同義的“遂即”組合,早有用例,《三國志·魏書·劉曄傳》裴松之注引《傅子》:“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9]之后用例更多,如《水經注》卷2:“有頃,水泉奔出,眾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即引去。”[10]《舊唐書·程知節傳》:“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11]2504《警世通言》卷24:“王定遂即鎖了房門,分付主人家用心看著生口。”[12]
文獻中還有意義完全相同的倒序詞“即遂”,且在漢代即已出現:《漢書·匈奴傳下》:“聞漢出兵谷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3]3800其他文獻亦有眾多用例,梁寶唱《經律異相》卷31:“祇域白太后:‘王病可治,今當合藥太后即遂遣青衣黃門出。”[13]《太平廣記》卷387:“俗緣未盡,但愿勤修,勤修不墮,即遂相見。”[14]
“即遂”的用例比“遂即”要少,特別在宋代之后很少使用,這是因為“遂即”這一詞形更符合復音詞語素排列的調序原則[15]。
蔣先生認為:“遂即”組合中“即”顯得多余,若“遂即”理解成“副詞連用,則拖泥帶水,不倫不類”[1]81。我們不同意這種說法:“遂”、“即”用于連接前后相承的兩件事,意義及功能完全相同,復合成“遂即”、“即遂”,與單用“遂”、“即”并無不同,故而不存在多余之說。事實上,“遂”、“即”、“乃”、“便”均可兩兩復合,且大多數在變文中有其用例。詳見下文。
便即* 蔣文舉有六例,此舉其二:《燕子賦》:“見他宅舍鮮凈,便即兀自占著。”《葉凈能詩》:“凈能一見慕之,便即留意……長年廿,便入道門。”針對上述兩例,他分析說:“‘兀自的‘自是詞尾,‘兀自猶‘兀然,‘便即與‘兀自駢列同型,‘即亦是詞尾。”“‘便即與‘便對用,‘即為詞尾尤明。”[1]82
其實,《燕子賦》中“便即”與“兀自”功能完全不同,“兀自”用以修飾動詞“占”,相當于公然;而“便即”則起連接作用,表后一事緊接前一事發生,二詞雖然相連,但并非駢列,由“自”作詞尾推斷“即”亦為詞尾難以成立。《葉凈能詩》中“便即留意”與“便入道門”結構相似,或可得出“便即”與“便”同義,怎能得出“即”為詞尾的結論呢?
同義的“便即”早在魏晉時即已產生并沿用,且用例極多,《后漢書·魯恭傳》:“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4]882《南史·賀琛傳》:“累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16]《西游記》70回:“妖王大笑,陪禮道:‘娘娘怪得是,怪得是!寶貝在此,今日就當付你收之。便即揭衣取寶。”[17]
其同義倒序詞“即便”亦有極多用例,變文中即有數十例,此舉其一:《八相變》:“大王見說上事,即便歸宮,處分彩女頻(嬪)妃,伴換太子,恒在左右,不離終朝。”[8]510它在魏晉時即已產生并沿用,《后漢書·王堂傳》:“后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4]1106《抱樸子·內篇》卷4:“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18]《西游記》65回:“三藏聞言即便下拜,八戒也磕頭,沙僧也跪倒,惟大圣牽馬收拾行李在后。”[17]873
蔣文在列舉“便即”用例后指出:“上例之‘即,均可略去,略去后不僅意義無別,而且更覺簡練(按通常理解)。我們以為這些“即”都是詞尾。”[1]82
誠然,“便即”中“即”可以略去,且意義無別。不過,“便即”中“便”同樣可以略去,意義也不會改變,而其倒序詞“即便”同樣如此。究其原因,“便”與“即”本為同義詞,組合構成同義復合詞,其功能與單用“便”、“即”并無不同,至于使用哪一個,主要取決于字句和諧的需要。
乃即* 蔣文舉有兩例,此舉其一:《燕子賦》:“知他窠窟好,乃即橫來侵。”[1]83
同義的“乃即”早在魏晉時即已產生并沿用,但用例不多:《三國志·魏書·趙儼傳》:“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9]669-670《敦煌變文校注·燕子賦》:“知他窠窟好,乃即橫來侵。”[8]413《石點頭》第9回:“韋皋乃即開門,先請蘇玉入城,受其詔書。”[19]
其同義倒序詞“即乃”在變文中亦有用例,《張義潮變文》:“仆射聞吐渾王反亂,即乃點兵,鏨兇門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進軍。”[8]180它在梁代即已出現并沿用,如梁寶唱《經律異相》卷40:“到王所言:‘今來對義。即乃說偈。”[13]607《太平廣記》卷453:“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之事,期方賒緩,即乃典貼舊業田園,卜居近坊,為生生之計。”[14]3699《兩晉秘史》309回:“是日恰好使者至,說劉裕有召,即乃馳還京師,入見劉裕。”[20]760
文獻中除了“即”與“遂、便、乃”可組合成詞之外,“遂、便、乃”之間也可兩兩復合成詞,其中“便乃、乃便、遂乃、遂便”在變文中都有用例,此各舉其一:
便乃 《太子成道經》:“太子聞知,亦加不悅,便乃還宮。”[8]438
乃便 《董永變文》:“慈耶得患先身故,后乃便至阿娘亡。”[8]174
遂乃 《目連緣起》:“一自娘娘崩背,思量無事報恩,遂乃投佛出家,獲得神通羅漢。”[8]1013
遂便 《廬山遠公話》:“白莊聞語,然而信之,遂便散卻手下徒黨。”[8]257
“乃遂、便遂”在其他文獻中有用例,此各舉其一:
乃遂 《史記·齊太公世家》:“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7]1484
便遂 梁寶唱《經律異相》卷29:“母言:‘汝實是鬼也,我懷汝時,夜夢見鬼,與我共會,便有汝耳。王便遂寤,改不殺人。”[13]479
有時甚至還有三字連言者,如:
遂乃便 唐義靜《成唯識寶生論》卷2:“有說由心惑亂,遂乃便生時處定解。”[21]①
遂即便 唐不空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卷5:“聞此教已,遂即便發無上正等菩提之心。”[22]
便乃即 宋曇秀輯《人天寶鑒》:“若能一念回光,便乃即同諸圣。”[23]
“遂、便、乃、即”單用連接前后相承的兩件事,意義及功能完全相同;兩兩之間構成“遂即、即遂、便即、即便、乃即、即乃、便乃、乃便、遂乃、乃遂、遂便、便遂”等6組12個具有倒序關系的組合,意義及功能與單用時別無二致;再加上一些同義的三字連言組合的存在,無不說明,“遂即、便即、乃即”以及上舉其他組合是毫無疑義的同義復合。
蔣文所舉“忽即”中的“即”亦用于連接前后相承的兩件事。
忽即* 蔣文舉有四例表忽然義的“忽即”[1]83,其中兩例理解有誤:《廬山遠公話》:“二足者,人生在世,有身智浮名為二足,忽即有口(身)而無知(智),忽即有智而無身。”此例中的“忽”通“或”,“忽即”即“或即”,用以列舉(參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卷2及下文“或即*”一詞的分析[8]263)。另外兩例如下:
《伍子胥變文》:“子胥祭了,發聲大哭,感得日月無光,江河混沸。忽即云昏霧暗,地動山摧。”《搜神記》:“乃送食來,語其夫曰:‘有何異事?忽即發被看之,乃有一胡人床上而臥。”[1]83
“忽即”連用,佛典中有較多用例,晉竺法護譯《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下:“身中出火,還耶維已,而般泥洹,忽即霍滅,無有煙炭。”[24]隋阇那崛多譯《起世經》卷8:“起此念時,其身五系,即還縛之,五欲功德,忽即散滅。”[25]唐道世《法苑珠林》卷18:“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贊言……”[22]相對來說,中土文獻用例較少,宋張君房《云笈七簽》卷120:“母死月余,獻亦暴死。三日心暖,家人不敢便葬,忽即起活。”[23]
仔細體會上述各例,“即”的前后文仍為前后相承的兩件事,使用“忽”只是強調后一件事發生的迅疾和突然。以上舉《起世經》為例,句中“其身五系,即還縛之”與“五欲功德,忽即散滅”均承“起此念”而言,強調二事緊承發生,“其身五系,即還縛之”中的“即”正是這一功能的體現。同樣,“五欲功德,忽即散滅”中的“即”仍表此功能,我們不能因為有了“忽”的存在,就將它看作詞尾,事實上,去掉“忽”之后,如果不考慮字數不協,“五欲功德,即散滅”完全成立。
不僅“即”可如此用,與“即”同義的“便”、“乃”也可與“忽”構成用法相同的組合:
忽便用例很多,西晉竺法護譯《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卷1:“時阿耨達并余龍王及諸眷屬,自乘神力,踴升虛空,興香之云,忽便普布。”[28]《晉書·甘卓傳》:“卓性先寬和,忽便強塞,徑還襄陽,”[29]1865《太平廣記》卷133:“鄰有張生者,亦以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14]947此例“忽便起坐”與上舉《云笈七簽》中“忽即起活”相類,亦可證“忽即”與“忽便”實同。
忽乃用例較少,《太平廣記》卷369:“其后半歲,累獲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復逸,逐之,忽乃入糞土中。”[14]2933《太平廣記》卷437:“言訖,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覓。”[14]3560
“即、便、乃”可用于連接前后相承的兩件事,而上舉組合所處語境均屬此類。雖然在翻譯時,“忽即、忽便、忽乃”可以用“忽然”對譯,但這并不能說明“即、便、乃”的連接功能不復存在,事實上,“即、便、乃”單用連接前后相承的兩件事,也不是非譯不可。另外,上舉各用例去掉“即、便、乃”前的“忽”,如果不考慮字句和諧,完全可以成立,只是不能體現事情發生的突然性罷了。基于此,我們認為,“忽即”組合中“即”的連接功能并未消失,它并非僅用以湊足音節的詞尾。
二 用于連接具有轉折或平列關系
的句子,“雖即”、“或即”屬于此類
“即”除了作副詞,連接前后相承的兩件事之外,還可用作連詞,表多種句式關系。蔣文所舉“雖即”中“即”表轉折;“或即”中“即”表平列,用于情況的列舉。
雖即* 蔣文舉三個用例,此舉其一:《維摩詰經講經文》:“雖即壽年長遠,還無究竟之多;雖然富貴驕奢,豈有堅牢之處?”蔣先生分析說:“以上‘雖即都是‘雖然的意思,均可以‘雖然置換,例(15)[即上舉《維摩詰經講經文》例]更是昭然豁然。”[1]82
誠然,變文中“雖即”均可解作“雖然”,而《維摩詰經講經文》中的對應更說明“雖即”與“雖然”同義,但這并不能說明“雖即”之“即”等同于“然”而為詞尾。
事實上談及“雖即”,我們不能忽視另一個詞“雖則”,它同樣表雖然,且用例更早更多,如《尚書·秦誓》:“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發,則罔所愆。”[30]《后漢書·馮衍傳》:“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4]968《舊唐書·虞世南傳》卷1:“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系囚,庶幾或當天意。”[11]2566變文中亦有用例,《目連變文》:“天地路殊,久隔互不相見。雖則日夜思憶,無力救他。”[8]1072《王昭君變文》:“此間雖則人行義,彼處多應禮不殊。”[8]159
我們知道,“即”與“則”音近義通,常可通用,關于這一點,發之者甚多,如《諸子評議·墨子一》“即舉其事速成矣”,俞樾按:“即、則古通用也。”[31]《漢書·韓安國傳》“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劉淇《助字辨略》卷5引此文曰:“此即字,猶則也。”[6]275《經詞衍釋》卷8:“即,則也,古同聲而通用……《項羽紀》:‘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即、則對文,即實則義。”[32]
變文中“即”與“則”的使用亦能體現這一點,《太子成道經》:“大臣云:‘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8]437同記此事的《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作:“忽有大臣奏云:‘主憂即臣辱,不如臣則死。”[8]470《太子成道經》:“遂遣車匿問之,‘則君一人如此,諸余亦然?”[8]438下文近似的句式作:“即此一個人死,諸人亦然?”[8]43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憂則共戚,樂即同歡。”[8]972《維摩詰經講經文》:“視慈云則普垓三界,施利濟即廣度四生。”[8]759此兩例“則”、“即”對文同義。《雙恩記》:“太子曰:‘然即如此,不敢違王。欲擬上聞,請乞一愿。”[8]930“然即”即“然則”,這種用法在早期文獻中即可見到,漢王充《論衡》卷14:“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黃暉校釋:“‘然即猶‘然則也。”劉盼遂案:“‘即與‘則通,‘然即亦‘然則也。”[33]
另外,我們對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中的“即”與“則”用例作了統計[34],發現“即”有998個用例,而“則”僅140個用例。用例如此懸殊,可能與變文所用方言習慣使用“即”有關。
基于“即”與“則”的密切關系,以及“雖即”與“雖則”用法意義完全相同,我們認為,“雖即”組合中,“即”與“則”相當,“雖即”即“雖則”。那么“即”與“則”在“雖即”、“雖則”組合中是何種性質呢?
考連詞“則”,很早即可單用表轉折,如《呂氏春秋·任地》:“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35]《三國志·魏書·杜夔傳》裴松之注引傅玄序曰:“巧則巧矣,非盡善也。”[9]807變文中亦有用例,如《唐太宗入冥記》:“催子□□(玉答)曰:‘得則得,在事實校難。”[8]320作為與“則”通用“即”,也有表轉折的用法,變文中即有多例,此舉其二,《廬山遠公話》:“善慶口即不言,心里思量……”[8]261《太子成道經》:“殿下位即尊高,病相亦皆如是。”[8]438他例如《唐律疏議》卷11:“諸有所請求者,笞五十謂從主司求曲法之事。即為人請者,與自請同。”[36]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3:“瘦即瘦,比舊時越模樣兒好否?”[37]此例與上舉《馬先生傳》“巧則巧”、《唐太宗入冥記》“得則得”用法完全相同,從中也可看出“則”與“即”的關系。
“雖即”在其他文獻中也有用例,且有意義相同的倒序詞“即雖”,以下舉《唐律疏議》中的用例以作比較。先看“雖即”用例,卷3:“及受財而不枉法者,謂雖即因事受財,于法無曲。”[36]卷7:“御膳以下闌入,雖即持杖及越垣,罪亦不加。”[36]再看“即雖”,卷13:“婢為主所幸,因而有子;即雖無子,經放為良者:聽為妾。”[36]卷26:“‘賭飲食者,不坐,謂即雖賭錢,盡用為飲食者,亦不合罪。”[31]
“即”單用可表轉折,“雖即”組合有同義倒序形式“即雖”,再加上同義的“雖則”的使用,無不證明“雖即”組合中“即”仍發揮著表轉折的連詞功能,而非僅用以湊足音節的詞尾。
或即* 蔣文舉有三例,《維摩詰經講經文》:“(魔女)合玉指而禮拜重重,出巧言而詐言切切。或擎樂器,或即吟哦;或施窈窕,或即唱歌。”《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有時拗眼烈睛,或即高聲應對。”他認為:例20(即《維摩詰經講經文》例)“或即”與“或”對用,其“即”但助音節;例21(即《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例)對偶為文,為避復前言“有時”,后換用同義詞“或”,為了字數整齊,便給“或”帶上了詞尾“即”[1]83。
此種用法的“或即”其他文獻亦有用例,隋達摩笈多譯《起世因本經》卷7:“將詣果林,盛種種果,或即噉食,或取汁飲。”[38]唐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卷14:“凡人飲酒洽醉,狂詠便作,或即斗死,或則相傷賊害,或緣此奸淫,或緣茲高墮,被酒之害,不可勝記。”[39]《古尊宿語錄》卷20:“會即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半吃泥吃土,一半食麥食麻。或即降龍伏虎,或即摝蜆撈蝦。”[40]
“或則”有完全相同的用法,上舉《要修科儀戒律鈔》例中“或即”即與“或則”、“或”對舉使用,它例如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4:“世親才見十地,即為論釋,或則未窮廣文,或則知見有異,未全克定。”[41]《太平廣記》卷364:“或則叫噪,曾不動搖;或則彎弓發矢,又無中者;或欲環之前進,則亦相顧莫能先焉。”[14]2896
“或即”、“或則”中的“即”與“則”是否為“但助音節”的詞綴呢?我們以為并非如此,以下試論之。
考“即”與“則”單用,可用于并列分句中,表對情況的列舉和對比,文獻中用例甚多,此舉變文為例:《雙恩記》:“莫若入大海內,拜謁龍王,求摩尼寶珠,與眾生利益,要飯即雨飯,要衣即雨衣,要金銀即雨金銀,要珠玉即雨珠玉。”[8]934《長興四年中興殿應圣節講經文》:“遠即成佛度人,近即安民治國。”[8]618《廬山遠公話》:“當立即有,不立即還無,當信即有,不信即還無。”[8]262-263此三例“即”分別出現于并列的各分句中。有時“即”只出現于某個或某些分句中,如《雙恩記》:“多即我能施滿足,少時他不為添陪。”[8]933《捉季布傳文》:“閑來每共論今古,悶即堂前話典墳。”①[8]95
與“即”音近義通的“則”在變文中亦有相同用法,多分別出現于并列的各分句中,如《父母恩重經講經文》:“逐日則長隨惡伴,終朝則不近好[人]。”[8]978《祇園因由記》:“必要如此,請佛弟子共我角其神力,強則任致,弱則不許。”[8]602也有出現于某個或某些分句中的用例,如《韓擒虎話本》:“限百日之內,有使臣詔來,進一日亡,退一日則傷。”[8]29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約束時直要諦聽,嗔罵則莫生衹對。”[8]978
不僅如此,“乃”亦有此種用法,分別出現于各分句的用例如《降魔變文》:“六師乃悚懼恐惶,太子乃不勝慶快處。”[8]564也有單現于某個分句者,如《伍子胥變文》:“餓乃蘆中餐草,渴飲巖下流泉。”[8]4
“即”、“則”、“乃”還可對舉使用,如《伍子胥變文》:“兇即請自當,吉則知吾意。”[8]13《伍子胥變文》:“君乃先辱不輕,妾即后嫌不受。”[8]14《長興四年中興殿應圣節講經文》:“出乃百壁(辟)歡忻,入則六宮瞻敬。”[8]620
相同用法的“而”可幫助確定“即”、“則”、“乃”的連詞性質:《長興四年中興殿應圣節講經文》:“聞半偈而捐舍全身,求一言而祇供千載。”[8]618《長興四年中興殿應圣節講經文》:“至焉所化,廣大如斯,振搖而不異云雷,沃潤而還如春雨。”[8]621
將“即”與“則”的上述用法與“或即”、“或則”的用法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它們均用于平列結構中,在列舉功能上并無二致;不同之處在于,“或即”、“或則”句中“或”的指代對象不明,而未用“或”的句子,“即”、“則”前的成分往往直接說出。這種不同只是“即”、“則”前成分的差異,而不涉及“即”、“則”本身,“忽即”、“忽則”組合中“即”、“則”的連接功能并未消失,自然也就不是詞尾了。
三 表強調,加強肯定語氣,“實即”屬于此類
實即* 蔣文舉有兩個用例,《維摩詰經講經文》:“禪堂迮(窄)隘,實即難留;幽家非寬,無門受納。”《燕子賦》:“今欲據法科繩,實即不敢咋呀。”他認為“實即”相當于實在,“‘實即之‘即無義,有如現代漢語‘實在之‘在”[1]82。
此種用法的“實即”在其他文獻中亦有用例,只是較少見。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卷6第1287號:“著綺羅,掛綾絹,殮入棺中虛壞爛。分毫善事不曾修,實即令人哀憫見。”[42]《唐會要》卷77:“每讀《尚書·洪范》,至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并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即不倫。”[43]
“實即”解作“實在”沒什么問題,但“即”是否就是不表義的詞尾呢?我們認為需要慎重,因為文獻中可以看到與“實即”用法相同的“實乃”、“實為”、“實是”的用例,而且現代漢語中還有“實在是”與之相應。
實乃 《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北魏》:“功堅易于折枯,摧強甚于湯雪,偃骸積尸,野成京觀,獲將獻俘,千有余級。實乃殊機異詭,應時克捷也。”[44]《南史·梁宗室列傳上》:“上悅,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16]1275
實為 《晉書·杜預傳》:“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里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24]1031《南史·沈僧昭傳》:“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16]970
實是 《藝文類聚》卷37引陶弘景《答謝中書書》:“高峰入云,清流見底……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45]《敦煌變文校注·太子成道變文》:“如斯苦切,實是難陳。”[8]492
上舉“實乃”、“實為”、“實是”以及變文中的“實即”,都可以用“實在是”對譯,如“實即不敢咋呀”可譯作“實在是不敢違拗”;“如斯苦切,實是難陳”可譯作“像這樣的痛苦,實在是難以陳說。”
“實即”與“實乃”、“實為”、“實是”用法相同,當非偶然。我們知道,“即”可用于表強調,加強肯定語氣,相當于“是、就是”,為其常義,如《史記·項羽本紀》:“梁父即楚將項燕。”[7]295“乃”、“為”、“是”①均有相似用法,它們與“實”組合后,并未喪失這種強調功能,自然也就不能將“即”定性為詞尾了。而且若將“即”看作詞尾,與之用法相同的“乃”、“為”、“是”又該如何處理呢?
四 其他“即”的用例辨析
蔣文在論證變文中的“即”與六朝而下的詞尾“自”、“復”特點基本相同時,舉了變文中四個作為襯詞的“即”的用例:《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經文》:“善業感招生勝處,業緣重即卻沈淪。”《捉季布傳文》:“閑來每共論今古,悶即堂前話典墳。”《維摩詰經講經文》:“悶即交伊合曲,閑來即遣唱歌。”《維摩詰經講經文》:“如今看即證(菩提),不可交卻墮落。”蔣文認為:上述第一例“業緣重即”猶言“業緣重”,加一“即”字特為整齊罷了。二、三例“悶即”與“閑來”相對,第四例“看即”與“交卻”應合,“來”、“卻”都是語辭,故“即”字亦為語辭[1]83-84。
上舉四例“即”確有使字句和諧的功能,但并非襯詞,它在各句中仍保留有其固有語法功能:前三例均屬“即”連接平列結構的用法(“則”亦有此種用法,詳見第二部分“【或即】”下論述),其特點是:各分句所述情況相反或相對,以表列舉或對比,一般“即”同時出現于各分句,也有單獨出現某個分句之中的情況。以第三例來說,從字面上看,似乎“悶即”與“閑來”對應,實則前后兩句都有“即”字,在句中對應使用,起連接作用,“悶”真正對應的是“閑來”。一、二例亦屬此類,只是出于字句整齊的考慮,“即”僅出現于其中一個分句罷了。
第四例,“交卻”之“卻”并非語辭,這從文句前文可以知道:“持世告假帝釋曰:‘我修行日久,悟法分明,不可取你人情,交(教)我再沉惡道。況此之女等,三從備體,五障纏身。他把身為究竟身,便把體為究竟體。我所以棄如灰土,自力修行,如今看即證菩提,不可交(教)卻墮落。”[8]889“不可交卻墮落”對應“不可取你人情,交我再沉惡道”而言,“卻”乃“再”義。那么“如今看即證(菩提)”中的“即”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們認為這個“即”是其最普通的用法,“便、就”義,“看即”連用,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眼看就”,變文中還有其他用例,如《維摩詰經講經文》:“記取今朝相勸語,這身看即是無常。”[8]769《歡喜國王緣》:“王曰:‘夫人氣色,命有五朝,看即與朕不得相見。”[8]1090“看即”還可作“看看即”,《維摩詰經講經文》:“人身病,似枯樹,苦惱災危成積聚,看看即是落黃泉,何處令人能久住。”[8]834“看則”也有同樣的用法,《破魔變》:“莫為(謂)久住,看則去時。雖論有頂之天,總到無常之地。”[8]531還可作“看看則”,《漢將王陵變》:“玉漏相傳,二更四點,臨入三更,看看則是斫營時節。”[8]67“看看便”亦有相似用法,《維摩詰經講經文》:“廣現百般希有事,看看便是振春雷。”[8]767
蔣文還探討了詞尾“即”的起源,認為先秦兩漢文獻,未曾發現其端倪,六朝時,《世說新語》中有三例近是,分別為:
《德行》:“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文學》:“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為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1]84
第二例,“便即”乃同義組合,前文已經分析,此不贅。其他兩例中的“即”乃當時、立即義:第一例“即曉其旨”指殷覬“當時就知道他們的意思”,但他并未表現出來,而是趁行散時離開而不還,“即曉”與之后“行散離去”所間隔的時段正用以體現其有涵養;第三例“即解”與“即曉”義近,“于時謝不即解阮語”“即”緊扣“于時”,指當時謝安沒立即明白阮光祿之論①,因而才會有下文的“重相咨盡”。“即”的這種用法在文獻中很常見,如: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5]414《三國志·蜀書·譙周傳》:“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9[1028]《敦煌變文校注·燕子賦》:“既有上柱國勛收贖,不可久留在獄,宜即適(釋)放,勿煩案責。”[8]379
上舉用例中的“即”多置于副詞后,前后文語境能明顯揭示“即”之義。文獻中還有更多的“即”,所處語境不能明確揭示其含義,這種情況下,如果用“即”的既有意義去解釋并無問題,最穩妥的解決辦法,還是應當以其既有意義來處理。依照此原則,我們考察了大量文獻,得出的結論是:副詞與連詞與“即”構成的組合,難以有效佐證“即”有詞尾的用法。
五 “即”的詞尾性質探討的實踐意義
以上我們逐一分析了蔣文所舉變文中用為詞尾的“即”的組合,并系聯考察了與之結構及意義類似的其他組合,以及變文與其他文獻中“即”的使用,我們認為:在這些組合中,“即”主要發揮了其副詞及連詞的連接及強調功能,雖無實在的詞匯意義,但作為虛詞的語法功能并未消失,因此“即”并非詞尾。
另外,“即”的詞尾性質的探討,可為詞綴研究提供一些啟示:
一、一般認為,詞綴不負載詞匯意義,因而各家常以“義虛”作為詞綴的重要鑒別標準①[2]60。這個標準對有實在意義的實詞來說沒什么問題,但作為本無詞匯意義而僅發揮語法功能的虛詞來說,就不能適用。以“即”為例,它在“X即”組合中符合“義虛”標準,但不能因此將其定性為詞綴,因為它單用作副詞或連詞時,在很多情況下亦僅表語法功能,而無詞匯意義,構成“X即”組合后,其使用語境與“即”單用時并無不同,“即”在句中的既有語法功能并未消失。
二、學者們常利用去掉某個語素之后意義是否改變作為檢驗詞綴的方法,這種方法有一定的作用,但局限性很大,除了同義復合詞不能適用之外,其他一些結構的合成詞也有不適用的可能,而由無詞匯意義僅表語法功能的虛詞構成的組合②更多屬此類。以本文所舉“忽即、忽便、忽乃”來說,“即、便、乃”單用連接前后相承的兩件事,本就是可譯可不譯的成分③,與“忽”組合后,仍然如此,我們固然可譯成“忽然”,但譯成“忽然就”也未嘗不可。再如“或即”,“即”單用連接平列結構時,即無實義,在現代漢語中亦無對應成分,由它構成的“或即”組合,自然也不會有實義,這樣以去掉“即”意義是否改變來檢驗,當然不能說明問題。
三、學者們在論證某個詞為附加式時,常采用類比系聯的方法,如蔣文在論證“即”為詞尾時,將它與“自”、“復”聯系起來以證其性質[2]274。我們認為類比的方法確實重要而有效,但類比的使用必須符合“同類”的要求。以“即”與“自”、“復”來說,它們在詞匯意義、語法功能、與副詞連詞的組合能力以及組合出現和使用時代等方面均有明顯差異④,這樣的類比能在多大程度上說明問題,值得商榷。相對來說,將“遂即”、“便即”、“乃即”與“即遂、即便、即乃、便乃、乃便、遂乃、遂便、乃遂、便遂”等作類比,將“實即”與“實乃、實為、實是”作類比,將“然即”與“然則”作類比則要合適的多,因為無論作為單個語素還是所構成的組合,它們都具有很大共性。
四、蔣先生在文中特別強調,詞尾“即”的使用是為了湊足雙音節,以使字句和諧整齊,似乎這一點也可幫助確定“即”的詞尾性質(這是筆者閱讀時的體會,也許并非蔣先生本意)。其實,附加構詞固然是詞匯雙音化的重要手段,但絕不是唯一手段,事實上,同義復合遠比附加式重要,而使用只表語法意義的虛詞也完全可以達到組合雙音化、并使文句和諧整齊的目的。
參考文獻:
[1]蔣宗許.試論變文中的詞尾“即”[J].敦煌研究,1992(1):81.
[2]蔣宗許.漢語詞綴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9:273-275.
[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2:12.
[4]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3:2463.
[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0:288.
[6]劉淇.助字辨略[M].北京:中華書局,2004:219.
[7]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99:314.
[8]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7:2.
[9]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2002:447.
[10]陳橋驛.水經注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7:38.
[11]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2504.
[12]馮夢龍.警世通言[M].中華古典精華文庫:308.
[13]董志翹等.經律異相整理與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11:500.
[14]李昉.太平廣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3090.
[15]王云路.中古漢語詞匯史[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245.
[16]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1510.
[17]吳承恩.西游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949.
[18]葛洪.抱樸子內篇[M].北京:中華書局,1996:78.
[19]天然癡叟.石點頭[M].北京:學苑音像出版社,2005:469.
[20]楊爾增.兩晉秘史[M].中國古典精華文庫:760.
[21]大正藏:第31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81.
[22]大正藏:第20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748.
[23]大正藏:第87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1.
[24]大正藏:第17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795.
[25]大正藏:第5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349.
[26]周叔迦、蘇晉仁.法苑珠林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608.
[27]張君房.云笈七簽[M].北京:中華書局,2003:1865.
[28]大正藏:第15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490.
[29]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1865.
[30]慕平譯注.尚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9:323.
[31]俞樾.諸子評議[M].北京:中華書局,1956:174.
[32]吳昌瑩.經詞衍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162.
[33]黃暉.論衡校釋[M]. 北京:中華書局,1990:642.
[34]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M].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35]陳其猷.呂氏春秋校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1732.
[36]長孫無忌.唐律疏議[M].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
[37]朱平楚.西廂記諸宮調注釋[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139.
[38]大正藏:第1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401.
[39]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M].明正統道藏本.
[40]賾藏.古尊宿語錄[M].北京:中華書局1994:388.
[41]大正藏:第35冊[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529.
[42]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3]王溥.唐會要[M].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44]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34.
[45]歐陽詢.藝文類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