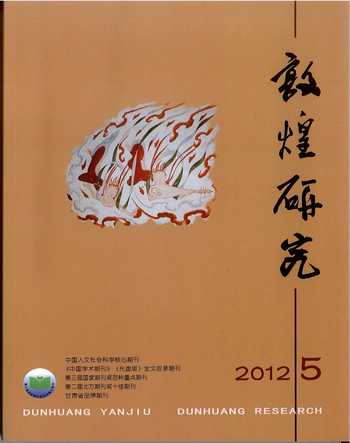唐宋之際敦煌農業領域受雇人的生活
徐秀玲
內容摘要:在敦煌出土的雇傭文書記載了唐宋之際農業領域里受雇人的工價。從文書記載可知,這時期的農業雇期雖然寫作“造作一周年”,實則為九個月;而雇價可能根據年齡的不同,有成丁雇價和非成丁雇價之分。非成丁雇價每月低于一馱;成丁雇價每月麥或麥粟一馱,“干濕中停”或“麥粟(種)中亭”。此期,敦煌普通農戶的生活支出主要有每日食糧、稅收、穿衣以及鄰舍人情往來等花費。因此,若農業領域里的普通農戶傭工收入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則其在農業領域的雇工收入不能、不足以養活自己和全家;反之,若受雇者本人是作為富余勞動力外出受雇,其收入也僅僅滿足家人的基本溫飽,幾乎沒有盈余。
關鍵詞:唐宋之際;敦煌文書;農業雇傭
中圖分類號:G25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2)05-0086-07
王梵志《貧窮田舍漢》詩云:“貧窮田舍漢,菴子極孤恓。兩共前生種,今世作夫妻。婦即客舂搗,夫即客扶犁。黃昏到家里,無米復無柴。男女空餓肚,狀似一食齋。里正追庸調,村頭共相摧。幞頭巾子露,衫破肚皮開,體上無裈袴,足上復無鞋。丑婦來惡罵,啾唧搦頭灰。里正被腳蹴,村頭被拳搓。驅將見明府,打脊趁回來。租調無處出,還須里正倍。門前見債主,入戶見貧妻。舍漏兒啼哭,重重逢苦災。如此窮硬漢,村村一兩枚。”[1]
這首詩惟妙惟肖地描繪了唐代農業領域里一對夫婦的傭作及其生活情況,婦給人舂搗,夫給人耕作,黃昏回家里,無米復無柴,還要交納庸調,被債主逼債,屋漏兒哭,日子過得極其艱難。此外,在吐魯番178號墓出土文書開元廿八年(740)記載:“阿毛孤一身,有(又)無夫婿,客作傭力,日求升合養姓(性)命。”[2]《太平廣記》卷347《李佐文》記載唐文宗太和六年(832),李佐文旅食南陽林湍縣官僚袁測田莊,見一婦人,自稱:“我傭居袁莊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齔之女又亡,貧窮無力,父子同瘞焉。守制嫠居,官不免稅。”[3]可見,在唐代受雇人的收入及生活極其艱辛。但是否這時受雇人的生活都是如此呢?在敦煌出土的一批雇傭文書為我們了解唐宋之際歸義軍政權下敦煌的工價和受雇人的生活提供了大量的資料。筆者以農業領域里的一批雇傭契約來分析此期農業受雇人的生活情況。
一 唐宋之際農業領域里的雇價
在敦煌出土的歸義軍時期的雇傭文書中,農業雇傭的周期一般寫作“一年造作”、“造作一周年”[4],只有極少數寫作“從正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末”[5],“從正月至九月末”等[4]60。但是筆者從雇主支付的雇價“見與春三個月價,更殘六個月價(到秋后)還”,實際上雇主只支付了九個月的工價給受雇的農業勞動者。為明白起見,轉錄文一件如下。北圖309:8374(即生字25)《甲戌年(974年)竇跛蹄雇工契(抄)》:
1甲戌年正月一日立契,慈惠鄉百姓竇跛蹄,伏緣家中欠
2少人力,于龍勒鄉鄧納兒缽面上雇男延受造作一周年。
3從正月至九月末,斷作雇價每月壹駝,春衣壹對,汗
4衫壹領,[衤曼]襠壹腰,皮鞋壹兩。自雇如后,便須
5兢兢造作,不得拋功壹日。忙時拋功壹日,克物貳斗。
6閑時拋功壹日,克物一斗。若作兒手上使用籠具鎌刀鏵[釒冓]
7鍬镢袋器什物等,畔上拋抶打損,裴(賠)在作兒身(上),不關
8主人之事。若收到家中,不關作兒之事。若作兒偷他(人)瓜
9菓菜如(茹)羊牛等,忽如足(捉)得者,仰在作兒身上。若作兒病
10者,算日勒價。作兒賊打將去,壹看大例。兩共對面平章,
11準格不許番(翻)悔者。已己,若先悔者,罰青麥壹拾駝,充入不
12悔人。恐人無信,故立私契,用為憑(后有勾)押字為定(押)。[4]69
從這件雇工契中我們可以看到,文書第2行雇主竇跛蹄雇龍勒鄉鄧納兒缽之子延受“造作一周年”,但是在文書第3行支付的雇價卻是“從正月至九月末,斷作雇價每月壹駝”。可見雇主僅支付了受雇者九個月的雇價。
由于農業雇工的實際受雇日期是九個月,那么雇主就不會如契約開頭所寫那樣,支付雇工一年的工價卻讓雇工干九個月的農活。從已經發現的敦煌雇傭文書看,這時期的大多數雇價一般寫作“逐月壹馱”、“每月壹馱,干濕中亭”或“每月一馱,麥粟各半”,有少數文書寫作“每月五斗”、“每月斷物捌斗”等①。可見,在歸義軍統治敦煌時期的農業雇價的多少并不相同。為明晰起見,詳見表1、表2①。
歸義軍時期農業雇價,從表1所列5件契約信息我們知道,每月不到一馱者,雇價從五斗、八斗、八斗七升到一石不等;表2所列21件為每月雇價一馱者,麥一馱或麥粟一馱,且麥粟各半。一馱是多少呢?把敦煌出土的歸義軍時期的雇傭契約與吐蕃時期的對比,歸義軍時期的契約并未注明雇主支付雇價糧是漢碩還是番斗。高啟安先生曾對“敦煌的馱”作過專門的研究,他認為“吐蕃的升斗和馱,很可能在張議潮率眾推翻吐蕃人統治后不久即自行消除了”[6]。換而言之,9世紀中葉以后的敦煌,作為量制的“馱”,就應該是漢馱了。而我們這里討論的敦煌雇傭契,均屬9世紀中葉以后唐末宋初時期的契約,所行用的應該是漢馱[7]。高啟安先生據S.6829《丙午年正月十一日已后緣修造破用斛斗布等歷》等文書判斷“一馱等于兩石”,而“在當時的敦煌,‘十斗為石是定制”[6]61-68,根據唐代的“權衡度量之制”規定“十合為升,十升為斗”[8]。如果按照每月平均30天計算,這時期表1中的日均雇價從1.67升到3.33升不等,表2中的日均雇價為6.67升。可見這時期農業領域里的雇價也是高低不平的。但是通過這兩個表格我們發現,從數量上看,表2所列雇價每月一馱者占這時期農業領域雇價的絕大多數。
在雇期一定的情況下,表1中的雇價比表2中的雇價要低。在表1中,除第4件文書殘缺嚴重看不出被雇者的身份外,其余四件的受雇者均是“于某面上雇弟(或男)”,即受雇者是某鄉百姓的弟弟或兒子。如第2件梁戶史氾三從“平康鄉百姓杜愿弘面上雇弟愿長”,第3件莫高鄉孟再定雇“龍勒鄉百姓馬富郎弟盈德”,第4件敦煌鄉百姓蘇流奴于“效谷鄉百姓韓德兒面上雇壯兒”。這三件契約的年代主要分布于歸義軍統治時期的924至955年間,與表2中的年代基本一致。但是我們通過考察表2中的受雇人信息發現,其中也存在“于某面上雇弟(或男)”的情況,如第2、3、5、6、7、10、11、13、14、15件,但是他們的雇價同本表中其他人的雇價一樣也是每月麥粟一馱,即日均雇價6.67升。是什么原因造成這種情況呢。《唐六典》卷6《都官郎中》記載:“四歲已上為‘小,十一已上為‘中,二十已上為‘丁。”[9]《舊唐書》卷43《職官志》記載:“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8]1825《新唐書》卷51《食貨志》記載:“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同卷又載:“明年(開元二十六年),又詔民三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二十以下為中。”[10]雖然不同典籍中記載的成丁、中男、小男年齡不一,但這僅是唐代不同時期政府統治政策的變化。那么,在表1和表2中所列這些“于某面上雇弟(或男)”,他們之間之所以有雇價上的不同,最大的可能是與他們年齡有關,即他們是否屬于成丁的范圍。因為雇工有是否成丁的區別,所以在這時期的農業雇傭中受雇者的雇價有很大的差別,即成丁雇價每月一馱,非成丁每月雇價不到一馱。
二 唐宋之際敦煌農業領域受雇人的生活
1.歸義軍時期敦煌的戶均人口及口糧消費
凍國棟先生認為,唐前期西州地區戶均人口4—5人。就敦煌籍帳所見唐前期沙州戶均口數和內地諸州相比差別不大,一般也應以5口之家居多[11]。但是到歸義軍政權時期,特別是經過張議潮多次戶口登記及析戶后,敦煌戶口結構基本趨于合理,從保留下來的戶籍看,每戶人口主要以5—7口為主。但是從大順年間起敦煌地區出現了一個現象,就是戶口變得越來越小,五口之家、三口之家比較常見[12]。然而即使如此,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地區其人口平均還是在四口及以上。
在唐宋時期,每人日均食糧情況記載如下:《新唐書》卷54《食貨志》記載:“當時議者以為自天寶至今,戶九百余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為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10]1387《宋史》卷175《食貨志》記載:“陜西都轉運司于諸州差雇車乘人夫,所過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13]《宋史》卷181《食貨志》記載:“天圣以來,兩池畦戶總三百八十,以本州島及旁州之民為之。戶歲出夫二人,人給米日二升。”[13]4415《宋史》卷194《兵志》:“中興以后,多遵舊制。紹興四年,御前軍器所言:萬全雜役額五百,戶部廩給有常法。比申明裁減,盡皆遁逃。若依部所定月米五斗五升,日不及二升……詔戶部裁定,月米一石七斗增作一石九斗。五年詔,效用入資舊法,內公據,甲頭名稱未正,其改公據為守闕進勇副尉,日餐錢二百五十,米二升;甲頭為進勇副尉,日餐錢三百,米二升。非帶甲入隊,人自依舊法。宣撫使韓世忠言:本軍調發,老幼隨行。緣效用內有不調月糧,不增給日請。軍兵米二升半、錢百。效用米二升,錢二百。乞日增給贍米一升半。”[13]4846-4847《宋史》卷491《日本國傳》:“淳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毆鄭作死……以其國之法,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眾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者,復百余人。詔: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13]14137
從以上諸條史料的記載,唐宋時期人均日食糧是糧2升或者接近2升。并且,傳世典籍中每人日均的記錄也被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記載驗證。如《唐蘇海愿等家口給糧三月帳》:
16戶主劉濟伯家囗
17二人丁男,一日粟三升三合三勺。二人丁妻,一日粟二升五合。
18一人中小,一日粟一升五合。[14]
又如《唐神龍二年(706)七月西州史某牒為長安三年(703)七至十二月軍糧破除見在事》記載:
7米一斗八升
8右被倉曹十二月一日牒給伊州鎮兵雷忠恪充十日
9糧,典宋祚,官準前
10米五斗二升
11右被倉曹十二月十日牒給患兵陰懷福三人充十
12日糧,典張達,官準前
13米七斗二升
14右被倉曹十二月廿三日牒給患兵田文囗等四人
15糧,典和讓,官準前
16米七斗二升
17九月前牒給患兵喬什力等四人充十日糧,官典準前。[15]
在這兩件文書中,劉濟伯家五口人日均糧食約2.4升;長安三年鎮兵雷忠恪和患兵田文囗、喬什力等九人的軍糧日均1.8升,患兵陰懷福等三人的軍糧日均1.73升。那么,在唐代成年丁的食糧定量一般在每日1.8升到2.4升之間,以日均二升為主。如此,根據不同時期每人日均配額糧2升,一個成年丁男或者丁女一年365天要消費糧食730升,即7.3石。因此,如果我們按照人均年消費7.3石計算,以5口之家算,則需要36.5石;即使按照每戶均3口算,一年的糧食消費也至少需要21.9石。
2.敦煌普通農戶的土地收入及其支出
在歸義軍政權初期,無地或少地的民戶,政府授予土地的數量是每人七八畝[16]。一家四五口人有地三四十畝。當時敦煌糧食的產量據P.2451《乙酉年(925或985)二月十二日乾元寺僧寶香雇百姓鄧仵子契》中雇價的支付“每月斷作雇價麥粟壹馱。內麥地叁畝,粟地肆畝,其地折柒個月”[4]70,即麥地三畝和粟地四畝計七畝地的收入折合七個月的雇價麥粟七馱。平均每畝地收入麥粟一馱。與吐蕃時期的產量如P.3774《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龍藏牒——為遺產分割糾紛》中記載:“去丙寅年至昨午年卅年間,伯伯私種田卅畝,年別收斛斗卅馱。”[4]283平均每畝收獲一馱。可知,吐蕃和歸義軍時期的糧食產量相差不多。那么,歸義軍政權初期的每人七、八畝土地,年收入七、八馱,即14至16石之間;戶均三、四十畝土地,收入才三、四十馱。
但是,我們從零星的史料知道中古時期的受雇人也是要納稅的,如劉宋時期官府對郭世道“蠲其稅調”[17],王彭“蠲租布三世”[17]2250,南齊時對公孫僧達等人“蠲租稅”[18],王梵志詩《貧窮田舍漢》詩云:“貧窮田舍漢,庵子極孤恓。兩共前生種,今世作夫妻。婦即客舂搗,夫即客扶犁。黃昏到家里,無米復無柴。男女空餓肚,狀似一食齋。里正追庸調,村頭共相摧。幞頭巾子露,衫破肚皮開,體上無裈袴,足上復無鞋……驅將見明府,打脊趁回來。租調無處出,還須里正倍。”《太平廣記》卷347《李佐文》記載唐文宗太和六年(832),李佐文旅食南陽林湍縣官僚袁測田莊,見一婦人,自稱:“我傭居袁莊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齔之女又亡,貧窮無力,父子同瘞焉。守制嫠居,官不免稅。”[3]2752況且我們從歸義軍時期受雇人的身份看,他們都是各鄉百姓,在雇傭契約中記載有鄉名,是具有正式戶籍的編戶。因此,他們也必須納稅。而歸義軍政權時期的賦稅主要包括地子、官布、草、柴等。其中地子的稅率是麥粟合計每畝一斗。25尺為一匹的官布,若250畝納官布一匹,一畝地為0.1尺,若300畝地納布一匹,則一畝地為0.08尺。百姓田地每畝稅草約三至七分,即0.3—0.7束。至于稅柴的具體稅率,即一畝地納柴多少束,則由于資料的缺乏,目前還無法給予明確的回答[16]107,130,140。但官布和糧食的征納是可以換算成以糧食為標準價比率的。在P.2504《年代未詳(10世紀)龍勒鄉百姓曹富盈牒(稿)》中記載了布與麥粟的比價,轉部分錄文如下:
1龍勒鄉百姓曹富盈。右富盈小失慈父,狗(茍)活艱辛。
2衣食之間,多有欠缺,只有八歲父馬一疋,前日叔父都衙
3賣將,判絹兩疋已來,內一疋斷麥粟廿七石,內
4十二(應為二十:筆者注)石直布兩疋,又欠七石,又一疋斷牛一頭。(后略)[4]313
這是一件10世紀曹富盈狀告其八歲父馬被叔父都衙賣掉不給價錢之事。在文書中我們知道,馬被賣絹兩匹,其中一匹絹被斷麥粟27石,并且27石麥中的20石值布兩匹。雖然我們不明布的質地如何,但假若是官布,那么此時期的官布一匹相當于麥粟10石,官布一匹25尺,即官布一尺折合麥粟4斗,那么,每畝交納官布0.1尺或者0.08尺,折合糧食麥粟大約3.2升—4升之間。如此,歸義軍時期的地子和官布征收折合糧食將在1.32斗—1.4斗。在歸義軍政權初期平均每人七、八畝的土地至少要交稅在9.3斗至11.2斗之間,即大約1石左右,再加上每人要交納附著于土地上的各種賦役雜稅以及承擔諸種勞役,其負擔還是比較重的。
在歸義軍時期,即使用最便宜的昌褐作春衣,一個成年丁男也得需要“貳仗叁尺”或“貳仗肆尺”[19]抑或是“粗布一疋”[19]254,“皮鞋一量”花費“一石三斗”[19]153。關于衣服的支出,在P.2504中記載的是布一匹值糧食10石,吐蕃時期氾英振承造佛堂契中是“其麥平章日付布壹疋,折麥肆碩貳斗,又折先負慈燈麥兩碩壹斗”即布一匹值麥六碩三斗。做衣服的粗布一匹如果按照吐蕃時期的最低價6石3斗計算。這樣,一個成年人一年的服裝消費折合糧食至少要在7石3斗左右。在敦煌的農業雇傭中雖然有的雇主為受雇人提供了衣服鞋襪等衣物,但是其家庭成員的衣服鞋襪等的支出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在以上諸種情況下,歸義軍時期的普通農戶一年里土地上的收入可能收支基本平衡,滿足其及家人最低的生活需求。但這還不包括我們未知的鄰里鄉親之間的人情往來花費。
由此可知,歸義軍時期敦煌農業領域的雇工,若其傭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則其在農業領域的雇工收入不能、不足以養活自己和全家。當一個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外出受雇,家中僅靠妻兒婦孺是很難組織正常生產活動的,在S.3877背《戊戌年(878)令狐安定請地狀》[4]469中記載同鄉女戶陰什伍有地15畝,女戶陰什伍可能只有一口人,“今緣年來不辭承料”①,其地被令狐安定兄弟請去。反之,若其本人是作為家庭中的富余勞動力外出受雇,且家中人均耕地不少于七、八畝,其收入是對家庭經濟收入的補貼。總而言之,唐宋之際歸義軍政權下的敦煌農業雇工收入雖然不像王梵志等詩文中所描繪的那么凄慘,但也僅僅滿足自己及其家人的基本溫飽。
參考文獻:
[1]項楚.王梵志詩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651.
[2]唐長孺.吐魯番出土文書:第8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385.
[3]李昉.太平廣記:卷347[M].北京:中華書局,1961:2752.
[4]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二輯[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印中心,1990:67,69.
[5]乜小紅.俄藏敦煌契約文書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88.
[6]高啟安.唐五代宋初敦煌的量器及量制[J].敦煌學輯刊,1999(1):61-68.
[7]乜小紅.對敦煌農業雇工契中雇傭關系的研究[J].敦煌研究,2009(5):119-120.
[8]劉昫.舊唐書:卷48[M].北京:中華書局,1975:2089.
[9]李林甫.唐六典:卷6[M].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2:193.
[10]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51[M].北京:中華書局,1975:1342,1346.
[11]凍國棟.中國人口史:第二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450,484.
[12]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區人口變化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04(12):26.
[13]脫脫.宋史:卷175[M].北京:中華書局,1977:4257.
[14]唐長孺.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六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8—21.
[15]榮新江,李肖,孟憲實.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M].北京:中華書局,2008:25.
[16]劉進寶.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18.
[17]沈約.宋書:卷91[M].北京:中華書局,1974:2244.
[18]蕭子顯.南齊書:卷55[M].北京:中華書局,1972:957.
[19]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三輯[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