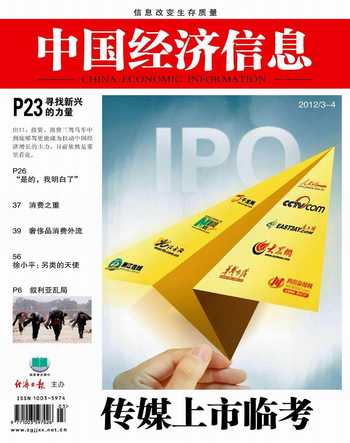美國富人納稅的邏輯
王素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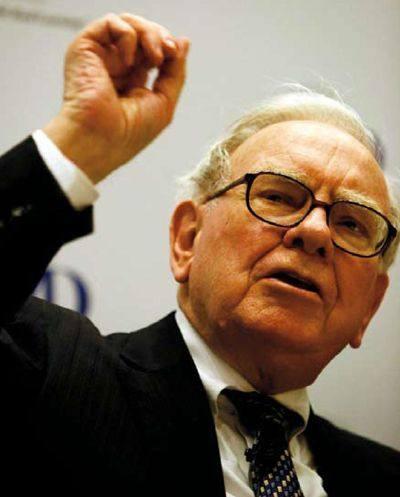
去過美國的人都知道,按時照章納稅在美國是一件既平常又普通的事。每年的4月15日是美國人申報上一年收入和納稅情況的最后截止日,這一天,美國人都會“自覺”的完成報稅事宜。
多年來,美國一直致力于信譽的制度的建立,稅制只是這種制度的縮影。在美國一個公民如“擁有”逃稅的信譽紀錄,那么接下來將面臨“不可承受的懲罰”。高昂的代價維護了稅制的尊嚴,至今美國建立的合理而先進的累進制稅制被多個國家效仿。
巴菲特規則
股神巴菲特是美國財富的象征,他的言談和行動早已成為“風向標”。2007年的一句笑談竟被命名為“巴菲特規則”,意思就是美國的富人應該納更多的稅。
2007年6月26日,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頓的一次競選籌款會中抨擊美國的稅收制度:“去年我的個人收入是4600萬美元,但是聯邦稅率是17.1%,而我公司前臺接待人員的聯邦稅率竟然高達30%,政府制定這樣的稅收不合理。”
美國的聯邦稅率累進制是這樣規定的:最窮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1萬5千4百美元)收入稅率為4.5%,中間三級的稅率分別為10%、14%、17%;最富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20萬7千2百美元)聯邦稅率為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萬美元)聯邦稅率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稅率只有17%,是因為他的大部分收入來自于股票之類的資本收益,而資本收益的稅率為15%。而且,在巴菲特交15%個人所是稅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交了35%的公司所得稅。在這個意義上,他實際上是被征了兩輪稅。
在美國社會,“富人俱樂部的精英”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他們深知,是良好的社會制度賦予了他們機遇與成長的土壤,要想使這一合理社會良性地循環下去,他們的責任就是讓政府“劫富濟貧”。
2010年,美國“財政實力之百萬富翁”組織誕生。最近,在該組織網站的首頁上發表了致美國“超級委員會”的一封公開信,信中請求國會增加年收入在百萬美元以上人的稅收,向美國的百萬富翁“定向加稅”。據信,在這封公開信上簽字的百萬富翁已經超過100人,其影響正在擴大。
在沒有得到美國政府回應后,2011年11月16日,由140名百萬富翁聯名向奧巴馬及國會領袖致函稱,“請做這件正確的事,提高對我們的征稅。”信中提到,良好的經濟曾讓他們受益,現在也希望別人能得到好處。
在“占領華爾街”這樣的事件背景下,“財政實力之百萬富翁”的壯舉被外界認為是一場“表演秀”。憤怒的“占領華爾街”人們認為,“華爾街精英”是制造金融危機的“背后黑手”,是賺取巨額財富的“掠奪者”。
這樣的論斷未免有失偏頗。“眾所周知,由于近年來科技經濟的發展、對沖基金的興起以及大公司CEO的薪金屢創新高,美國涌現了一批超級富翁。這些超級富翁之富,已經把一般的中產階級遠遠地甩在了后面,擴大了美國的貧富差距。據統計,美國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國民稅后收入比較已經從1980年的3.7%跳躍到了2002年的7.4%。1990年到2002年,美國底部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長1美元,頂部0.01%的人口(大約1萬4千戶家庭)就增長1萬8千美元。由于這些頂級富翁大量收來自于資本收益,而資本收益稅率只有15%,因此才出現超級富翁比一般中產階級稅率低的奇怪現象。也就是說,美國的稅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進和相對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節不保,驟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民主的細節》作者劉瑜分析道。
毋庸置疑,以上140名富翁,包括巴菲特在內,他們是美國這一稅制的最大受益者,累進制讓他們的收入得到了利益最大化,但這一群體已意識到這種稅制帶來的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合理,為此,呼吁奧巴馬政府改革稅制。
在福利化社會,為實現社會的公平,常常是“劫富濟貧”。在美國,富人多納稅,窮人少繳稅甚至不納稅,被認為天經地義。據美國國稅局數據,2007年,美國收入最高1%的人所交的個人收入所得稅占聯邦政府所得到的個人收入所得稅的40.4%,而95%的中低收入納稅人所繳的個人收入所得稅占政府所征收個人收入所得稅總額39.4%。
很顯然,金融危機已充分暴露出“福利化”社會的弊端。美國剛剛成立的“超級委員會”已于2011年11月21日宣布,其減赤努力以失敗告終。目前在美國二次分配不均已將“公平與效率”的不合理推向風口浪尖。
政府的回應
2012年1月24日,奧巴馬在國會發表就職以來的第三份國情咨文提出,以“巴菲特規則”改革美國的稅收體制,即對年收入在百萬美元以上的富人加稅。
奧巴馬說,美國的百萬富翁至少應該繳納30%的稅費,而不能只通過15%的收益所得稅率來“逃避社會責任”。在此基礎上,新稅制更提出美國富人也不應再享有住宅、醫保、退休和撫育方面的優惠稅收政策。
支持奧巴馬稅收改革的一方認為,推行“巴菲特規則”可謂一舉兩得。聯邦政府既能通過增收緩解赤字的燃眉之急,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社會不公的趨勢。
共和黨陣營及其他反對稅收改革的人則認為,向富人征稅的稅改措施達不到預期目的,特別是對美國當前的失業問題無助于解決。
凱托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邁克爾?坦納爾則認為,美國存在的社會不公并非緣于布什時期的減稅政策以及前政府對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缺乏投入,而是由美國經濟的重心從傳統的制造業向信息科技領域轉移導致的。“在經濟重心轉型的情況下,社會對高科技人才的需求增大,文憑高的自然比文憑低的掙得多,社會差距也就因此形成。盡管奧巴馬政府對教育投入巨大,但許多民眾未能提升素質以適應21世紀經濟形態的需求。赤字、債務和社會不公,與對富人減稅的政策沒有關系。”
坦納爾援引1974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哈耶克的理論說,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社會差距的基礎上,整齊劃一不能獲得發展,社會進步必然以人們的“階梯狀”方式實現。
近日,美國稅務專家細算了一筆賬:美國富人的繳稅稅率雖然表面上只有15%左右,但多數人的投資收益首先會被管理的公司抽去大約30%的稅費。如果兩項相加,很多富人實際的繳稅稅率達到了45%。此外,很多富人繳稅稅率偏低是因為他們對慈善事業的大額捐贈,從而享有稅收減免。譬如,“股神”巴菲特2010財年的可征收稅率為17.4%,但在減免之后只繳納了11%。羅姆尼的可征收稅率為17.6%,但最終只需繳納13.9%。
“問題的實質在于,美國的聯邦稅制發展沒有適應‘新經濟發展帶來大量超級富豪這個變化。這個問題也是民主黨和共和黨斗爭的戰場之一。布什政府2001年剛上臺的時候推出一個減稅方案,盡管這個減稅方案對每一個階層都減了稅,但是這個減稅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統計表明,被減去的稅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0.1%人口。2001到2006年美國收入最低的20%人口通過減稅收入只提高了0.3%,中間20%的人口同比為2.5%,但是最富的1%人口同比為5.4%。客觀地說,是經濟結構的變化而不是稅制或者稅改造成貧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稅制顯然沒有適應經濟結構的變化而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劉瑜指出。
在美國,向富人征稅是一件很難的事,共和黨的陣營中集合了美國的“財富大亨”,奧巴馬的減稅計劃必須要通過國會通過。前不久,“超級委員會”提交減赤草案努力的失敗已說明,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在治國經濟理念上的巨大差異,奧巴馬能否有力量了粘合這種差異,我們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