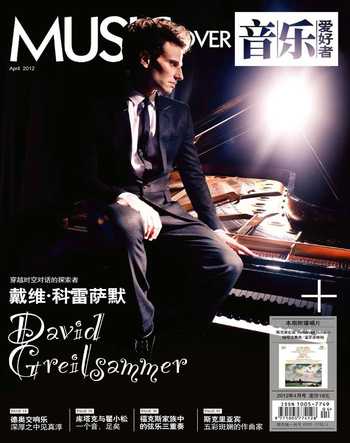無憂宮里的腓特烈大帝
韓斌



皇帝能作曲,還能吹長笛?似乎有些讓人覺得不可全信,會不會外國皇帝也像咱們的乾隆爺那樣會附庸風雅,作個幾萬首御制詩,水平卻讓人不敢恭維?倒也不盡然,在西方音樂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帝王作曲家就是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他的水準就不是一般業余級別的,而是相當專業。
腓特烈大帝即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1712-1786),他不僅是普魯士王國杰出的君王、軍事家,還是一位作曲家、長笛演奏家、著名的音樂贊助人。他一生寫過一百多首長笛奏鳴曲、多部交響曲,還有如普魯士最著名的軍歌《霍亨弗里德伯格進行曲》大概也是出于他的手筆。
腓特烈大帝出生于1712年1月24日,他的父親是普魯士的威廉一世,因為他的兩個哥哥夭折,所以父親對腓特烈寵愛有加。雖然威廉一世希望兒子能像條頓騎士那樣對舞刀弄槍感興趣,但仍然安排蒙特巴爾夫人擔任他的家庭教師,讓腓特烈接受完整的法國教育。從小腓特烈就一副知識分子的模樣,喜歡偷偷地看書、和仆人們一起演奏長笛奏鳴曲,而且特別崇尚法國文化。腓特烈最重要的教師杜漢(Jacques Duhan)是一個標準的胡格諾教徒,他引導這位太子對詩歌、古希臘古羅馬經典文化和法國哲學倍感興趣,同時也使腓特烈那種兼具宗教信仰和實用主義的處事作風得以形成。
七歲的時候,腓特烈就隨御前管風琴師漢內(G. Hayne)學習作曲,他的姐姐威廉米娜也喜歡音樂,常常和弟弟一起演奏和作曲。1728年,腓特烈造訪德累斯頓,平生第一次聽歌劇,也第一次聽到匡茨演奏長笛,后來腓特烈就跟匡茨學習長笛了。不過,威廉一世感覺到兒子似乎對文藝過分喜愛,以至于對軍事不感興趣,于是,他開始將腓特烈周圍的法國人漸漸調走,并用軍事教育手段對他施加壓力。
1730年8月4日,十八歲的腓特烈異想天開地和好友凱特一起準備逃往英格蘭,結果當然被父親拘拿,禁閉起來,而凱特則被處決,以儆效尤。
為了讓兒子早點斷絕各種浪漫的念頭,威廉一世開始考慮讓腓特烈結婚,一開始的人選是俄羅斯的安娜公主。但由于國內親奧地利勢力強大,最終,威廉一世還是選定了布倫斯維克的伊麗莎白·克里斯蒂娜女公爵。1733年,腓特烈很不情愿地和伊麗莎白結婚,他對妻子表現出充分尊重,因為他答應過父親即便和妻子分居也不會去找情婦,這一點他做到了。早在1740年腓特烈大帝登基之前他們就已經分居,以至于腓特烈大帝膝下沒有子嗣。
腓特烈大帝之所以會被冠以“Great”的名號,當然與他登基之后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權戰爭以及七年戰爭中表現出來的卓越軍事才能有關。然而,歷史上腓特烈大帝同時也以擅長音樂和對音樂的贊助活動而聞名。這位醉心藝術的皇帝在宮廷里保留了一支小樂隊,1736年移居萊茵斯貝格的時候還帶走了十七位音樂家,其中不乏像約翰·本達這樣的出色作曲家。
1740年,腓特烈親政,在政治和國務活動之余仍然關心藝術活動,特別是復興普魯士藝術的工作始終讓他牽掛。就在親政之后不到兩個月他就下令由作曲家格勞恩擔任普魯士宮廷樂長,每年給他兩千泰勒的高薪,并讓格勞恩到意大利為新建的柏林歌劇院招賢納士。他還通過自己的好友(如伏爾泰或者意大利哲學家阿爾加洛蒂等)從巴黎和意大利為劇院搜羅演員、舞者、腳本作家甚至是道具工作者。
不久,奧地利王位繼承權戰爭爆發了,腓特烈大帝忙于軍務,以至于1741年3月格勞恩帶著第一批歌手從意大利回到柏林的時候也不在柏林。C.P.E.巴赫曾經在萊茵斯貝格擔任過宮廷樂隊的首席羽管鍵琴演奏家,1741年,匡茨也是在腓特烈大帝的親自關心下,從德累斯頓被“挖”到了柏林,當時他在德累斯頓宮廷供職,年薪兩百五十泰勒,腓特烈大帝大筆一揮,同意給他每年兩千泰勒。到1754年時,宮廷已經有了五十多位音樂家為皇家提供服務,其中樂手有四十位,獨唱歌手八位,還有專寫歌劇的宮廷作曲家。腓特烈大帝出手闊綽,對自己鐘愛的歌唱家更是如此,他給首席女高音喬萬娜·阿斯圖拉(Giovanna Astrua)每年的年俸就是六千泰勒,這在當時可是一個天文數字。皇帝還新建了歌劇院,即便在七年戰爭期間仍然沒有荒廢自己的藝術情趣,不僅觀劇不輟,而且還在皇宮里組織演出,讓匡茨為自己寫長笛協奏曲。
然而,在七年戰爭期間,腓特烈大帝的“口味”卻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他變得越來越保守,尤其不喜歡器樂作品,以至于包括C.P.E.巴赫、尼希曼等在內的一批優秀作曲家離開了普魯士。作曲家的離開使歌劇創作陷入低谷,從1756到1764年,柏林歌劇院沒有上演過新作品,直到1786年腓特烈大帝去世時,劇院也大多上演七年戰爭之前的作品。
腓特烈大帝一直是藝術愛好者和贊助人,他喜歡聽歌劇,所以親自過問了柏林國家歌劇院的修建工作,還督促建造了皇家圖書館(今德國國家圖書館)、圣海德薇格教堂和亨利親王宮(今洪堡大學),當然還有在波茨坦的著名的無憂宮(Sanssouci),據說這個美麗宮殿的名字來源于大帝的一句話:“吾到彼處,方能無憂”(Quand je suis là, je suis sans souci)。就在這座宮殿里,腓特烈大帝和樂隊一起演奏,由宮廷畫家門澤爾執筆,畫下了那幅著名的《無憂宮的長笛音樂會》。
在腓特烈大帝的宮廷里,曾經駐有一大批優秀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后來在音樂史上名氣最大的當屬C.P.E.巴赫,這位后來被稱為“漢堡巴赫”的作曲家在腓特烈大帝宮廷擔任羽管鍵琴演奏家,為皇帝演奏長笛的伴奏。不過,當時C.P.E.巴赫在宮廷的地位并不高,薪俸也比較可憐,后來由于泰勒曼去世,他才從柏林移師漢堡,最終在那里功成名就。值得一提的是C.P.E.巴赫的父親J.S.巴赫在1747年曾經造訪過兒子工作的柏林,并拜見了腓特烈大帝,皇帝對老巴赫推崇備至,兩人相談甚歡,最后,腓特烈大帝親自寫了一個主題給巴赫,希望他能夠譜寫一首賦格。老巴赫回到萊比錫后即動筆譜曲,這些作品就是后來集成一套的《音樂的奉獻》。
有一位可以說影響了腓特烈大帝創作與演釋的音樂家是約翰·約阿希姆·匡茨(Johann Joachim Quantz)。1697年,匡茨出生在哥廷根,比腓特烈大帝大十五歲。匡茨早年喪父,由叔父教授他音樂知識。匡茨去德累斯頓和維也納學習過小提琴、雙簧管和長笛,后來他專攻長笛,成為當時歐洲首屈一指的長笛演奏家。匡茨曾經在波蘭的奧古斯都二世宮廷里供職,創作過不少長笛協奏曲。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匡茨到法國和英國旅行演出,對長笛樂器進行了改造并教授如何演奏長笛。還是王儲時腓特烈就向匡茨學習長笛,匡茨是一位稱職的教師,和一般演奏家只示范卻沒有方法不同,匡茨很會總結方法,他在1752年還寫過一本《長笛演奏法》。匡茨的成功教學使腓特烈大帝終生對長笛情有獨鐘,并達到了相當高的演奏水準。
還有一位作曲家也對腓特烈產生了重要影響,就是卡爾·海因里希·格勞恩(Carl Heinrich Graun)。1704年5月,格勞恩出生在勃蘭登堡的一個音樂世家,在遷居布倫瑞克之前他一直在德累斯頓的唱詩班里擔任歌手,業余時間還寫過六部歌劇。1735年格勞恩來到了萊茵斯貝格,因為曾經為腓特烈大帝的婚禮寫過慶賀歌劇,格勞恩很得恩寵,先是在王儲那里當樂長,1740年腓特烈大帝登基后便被擢升為普魯士宮廷樂長。格勞恩是當時重要的歌劇作曲家之一,他寫過很多歌劇,如1742年為柏林歌劇院開幕而作的《凱撒與克里奧佩特拉》(Cesare e Cleopatra)就是很有名的作品。腓特烈大帝對格勞恩十分信任,向格勞恩學習作曲,因此,其創作風格完全是對老師的模仿。除了歌劇,格勞恩的宗教音樂創作也是巴洛克時期的代表,如1755年寫的受難曲《耶酥之死》(Der Tod Jesu)至今仍在上演。當然,作為宮廷作曲家格勞恩的主要任務還是為皇室服務,鑒于腓特烈大帝對長笛的鐘愛,格勞恩還寫過不少三重奏鳴曲,以供皇帝選用。
小提琴家、作曲家弗蘭茨·本達也曾是腓特烈大帝宮廷的座上客。本達出生于波西米亞的一個音樂世家,是歐洲當時首屈一指的小提琴演奏家之一,也是所謂德國學派的鼻祖。他十八歲回到布拉格隨格勞恩學習過一段時間,不久到華沙工作。1732年,他來到還是王儲的腓特烈大帝的宮廷供職,深得嘉許,后來成為腓特烈大帝的音樂會主管,在此后的四十多年服務期間有案可查他演奏過超過五萬場音樂會,可謂盡職盡力。
腓特烈大帝的博學與虔誠,僅僅從他的語言天賦就可見一斑。除了德語之外,他還能熟練地說法語(說得甚至比母語還要好)、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意大利語,他還懂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希伯來語,這在巴洛克時期的歐洲帝王中是非常少見的。從童年起,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腓特烈大帝就對法國文化極為崇尚。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像羅馬皇帝奧里略(Marcus Aurelius)那樣的哲學家皇帝,又十分贊同法國的啟蒙運動思想。
在音樂方面,腓特烈大帝是一位水平相當高的長笛演奏家,還是作曲家和腳本作家。從現存的評論來看,腓特烈大帝的演奏水平很高,擅長協奏曲,尤其是慢板樂章。他還作曲,從七年戰爭之前他寫的一些作品來看,無論是長笛奏鳴曲還是長笛協奏曲,腓特烈大帝的模仿對象大多是匡茨,有時也借鑒塔蒂尼或者維瓦爾第。大帝還有一個嗜好就是寫歌劇腳本,特別是為格勞恩的創作提供素材。1755年,他完成了歌劇腳本《蒙特祖瑪》(Montezuma),使用的是法文,然后由宮廷詩人塔利亞祖齊(Giampietro Tagliazucchi)翻譯成意大利語供格勞恩使用。蒙特祖瑪是墨西哥土著阿茲特克王國的國王,后來被西班牙的赫納·柯蒂斯征服,歌劇就是根據這段史實而創作的。
晚年的腓特烈大帝非常孤獨,他沒有孩子,無法享受天倫之樂,只好終日和自己的愛犬待在一起,甚至在交代后事的時候還提出就安葬在愛犬的附近。不過,他的繼承人、侄子威廉二世卻沒有滿足他的愿望而是把他埋葬在教堂的地下墓穴。直到1991年(逝世二百O五周年)他才最終遷葬無憂宮,安息在那曾經充滿了音樂、歡樂的忘記憂慮的宮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