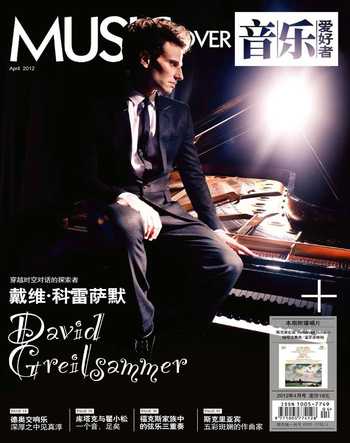庫塔克與瞿小松:一個音,足矣
方小貓


庫塔克:萬象化簡
在當代西方樂壇,吉爾吉·庫塔克(Gy?rgy Kurtág,1926- )以作曲方式“極為苛刻的樸素”而聞名。材料只有一兩個音,編制只有一兩件樂器,時長只有幾分鐘——這在他的作品中十分常見。
生活中庫塔克的行事作風與音樂上相同,寡言少語,極少公開發表言論。因此,庫塔克總讓人覺得神秘,有西方媒體認為他不茍言笑,“過著僧侶一般隱遁的生活”。
可事實并非如此。“庫塔克的創作來源于生活的各個方面,他并沒有活在象牙塔里。他從自然現象、色彩、各種事件、各種聲音、文學、建筑、各時期和風格的音樂中汲取材料,并以此回應世人,回應各種表達,回應一個微笑(看到一張約翰·凱奇微笑的照片后結束了他的一段低潮期),回應一個聲調——回應生命。”他的作品常常是獻給某位親友或逝去的故人,又或是描述平凡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甚至一個不為外人所知的秘密。而且庫塔克的語言能力極強,他能夠自如運用羅馬尼亞語、匈牙利語、德語、法語、英語、俄語、古希臘語。
寡言少語,是他面對生命的一種深沉的態度。一個音,或者說,樸素地作曲,極為簡單的材料,但要求作曲家必須具備敏銳洞察和準確操作的能力,否則自我難以表達,他者無法體驗。
從1973年創作至今的鋼琴曲集《游戲》(Játékok)已出版了八卷,創作仍在繼續,其中有一首小曲《無窮動》(Perpetuum mobile),原本是一種器樂曲體裁,以大量音符、連續快速節奏的跑動為特點,常用于小提琴和鋼琴;庫塔克這首《無窮動》中沒有音符和節奏,雙手交替刮奏,升降記號表示黑鍵,還原記號回到白鍵,音域從中央C開始,隨波浪線的幅度變化。
全曲不過一分鐘,技法簡單到沒有學過鋼琴的人也能演奏。簡單的波浪線取代原本復雜的音符和節奏,演奏者自身雙手的交替運動和層層推動的音幅動勢對“無窮動”作出極為貼切的嶄新詮釋。
如此敏銳與準確的把握來自于對生活踏實、深切的體認,然而將所體驗到的各種事物準確地化為只字片語的音響實非易事——看似一蹴而就的極簡風格,庫塔克為此付出艱難的代價。
他生長在羅馬尼亞與匈牙利交界處的小鎮,1946年移居布達佩斯,二十三歲時取得匈牙利國籍并進入李斯特音樂學院,主修鋼琴、室內樂和作曲。此時匈牙利開始陷入社會重大動蕩之中,文化藝術為政治所屈服,庫塔克一度被卷入政治崇拜而不自知,創作了一些“頌歌”式的作品。1957年他獲得赴巴黎參加米約、梅西安音樂課程的機會,同時也擔任藝術心理學家瑪麗安娜·斯坦的助手及學生。身在法國的他為國內的政治動亂深感痛苦,對自己的政治信仰產生懷疑,進而對音樂創作、人生和價值觀感到迷茫,情緒一度低落,體重狂跌,創作停滯不前。此時瑪麗安娜·斯坦教授給予了庫塔克巨大的幫助,面對庫塔克在巴黎唯一的作品——一部宏大的鋼琴曲時,教授建議,如果給自己一些簡單的音樂任務,比如探索兩個音符之間的多種聯系方式,他的作曲音響將得到有效開發。同時她也對庫塔克進行藝術心理治療,方法就是讓庫塔克用火柴棍拼圖案。除此之外,庫塔克反復閱讀著卡夫卡的《變形記》。
1958年回到布達佩斯之時,庫塔克已將自己的身心洗刷得干干凈凈,于是三十二歲的庫塔克創作了他的第一首編號作品:《弦樂四重奏》(String Quartet,Op.1),獻給瑪麗安娜·斯坦,內容是關于一只蟑螂在尋找光明。斯坦教授探索兩個音關系的建議讓庫塔克學會追問每一個音存在的理由和意義,他將曾經音樂語言中的繁雜和空泛一一剔除,并意識到,一個音,能夠完成更加直接和有效的表達。從此,庫塔克在音樂上確立自己的風格,獨來獨往,只做自己。
而當年那本《變形記》猶如當頭一棒讓卷入政治崇拜的庫塔克從痛苦中抽離,從那時起,人與社會的關系,人在社會中的不同生存狀態和體驗就成為庫塔克頻繁探索的主題。基于此題材創作的作品第十七號女高音與室內樂《來自逝去女孩特魯莎娃的聲音》(Messages of the Late R. V. Troussova)以干冷的音色、節制的音符、清晰的軌跡、碎裂的節奏為主人公——特魯莎娃造型,一經上演便轟動樂壇,為庫塔克帶來國際性的聲譽,在此之前,他是作為優秀的鋼琴家和室內樂教師而不是作曲家受到矚目。有評論認為作品反映了他與那個陷入瘋狂時期的匈牙利的關系,女主角生活的遭遇和內心的掙扎正是庫塔克在十年紛亂歲月里的真實寫照。他本人卻對此緘默不語。
成名之后各種委約紛至沓來,庫塔克這類作品的創作速度出奇的慢,有些作品至今未完成。面對委約,他鮮有動力;而面對朋友的離世,面對孩子的成長,面對老師的九十歲生日,他卻可以佳作迭出。
1986年庫塔克從李斯特音樂學院教職退休,此后七年間這位蜚聲國際的“沉默者”在匈牙利行事低調,只開設數量相當有限的大師課,認真生活,認真創作,完成近二十部作品。1993年開始庫塔克攜鋼琴家夫人瑪塔·庫塔克(Márta Kurtág)依次在柏林、維也納、阿姆斯特丹、巴黎居住,擔任各大音樂組織的駐團(駐節)作曲家或音樂總監,夫婦二人曾舉辦過少許《游戲》鋼琴演奏會,除了工作和教學,不接受采訪,不發表言論。2002年起至今定居法國波爾多附近的小鎮。這二十年間庫塔克完成十六部作品,其中包括創作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以《石碑》(Stele,Op.33,獻給阿巴多與柏林愛樂)為代表的三部大型管弦樂。以此三部屈指可數的大型樂隊作品,古稀之年的他再度震撼樂壇,但隨后很快回歸到他鐘愛的僅有兩三件樂器的小型室內樂編制。
同為作曲家的摯友里蓋蒂(Gy?rgy Ligeti)說過,庫塔克的“內心令人驚奇地集中于微小、不起眼的事物”。2011年9月1日,瑞士Contrechamps室內樂團在日內瓦首演庫塔克的最新創作:小型室內樂《簡短的消息》(Brefs messages:for small ensemble,Op.47)。此時的庫塔克,八十五歲,作品總數已超過一百八十五部(編號作品與無編號作品總數)。
只要活著,庫塔克對人生的描繪就不會停止,用音樂表達,已成為本能。“對我而言,將一件平凡的事轉化為音樂,比轉化成語言更容易。”曾經的那一次猛醒,庫塔克建立起一種極強的自省和清醒意識,之后,他在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對人生保持著誠懇和篤定。靈魂的自由與獨立,釋放出強大的爆發力,他以一種自我而準確的方式,源源不斷地,將眼中的世間萬象化繁為簡,以簡作樂,寥寥數筆,直射人心。
瞿小松:簡中虛實
1990年香港實驗劇團“進念十二面體”受邀參加美國費城現代藝術機構“黃泉”(Yellow Spring)為時一個月的工作坊,劇團總監榮念曾先生邀瞿小松一同前往。在“黃泉”工作室里有一天瞿小松將自己的一部舞劇作品進行試驗,原作一開頭是一個D音的緩進緩出,一小節休止之后,再次出現。將磁帶速度放慢一倍、四倍、八倍之后,瞿小松不再能認出這是自己的作品,只聽到“某種不可名狀的白噪音,如同地震中的深深轟鳴”,極其緩慢極其微弱的出現,繼而同樣緩慢和微弱的遠去,隨后是一陣漫長的沉默,剛懷疑機器出了毛病,聲音又來了。這次特殊的經歷讓瞿小松領悟到一種寂靜,而聲音,是為寂靜而存在:“寂靜是根本的存在。聲音是短暫的,而寂靜是永久的,聲音從寂靜中誕生,又回歸寂靜。”
這之后他接受荷蘭新音樂團委約,開始創作室內樂《寂Ⅰ》“寂谷”,在大量的休止符中間,稀疏的音符顯得格外珍貴,讓人不由自主地去尋找一個音到另一個音的過程,以及它們之間的靜默。從1990年至1997年,《寂》系列不斷更新,分別是Ⅱ.“行云”,Ⅲ.“空山”,Ⅳ.“混沌”,Ⅴ.“破石”,Ⅵ.“流沙”,Ⅶ.“靜水”,編制有獨奏、小合奏、大型混合合奏的多種形式,音符節省,技法簡單,自然而精煉,以有限的音,造無限的靜,頗有中國水墨畫留白的意境。
可是,曾經瞿小松的音樂可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1968年十六歲的瞿小松下苗區插隊,在黔東南的山上當了整整四年的農民,他自得其樂,過得快活,從此心中打下大山的烙印。“山的氣質、山民的氣質,正是具體我這個人的氣質,粗樸、直接、強悍……本質的野性,不愿意循規蹈矩。”
1978年考入音樂學院后瞿小松正規地學習到各種西方音樂風格和技法,創作了一系列練習性質的作品,但極為西方的方式讓他有些無所適從,獨有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創作風格曾讓他著迷。大三開始,巴托克也無法令他滿足,骨子里那股野性逐漸凸顯,那種山的氣質、青春的張揚,反映在他的音樂中。入學到留校任教十年間的作品,從最初的小提琴獨奏《谷》(1978)、《大提琴無伴奏組曲》《弦樂交響曲》(1981),到《山之女》(室內樂版/管弦樂版1982)、《山與風土》(管弦樂1983)、《Mong Dong》(混和室內樂1984),以及多部電影配樂:《青春祭》(1984)、《獵場扎撒》、《盜馬賊》等(1985),再到《第一交響曲》(1986)、清唱劇《大劈棺》(1987),瞿小松的創作經過了一個清晰的由規范到自我、由基礎到純熟的成長歷程,并進一步趨向寫作大型作品。其中《Mong Dong》是他早期風格的代表。
受到云南滄源原始崖畫的啟發,瞿小松以男聲、短笛、打擊樂和弦樂的混合編制創作了《Mong Dong》,標題表達一種拼音式的發聲意境。在作品中他避免任何訓練有素的西方風格和專業音響,追求自然、民間的那種本真和粗樸,更為準確地講,他用聲音造出了一個原始而遙遠的世界。男聲以假聲和低音兩種方式演唱,假聲飄忽悠轉,類似民間山頭的吆喝,低音粗硬平實,回到樂音產生之初那種祭祀性的低唱;器樂在紛雜和單一的音色之間張弛,以野性的音響釋放出原古大自然的喧囂和沉靜。《Mong Dong》隨后成為動畫短片《牧童與蠻牛》的配樂,音樂與畫面相得益彰。
1989年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中藝術交流中心之邀,由美國亞洲文化基金會贊助,瞿小松赴美訪問。初到紐約,高樓林立的繁華讓他覺得自己像一只煩躁的籠中困獸。隨后,“黃泉”工作坊的經歷讓他突然明白,籠子不是紐約而是自己的心念,因為內心的繁雜是由于對世界無止境的欲求所生,這一點身在繁華之中的人們很難體會;而在寂靜之中,除了自己再無依靠,于是背向繁華學會面對自我內心。所以看似繁華世界不過一場虛空,而看似虛無之寂卻是存在之實。領悟到這一切之后,瞿小松在美國呆了十年,以極簡音樂探索寂靜,以極簡音樂凈化內心,并從儒、釋、道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著啟示。
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歌劇《俄狄浦斯之死》(1993-1994)。瞿小松認為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在被流放后,是另一段生命歷程的重新開始,作曲家根據自己的理解,自行創作劇本,探討了俄狄浦斯在流亡的二十年后,坦然接受命運,走向超脫、走向自由、走向智慧的過程。配合戲劇語言的需求,音樂高度的簡練和概括,大量留白,單獨的音符零星地出現,暗示人物內心的孤獨與深沉。在瞿小松筆下,俄狄浦斯在生命的最后走向禪宗的道路。
2000年瞿小松回國,隨即為臺灣現代舞團“云門舞集”創作了舞劇《行草》的音樂。經過了十年的探索,《行草》成功找到了在“黃泉”時體會到的那種感覺。全曲時長五十多分鐘,分為九段,僅用大提琴和三件打擊樂,音樂的句子感模糊,自有一套呼吸吐納,強調極慢、極簡、極靜,又有從容的流動與狂放的噴涌。音樂生于寂靜,又在寂靜中幻化成虛。
《行草》還體現出瞿小松多年來音樂創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對打擊樂的獨到運用。一直以來打擊樂都是瞿小松音樂中最頻繁使用的音色,即使在《寂》與《行草》這一類“靜”的作品中也常能聽見這種粗糙的、短促而突兀的爆發。這是他骨子里的野性使然。其實野性與寂靜原本也是相通,無非是自在自然的不同狀態而已。只不過現在的瞿小松化自然的靜為內心的凈,求悟以修心。
“五音令人耳聾,走到這一步,我不需要太多音了……到了《行草》,我的創作和人生都進入了一個很舒坦的境界,回看我的創作歷程,就像一次修行。”
他們……
庫塔克與瞿小松,走在極簡延伸出的兩端,除了從一個音中獲得啟示之外,他們的道路千差萬別。可是,扎根平凡,繪出世間萬象,若沒有超然的視角,怎能描繪得如此精妙?超然世外,追求精神靜悟,若沒有俗世的磨煉,哪得心中至禪?
是不同,也是同。
從《寂》開始,瞿小松認為當代西方作曲家已無法對他產生任何影響,甚至公開表示對現在西方學院派音樂感到失望和麻木,只有一人除外——庫塔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瞿小松短暫回國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了一次講座,演講的主題是庫塔克。1999年瞿小松觀看了庫塔克的公開排練,為了使樂手找到感覺,“七十多歲的老頭突然用手掐住了自己的脖子,喉嚨里擠出嘶聲,卻出不了腔……這位匈牙利老頭,有真話要說,用真心在寫。”回國后,瞿小松在個人文集和各類采訪中也曾多次提及:“在所有健在的作曲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庫塔克,他的實踐有些接近我的所為——以精簡的語言和精簡的方式創作。但精神上,我在自己的路上體悟……他的語言非常集中和精簡,只落真正要落的筆,并且你真正聽到音樂,不只是‘作曲,不只是‘設計,你聽到他對人類苦難的深沉關注。”
如有機會,他們應該早已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