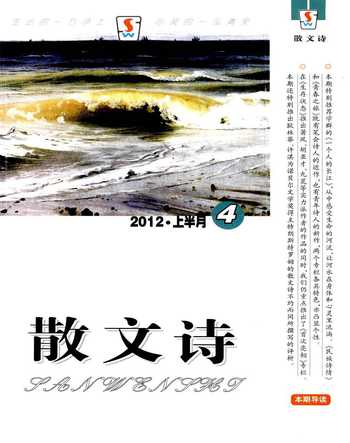對(duì)《一封信的回答》賞析
許淇
今年(2011年)10月,瑞典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授予瑞典8l歲的老詩(shī)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實(shí)至名歸,世界詩(shī)壇同聲贊譽(yù)。正如去年的得主——秘魯、西班牙作家巴爾加斯·略薩一樣。略薩是結(jié)構(gòu)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家,具有世界影響已久,得獎(jiǎng)后即到中國(guó)來訪問。特朗斯特羅姆也曾兩度來華,首次是在1985年,轉(zhuǎn)了北京胡同,登上八達(dá)嶺長(zhǎng)城,老詩(shī)人很高興。后一次是2001年,為《特朗斯特羅姆詩(shī)全集》的譯本首發(fā),在北大舉行朗誦和研討會(huì),然后赴昆明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畫廊和酒吧去。今天,他不可能像巴爾加斯·略薩那樣,獲獎(jiǎng)后來到企待著的中國(guó)詩(shī)人面前,他中風(fēng)癱瘓失語(yǔ)拄拐杖坐輪椅,若出國(guó)遠(yuǎn)游。非得依靠詩(shī)歌的翅膀了。
特朗斯特羅姆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新詩(shī)人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不僅有多年的中國(guó)譯家李笠、董繼平等,精通外語(yǔ)的詩(shī)人王家新、北島、于堅(jiān)等都和他有過或短或長(zhǎng)的交往。生活在國(guó)外的北島寫過回憶長(zhǎng)文,描繪了托馬斯居住的斯德哥爾摩附近小島上的藍(lán)房子,1985年第一次作客以后,曾多次去拜會(huì),有時(shí)還投宿在藍(lán)房子;1991年老詩(shī)人中風(fēng)以后,北島再次特地去探病,送去了巴赫的鋼琴協(xié)奏曲。托馬斯會(huì)彈鋼琴,自稱:“我感覺自己是一件幸運(yùn)或受難的樂器。”(見北島《時(shí)間的玫瑰》)
人們說:譯詩(shī)是不可能的。譯好譯成一首詩(shī),其難度猶如重新創(chuàng)造一顆行星。因?yàn)樵?shī)本身就是詩(shī)人將口語(yǔ)散文轉(zhuǎn)化為詩(shī)句,而譯詩(shī)又必須完成轉(zhuǎn)化的轉(zhuǎn)化,特別是漢語(yǔ)方塊字,讓它從固體化為液體,活潑起來,滾動(dòng)起來。用我們的白話文,不受古音韻格律的束縛,原本外國(guó)的無韻自由詩(shī),肯定會(huì)譯得更自由而等同于散文詩(shī)了。所以我學(xué)散文詩(shī),從修辭的角度。必須將提煉的意象轉(zhuǎn)化為詩(shī)的語(yǔ)言,特朗斯特羅姆的詩(shī)和散文詩(shī),其語(yǔ)言的再造能力,常常使我既驚訝又欽佩。他猶如小島上的狩獵者,“將靈感捕獲進(jìn)語(yǔ)言”,同樣是我一生的追求。
這次諾獎(jiǎng)的授獎(jiǎng)詞說,特朗斯特羅姆“通過凝煉、透徹的意象,為我們提供了通向現(xiàn)實(shí)的新途徑。”其詩(shī)歌的特點(diǎn)是“凝煉、透徹”,如何能做到?詩(shī)人曾透露說:“必須敢于割愛、刪減:如果必要,可放棄雄辯,做一個(gè)詩(shī)的禁欲者。”我以此檢查我的散文詩(shī)的弊病,便是總要“賦得”和“雄辯”一下,總要“縱欲”而不肯“禁欲”,不肯“舍棄”。書此以自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