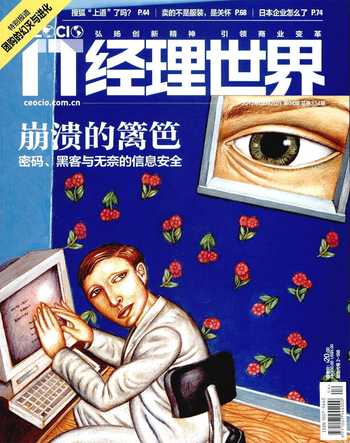生活流
胡泳
今天的Twitter和Facebook都可被稱為“生活流媒體”,這類媒體意義深遠(yuǎn),潛力不可限量。
在20世紀(jì)最后幾年產(chǎn)生的“新媒體”,相對(duì)于傳統(tǒng)媒體有一些明顯的不同。比如,新媒體可以讓人們根據(jù)自身的需求在任何時(shí)間、地點(diǎn)和設(shè)備上獲取內(nèi)容,并圍繞這些內(nèi)容彼此互動(dòng),參與創(chuàng)造和形成社區(qū)。另外一個(gè)重要特征是,新媒體在內(nèi)容創(chuàng)造、出版、分發(fā)和消費(fèi)上造就了“民主化”與“去中心化”。 或許對(duì)于新媒體的如上特性人們已耳熟能詳,然而新媒體從最早的論壇、博客發(fā)展到后來的SNS和微博,在形式上也不斷推陳出新。可能很少有人意識(shí)到,在21世紀(jì)第一個(gè)十年的后半葉,人類在媒體形式上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里程碑式的發(fā)展,它的意義深遠(yuǎn),潛力不可限量。 2006年9月,F(xiàn)acebook創(chuàng)始人扎克伯格開發(fā)出一種叫做News Feed的東西,這是一種能主動(dòng)把用戶主頁上的變動(dòng)向所有好友廣播的內(nèi)置功能。學(xué)生們再也不用把時(shí)間花在檢查朋友主頁的更新上了。現(xiàn)在他們只需登錄Facebook,然后就會(huì)看到News Feed:一個(gè)類似18世紀(jì)社交界新聞公報(bào)的頁面,上面列出所有好友的最新動(dòng)態(tài),全天不停更新。用扎克伯格的話來說,就像是“一股由生活中發(fā)生的點(diǎn)滴事件匯聚而成的涓涓細(xì)流”。 Facebook的用戶在扎克伯格剛開發(fā)這個(gè)功能時(shí),并不認(rèn)為自己需要經(jīng)常、實(shí)時(shí)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但當(dāng)自身處于這種無處不在的信息中時(shí),他們覺得十分有趣甚至流連忘返。這是什么原因呢?社會(huì)科學(xué)家給這種不間斷的網(wǎng)絡(luò)聯(lián)系起了一個(gè)名字,叫做“環(huán)境知覺”(Ambient Awareness)。每條小的更新本身是微不足道甚至十分平庸的。但若假以時(shí)日,當(dāng)它們匯集起來,這些小片段就漸漸結(jié)合成一幅細(xì)致得驚人的、描繪你朋友或家人生活的畫卷。 這種媒體形式的神奇之處在什么地方呢? 早在1991年,耶魯教授大衛(wèi)?蓋勒特(David Gelernter)就預(yù)見說,未來的計(jì)算,將圍繞“生活流”(lifestream)來組織。蓋勒特認(rèn)為,在上世紀(jì)90年代早期,文檔系統(tǒng)就已然千瘡百孔臃腫不堪。人們的桌面遍布圖標(biāo),以至于當(dāng)你打開電腦,有時(shí)甚至?xí)霈F(xiàn)一個(gè)彈窗,詢問你是否可以清理不常使用的圖標(biāo)。 在這種復(fù)雜的局面之上,90年代中期之后,很快又出現(xiàn)了更加復(fù)雜的萬維網(wǎng)。萬維網(wǎng)經(jīng)由超鏈接連為一體,但除了Google,沒人喜歡它的組織方式。 蓋勒特設(shè)想有一種嶄新的用以整理我們數(shù)字化映射世界的方式。生活流是組織數(shù)字化內(nèi)容的一種方法,這些內(nèi)容可以是照片、郵件、網(wǎng)絡(luò)鏈接、文件、音樂,把它們按時(shí)間順序來呈現(xiàn)。本質(zhì)上,一條時(shí)間軸(timeline)既伸展到過去,又延展到未來(比如約會(huì)日程等)。 所以,今天的Twitter和Facebook都可被稱為“生活流媒體”。在Facebook,你給朋友的留言、你按“贊”的網(wǎng)址鏈接、你投過票的民調(diào)、你和誰變成新朋友等動(dòng)態(tài)信息,都會(huì)“自動(dòng)發(fā)布”到個(gè)人涂鴉墻上,你的朋友也都能看到你最近干了什么。 Twitter的信息流也是如此。在這條信息長流之中,匯集了好玩的點(diǎn)子、稀奇的思緒、紛雜的內(nèi)容和用戶的觀點(diǎn)。 蓋勒特認(rèn)為,生活流是一種更加直觀有用的組織我們數(shù)字化生活的方法,不僅過去和未來都可以在我們的屏幕上呈現(xiàn),更是因?yàn)槠聊坏闹行氖恰艾F(xiàn)在”——而“現(xiàn)在”是互聯(lián)網(wǎng)真正在乎的東西。 蓋勒特預(yù)測說,最終,建立在生活流基礎(chǔ)上的商業(yè)模式會(huì)統(tǒng)治互聯(lián)網(wǎng)。世界上所有數(shù)據(jù)將會(huì)被展現(xiàn)為“世界流”(worldstream),某些是公共的,但大部分是專有的,只對(duì)被批準(zhǔn)的用戶開放。網(wǎng)絡(luò)瀏覽器將被生活流瀏覽器所替代。用戶將會(huì)習(xí)慣追蹤和操控以流的形式出現(xiàn)的數(shù)字化內(nèi)容,而不再是從文件系統(tǒng)中讀取文件。生活流會(huì)變成他們生活故事展開的一種鏡像。 生活流將是可視化的。當(dāng)我聚焦于自己的東西時(shí),我會(huì)獲得世界流的一個(gè)子流。當(dāng)我在生活流當(dāng)中搜索某人時(shí),所有同這個(gè)人不相關(guān)的又允許我看到的信息都會(huì)消失,我對(duì)世界流做了一個(gè)減法。因?yàn)閭€(gè)人向世界流中添加內(nèi)容的速度遠(yuǎn)低于世界流的流動(dòng)速度,這意味著滔滔洪水化為涓涓細(xì)流,內(nèi)容成為可管理的。 這樣的方式操作簡單,與身體本能若合符節(jié),使人們更加理解互聯(lián)網(wǎng);互聯(lián)網(wǎng)也因此支持了自身最重要的功用,那就是:及時(shí)展現(xiàn)相關(guān)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