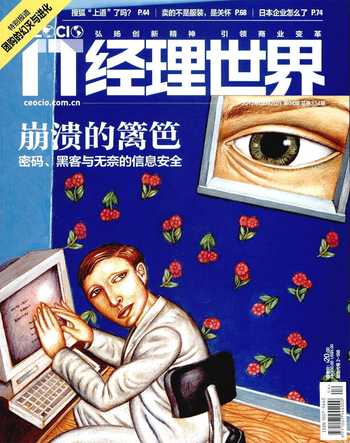日本式管理的生命力
鄭悅

記者:最近日本企業(yè)業(yè)績不佳,奧林巴斯等爆出財務造假的丑聞,很多人開始對上世紀80年代在全世界風靡一時的日本式管理質疑。在您看來日本式管理的內涵到底是什么?它的生命力究竟如何?有沒有經歷變化?
楊杜:日本式管理的本質沒有發(fā)生變化。我認為日本式管理有八個特點值得我們關注。1. 日本企業(yè)高層并不是簡單的通過決策,而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溝通,這也造成了日企的會議特別多,像董事會、專務會、常務會、社長會、連鎖店長會、業(yè)績會等等不一而足。經過反復溝通之后,大家相互理解、形成共識。2. 中層管理者有強大的影響力,事情往往都是由中層主動提出,上級認可,下級執(zhí)行的方式來進行。3. 重視企業(yè)理念、文化和價值觀,這與美國企業(yè)強調制度、規(guī)則形成對比。4. 人脈等各種非正式組織因素起很大的作用。5. 講究上下級秩序。比如在辦公室布局上,領導坐在窗邊,員工在中間,大家互相監(jiān)督,也方便相互之間的溝通。6. 采用工作輪換制度,讓每個員工對整個組織都有所了解,溝通起來也方便;同時人員流動也可以釋放機會,一定程度上化解組織僵化的傾向。7. 對人和事都采取長期考核的方式,對于一時的差錯,會采用集體幫助改正的方式,而不是一棒子打死。從這一點,也能看出奧林巴斯集體造假的原因,他們的初衷在于期待更長遠的發(fā)展。8. 在具體的業(yè)務實踐上多采用小團隊制,注重精細管理,不斷改進和優(yōu)化。
另外,大家比較熟悉的日本式管理 “三大神器”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年功序列、終身雇傭制和企業(yè)內工會制度。盡管這些年出現(xiàn)了勞務派遣等用工形式,但核心員工依然采用終身雇傭制。員工基本上還是按照經驗和在企業(yè)服務的年份,得到地位和職位的提升。盡管近年來按照能力主義開始實行工資的差別化,但總體來講,員工的工資分配仍然以保障生活為準則,因此彼此的差別不是很大。與歐洲行業(yè)工會常組織罷工不同,日本的企業(yè)內工會與所在企業(yè)交涉中更多的是充當調節(jié)和內部溝通的職能,這樣有利于尋找到內部的妥協(xié)點,也使得日本企業(yè)的勞資關系矛盾沒有那么尖銳。
記者:日本式管理上世紀80年代在全世界受到熱議和追捧,包括美國、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的很多企業(yè)都普遍有向日本企業(yè)學習的經歷。今天,正像您剛才說到的,日本式管理依然在日本企業(yè)中發(fā)揮著作用。但是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美國式創(chuàng)新”和“中國式管理”,這是否是因為隨著日本經濟持續(xù)低迷,日本企業(yè)管理的光環(huán)效應消失的緣故?日本式管理與日本經濟的關聯(lián)性是怎樣的?
楊杜:對,人們的關注往往是以結果為導向的。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式創(chuàng)新、日本式管理、中國式管理輪番占據(jù)人們關注度的首位。日本式管理目前不受關注的原因是日本經濟低迷、企業(yè)業(yè)績不佳。
在我看來,如果日本在三個方面不進行大的變革,日本企業(yè)將無法擺脫這種困境。第一個方面就是整體經濟發(fā)展和企業(yè)競爭戰(zhàn)略的調整。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使得日本式企業(yè)管理無法發(fā)揮出其作用。這種追求成長的戰(zhàn)略在遇到市場萎縮時,既有的市場及其空間消失了,如果企業(yè)不轉型就無路可去。第二個是國際化。日本企業(yè)管理的方法在基層管理層面上卓有成效,這一點在全球企業(yè)向日企學習的風潮中已得到例證。從根本上講,這種小團隊的機制——在群體中采用表揚和溝通等方式,從本質上來講符合人性。但在日企高層中這種小團隊的特質很容易形成對外籍高管的排斥和不信任,這也是諸多歐美籍高管在日企中感到水土不服的重要原因。如何在國際化的道路上既體現(xiàn)日企“細水長流”和穩(wěn)扎穩(wěn)打的特性,又能有開放的心態(tài)迎接更多外國人的加入,這是日本企業(yè)必須解決的課題。第三,由于日本企業(yè)在戰(zhàn)略上習慣微調、在生產技術上習慣琢磨“造物技藝”,這種注重細節(jié)的工匠文化有自己的優(yōu)勢,但也會導致跳躍性的創(chuàng)意思維的缺乏。很多日本企業(yè)習慣了工業(yè)經濟時代直線延展性的思維,很難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特征,所以它們很難實現(xiàn)突破。但這個結論也不是鐵板一塊,在動漫領域,日本人獨有的靈性和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令世人矚目。如果日本企業(yè)在技術創(chuàng)新方面都能有這樣的靈性和想象力,那么肯定會迅速打造自己的優(yōu)勢。如果在這三點上,日本能出現(xiàn)重大變革,那么日本企業(yè)也將走出目前的困境。
記者:1989年以來,日本經濟持續(xù)低迷,被普遍認為是日本“失去的20年”。不過,《紐約時報》也指出,在這個失去的期間內,日本很多方面依然有很好的表現(xiàn):平均壽命增長4.2年;互聯(lián)網基礎設施建設位居世界前沿;日元匯率堅挺,甚至對歷來被視為最堅挺貨幣的瑞郎也走高;失業(yè)率僅4.2%;經常賬戶盈余增長3倍,等等。您如何看待這些現(xiàn)象?如何看待日本經濟的前景?
楊杜:這些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與日本經濟內部存在雙重結構有關。日本整個經濟分裂為兩大領域:一個是面向出口生產的部門(外向型經濟),主要包括像索尼、豐田這樣的大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很早就面向世界生產,參與國際競爭,熟諳市場經濟規(guī)則。這部分企業(yè)的生產率很高,甚至高于美國的大企業(yè)。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日本的經濟情況不好,企業(yè)生產率有所下降,但是許多大企業(yè)仍有能力與美國大企業(yè)一爭高下,其競爭力是相當客觀的。對于這部分企業(yè),政府沒有實行嚴格的管制和保護,沒有給予補貼。與此相對應的另一部門是面向國內生產的部門,主要是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比如,糧食加工、服裝制造、醫(yī)療服務和建筑業(yè)等。對于這部分企業(yè),日本政府進行了嚴格的管制和保護,并給予大量直接或間接的補貼。這部分企業(yè)數(shù)量極大,占日本GDP的85%,占日本勞動力就業(yè)人數(shù)的90%。由于受到政府的嚴格管制和保護,這部分企業(yè)的生產率很低,大約僅為美國企業(yè)的60%,根本談不上國際競爭力。
而且這種“雙重結構”不僅在日本經濟中存在,也存在于日本社會中。因此日本個人、家庭和企業(yè)的命運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這大概也是奧林巴斯企業(yè)為何會出現(xiàn)高層集體造假的原因之一。
在工業(yè)時代,日本產業(yè)曾經歷無限擴張的階段,而且這種擴張是超出其自身資源規(guī)模的。現(xiàn)在,日本經濟即使是衰退期,其體量依然相當可觀。另外,日本國民素質高、勤勞、社會結構穩(wěn)定等因素,使得這個國家的經濟依然富有活力和潛力,只是沒有之前那樣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