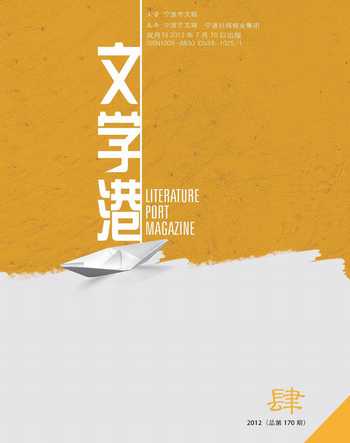故鄉的匠人
王樂天
剃頭匠
稍稍上了年紀的人,都會對鄉村那些走街串巷者的吆喝聲有著深深的記憶,繚繞著炊煙的鄉村還是一片靜謐時,一聲或高亢、或婉轉、或悠長的吆喝,隨即引來了全村的雞鳴犬吠,清脆朗朗的吆喝聲回蕩在大街小巷上,不絕于耳。“剃頭嘍……理發嘍……”剃頭匠的吆喝聲更會引起全村老小的注意。
六七十年代,在農村,常有挑著剃頭擔給人理發的民間手藝人,至于從哪朝哪代開始出現這種剃頭擔那是很難準確考證,要說剃頭擔有漫長的歷史是無可置疑的。靠吃這碗飯的手藝人大多數是祖傳的,他們手藝精湛,且對修眉、掏耳、修腳等也有一手絕活。
那時,剃頭匠沒有固定的鋪面,是在戶外作業的——夏天選陰涼的樹蔭下,冬天則找背風的旮旯。而工作的地點每天也在不斷地變化著。天一亮,剃頭匠就得早早地起床,先整理好剃頭擔,然后挑著擔子開始走街串巷。他們的工具往往比較簡單,一頭擔著燒熱水的爐子和小鍋,另一頭則是盆架和凳子,架子搭著手巾和擦剃刀的長方形帆布,上面放置一個臉盆,臉盆中擺放著木盒子,盒子里則擱著刮刀、推子、剪刀、梳子及香皂之類,這就是一個設備齊全的剃頭攤兒。師傅剛把擔子往曬谷場上或大樹下一放,就會圍滿來剃頭或湊熱鬧的老老少少。
每年的臘月是剃頭匠最忙碌的時候,生意格外的火爆。因為在農村有一種不成文的習俗,正月里不能剃頭,否則會容易招癩。快到過年時,剃個頭、穿新衣服和家中置辦年貨、貼春聯一樣重要,都成了過年的風俗。那些日子,幾乎每一位剃頭匠都會從早忙到晚,一個曬谷場上往往會擺上好幾副剃頭擔,洗頭的熱水要用上一個大鍋才能解決,有時要用兩三天的時間才能剃完全村人的頭。
要說剃頭,小孩子比較好剃,無需刮臉,省工省時。只見剃頭匠利索地將家當取出,“坐好坐好。”站在小孩子身后,將那塊沾滿發屑的圍布凌空一抖,兜手一轉,圍住孩子的前半身,在頸后系緊帶子,頓時嚴絲合縫,一根頭發茬都漏不進去。之后,一只手用力摁住小孩的頭,不讓他動來動去,另一只手拿推子推,三下五除二,就很快剃好了。接著大喊一聲:“下一個!”大人們則麻煩得多,除理發外,還要修臉刮胡子。先得用熱毛巾在長滿胡子的部位敷上幾分鐘,再擦上肥皂,待胡子完全變軟了以后,才在涂滿肥皂沫的腮幫上下手慢慢地刮。那時沒有電動剃須刀,用的是剃刀,剃頭匠將剃刀的刀口放在一塊長約50厘米、寬約10厘米的粗布(俗稱鐾刀布)上一邊蕩動,一邊用手指去試刀刃鋒利的程度,直到自己滿意,才開始為客人剃胡須。胡子多的人,往往要蕩上多次的刀,才能完成。在剃頭的過程中,剃頭匠往往邊剃頭邊同理發人拉起家常。因為剃頭匠經常走街串巷,見多識廣,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雞毛蒜皮,無所不聊,他們會把自己所耳聞目睹的新鮮事一股腦兒講出來,來打發漫長的剃頭時間。
論當時的發型,則是非常簡單,也不過是光頭、平頭、鍋鏟頭幾種而已。最神氣的當數男人們的三七分頭,油亮油亮的。愛美的姑娘們更要利用過年這一難得的時機,好好將自己打扮一番,她們大多數留齊耳短發,還有的留著一條烏黑發亮的大辮子。為了更洋氣,姑娘們往往要求前芽曲卷,剃頭匠就拿著筷子般粗的釬子往爐火中插下去,適當溫度拔出,前芽往上一卷抽出即可,這種發型往往能保持很長的時間,如同現在的燙發用啫喱膏定型一樣的功效。最有意思的是剃光頭手藝,那是真正考驗師傅的技術。先是用溫水洗頭,將頭發浸泡至軟,而后手執剃刀,從前至后,發叢中立即呈現出一條分界線,接著逐漸向兩邊擴展,直至剃光變成一只“燈泡”為止,而剃頭的人則要沉住氣,耐心地坐在凳子上,一動不動,任憑師傅在頭上不停地修整,生怕在上面劃破一個口子。
如今,理發行業得到迅速的發展,剃頭擔基本上銷聲匿跡了。即使在農村,也是難覓其蹤,早已被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的理發店、美發廳所替代。這些登堂入室的現代發廊,室內設施齊全,一點也看不出當年剃頭擔的痕跡,各種新潮的發型層出不窮。發廊的玻璃門上貼滿了燙、吹、拉、焗等字樣,更有不少發廊引進了洗耳、洗眼、泰式按摩、韓式松骨等舶來品,吸引著過往的客人。同時,在各地也出現了許多連鎖的美發機構,只要肯花上點錢,就可以到美發廳里舒服地享受美發休閑一條龍配套服務。
打鐵匠
現在無論居住在城市或鄉村,已經很難再看到打鐵匠的身影了。社會日趨進步,科技水平日新月異,轟隆隆的工廠取代了原來的手工業者,過去備受人們歡迎的打鐵匠已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但回憶起打鐵匠和他們所打制的鐵器來,依然親切而熟悉,恍如昨日。
以前在農村,教育沒有像現在那么的普及,能讀到高中已是相當的不易,考上大學更顯得鳳毛麟角,大多數孩子在上完中學后就輟學了。于是,家長開始琢磨著給孩子們學一門手藝,好歹將來靠手藝謀個出路。當時在家鄉就有一種“家有萬貫,不如武藝(手藝)隨身”的說法。一個人一旦有了某種手藝,就具備了一種養家糊口的本領,也意味著今后再也不會吃苦受窮。因此,手藝被人們認為是人生中最寶貴的東西。當時在農村就有泥水匠、油漆匠、木匠、石匠、打鐵匠等各類傳統手工匠。在我記憶中印象最深還是打鐵匠,因為在我老家的附近,就有好幾家打鐵鋪。它們總是顯得簡陋,擺設簡單,打鐵的火爐是用磚砌成的,1米見方,底下帶箅子,煙囪像個倒扣的大漏斗,邊上架起一個風箱(亦稱風匣),墻上往往掛滿了已打制好的鋤頭、火鏟、鐮刀、菜刀等鐵制成品,吸引著來往的行人,而每天會時常聽到叮叮當當的敲打聲。
可是,打鐵不光是一項技術,更是一個重苦力活。如果身體不結實,基本功不扎實,是根本掄不動那幾十斤重的大鐵錘,也不可能讓大錘在鐵礅上叮當一整天的,更不用說長年累月這樣叮當下去。因此,鐵匠師傅收拜師學藝的徒弟時,與其他手藝師傅相比,要求更加嚴格苛刻,不光要看人品,而且還要看是否具備了健壯的身體和堅韌的毅力。
打鐵匠首先要練打鐵的本領和拉風箱的功夫。拉風箱要學會邊拉邊察看火候,隨著風箱“呼啦”、“呼啦”的聲響,爐膛中橘紅色的火焰頓時會“呲呲”地向外噴射,待鐵料冒出鋼花時,就用火鉗快速夾至鐵礅上。打鐵要求三人配合默契,分工協作。一位鐵匠師傅往往帶著兩個徒弟,一個拉風箱,另一個掄大錘。師傅左手握長柄鉗,夾住發紅的鐵料,放在鐵礅上,右手握把小錘,輕打輕落,引導徒弟敲打。掄大錘的緊跟師傅的“錘跡”,一錘下去,火星飛濺。師傅一邊翻,一邊打,聲音叮叮當當,極富節奏感。由于在打鐵店里,熊熊爐火一直不停地燃燒著,往往溫度很高,即使在寒冷的冬天,打鐵的師傅也常常赤膊著上身。他們先按照顧客的要求打成器具的毛坯形狀,待鐵料冷卻了又要繼續加熱,如此反復直至一件鐵料成形,然后馬上投入水槽內進行“淬火”,以增強它的硬度和強度。那“淬火”的情景很好看,只聽炙熱的鐵件到了冰冷的水里就會發出撕帛般的非常美妙的聲音,隨之一縷白煙騰空而起,這時,徒弟們會隨著水霧的升騰而歡呼雀躍。而對此,司空見慣的師傅那黝黑的臉上只是舒展幾條皺紋,露出一絲微笑,哪怕是一閃即逝,卻也在為自己精心創作的一件件作品的誕生而感到欣慰。
老鐵匠給徒弟們傳授的真經就是“淬火”。常言說:“好鋼要用在刀刃上”。為了使所打制的鐵器更加堅韌鋒利,“淬火”顯得特別重要,這是打鐵中一道必做的工序,也是最重要的一環,同時還是一個難度大、技術性極強的活。特別是如何掌握“淬火”的火候,是打鐵中最為關鍵的,因為這將直接關系成品的質量以及銷路與信譽。像張小泉的剪刀、王麻子的菜刀能成為知名品牌享譽至今,原因就是他們會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使之不但鋒利且經久耐用、好使。
記得小時候,我們所使用的鐵器差不多有一半是本地的鐵匠所鍛造的。而現在,早已改成了用機器進行批量生產了,這些鐵器在商店或超市里都可以隨時買得到,雖然沒有打鐵匠打造得耐用,但看上去卻非常美觀,因此人們也都喜歡用它們,這就讓打鐵匠的生意越來越清淡了。為了能使自己得以生存和發展,他們不得不開始拓寬路子,除了打造常用農具以外,也開始利用現代的機器技術做起了鐵大門、鐵架子車之類的大型鐵活,甚至于一些工業件來。
隨著機械制造業的飛速發展,打鐵業已經由興轉衰。曾經家家必備的鐵制品已漸漸地被不銹鋼、塑料制品等所替代,“叮叮當當”的打鐵聲也逐漸在人們的生活中遠去。在經濟大潮的沖擊下,能堅守著那塊祖傳手藝活陣地的鐵匠是越來越少了,而一些老鐵匠由于年齡的增長也慢慢地淡出了打鐵的行列。
磨刀匠
肩扛一張長木凳,吆喝一聲聲:“磨剪子嘞……戧菜刀……”這個日漸遠逝的行當是那樣的熟悉。如今卻是難覓其蹤了。
過去,磨刀匠常常挑著擔子,提起嗓子,一路走街串巷。這擔子輕便好用,一頭是一只修理的工具箱,裝有錘子、搶子等工具,另一頭則是一張特別的木板凳,凳面一端固定著砂輪盤,一端裝有水磨石,凳面中間為作業座位,凳的下端設有屜柜,內放出門用的雨傘、干糧、茶水等,這就是隨身攜帶的全部“家當”。平時,磨刀匠走街串巷,哪里有活,就會在哪里扎下根來。他們沒有固定的地方,來到一個地方,生意好便多待上幾天,生意差就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招攬。
那時候,人們生活并不寬裕,很多生銹或用鈍的剪刀、鐮刀和菜刀都舍不得扔掉,就靠這些不斷流動著、上門服務的磨刀匠重新磨回以前的鋒利。
每當磨刀匠高亢悠長的吆喝聲一飄進村子,就會有很多家庭主婦熱情地將他們招呼上門,并忙不迭從家中搬出一大沓舊刀來:有鈍得不能切的菜刀,有生銹已久的鐮刀、剪刀,也有砍柴的柴刀甚至于鉸刀等。而農忙季節往往是磨刀匠職業的旺季。在這個季節里,農村磨得最多的非鐮刀莫屬。鐮刀是人們收割季節的主要工具,鐮刀鋒利,收割就會特別快,否則,收割時就很費勁。
磨刀看似簡單,其實也是一項技術性強的活兒,刀磨得薄了容易卷,厚了則切不了東西。在我的記憶中,常來家鄉磨刀的師傅是一位40歲開外的中年男子,憑祖傳的一身手藝來養家糊口。由于常年走南闖北,歷經風霜,臉膛總是黑黑的,整天戴著一頂草帽,因為這位磨刀匠手藝嫻熟,價格公道,服務熱情,因此深受鄉親們的歡迎。
多年來的磨刀生活讓他干起這一切來早已是駕輕就熟。干活時,他總是顯得不慌不忙,到了人家的門口,先拎下工具包,擺好板凳,接過顧客遞過來的舊刀,細心地審視后,才開始坐在板凳上進行作業。他用那雙粗糙而布滿老繭的手,捏著舊刀在磨刀石上來回“嘶嘶”地移動,時不時騰出一只手輕輕地在磨刀石上灑點水,一會兒看看刀鋒,一會兒調整一下磨刀手勢,那刀刃部就慢慢變亮。接著,他又將刀對準固定在板凳上的砂輪盤,伴隨著飛濺出的一串串火星,一把斷了頭的剪子終于鋒利了。完工后,磨刀匠先用手輕輕觸摸一下刀刃,檢測其是否鋒利,然后瞇起眼睛,抽出座位下的抹布擦干水,并在一沓碎布上“喀嚓喀嚓”試剪幾下,或用已磨好的菜刀在砧板上切上幾刀,直至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才把刀子還給人家。就這樣,一把既銹又鈍的刀,到了他的手里,經打平、去銹、磨礪等四五道工序,立刻變得嶄新鋒利。
那時,磨刀匠干活時的一招一式和各式特色工具總能吸引孩子們目光,他們總對磨刀匠充滿著好奇和崇拜,因為一把舊刀在磨刀匠手里只要一會兒就變得油光锃亮,而且鋒利無比。由于磨刀需要一定的時間,是一件比較耗時和需要耐力的活兒,有時在一戶人家就得作業上半天的功夫。累了,磨刀匠也會停下來歇息一下,與圍在一邊看熱鬧的人們聊天。他總是喜歡把自己所知道的新聞、故事講給大家聽。由于他經常走街串巷,見多識廣,加上講話幽默,常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講者開心,聽者愉悅,使得氣氛更加融洽。當然,有時也會遇到一些斤斤計較的人,老是同他討價還價磨刀的價錢。對于這些人,他總是回答:“你自己看著辦,能給多少就給多少。”顯得格外大方。
現在,磨刀匠這個行業已經逐步淡出了人們的生活視野。在這個物質豐足的年代,刀用舊了,人們就會慷慨地把它棄掉,再去添置一把新的。雖然時過境遷,但兒時磨刀匠那抑揚頓挫、韻味悠長的吆喝聲和磨刀時的一情一景總讓人充滿著懷舊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