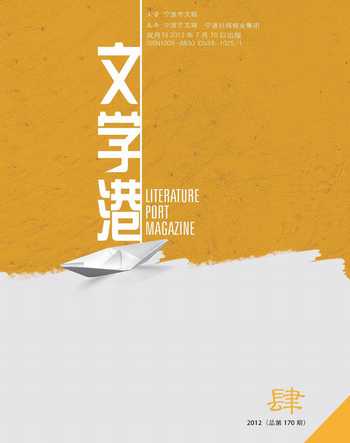百姓細事柴當先
鄭陸
記得幼時叔伯異爨,我家分到一個“缸灶”——矮腳的缸靠底部開個方口叫“缸灶洞”來添柴點火,上面放個鍋便可燒火作飯。燒松枝(我們叫“松毛”)最方便,一點就著,火舌會“火火”地叫,好像是笑聲,大人說火“笑”了,會有客人臨門。陰雨天氣,濕柴點火可麻煩了,用根竹管筒吹風助燃,好不容易點著了,嗆人的煙滿屋都是,熏得家人眼睛紅紅的,淚流不止。
幾年籌措,我家終于請了泥水師傅來打“大灶”。灶臺齊腰高,并排兩只尺四鍋,中間埋個鐵湯罐,利用余熱,飯菜煮熟,湯罐里的水也沸了。灶火洞對出豎起塊長條石擋住煨燼,便是“火缸”。柴草余燼里埋只小甕,人們叫“焐粥甏”,可以焐肉骨頭黃豆,那時沒有高壓鍋,只有焐粥甏里焐出的骨頭才嚼得碎,現今面市的悶燒鍋與它的原理差不多。草木灰積多了,便有農民收了去,用河泥船裝得滿滿的,說是去給西瓜地、楊梅樹施肥。
灶大了,但燒的柴成了問題,母親須起大早天才蒙蒙亮到盛興橋旁邊的埠頭去買柴,有時要跑到南門頭。如果遇到刁鉆的“柴客人”,買了他的柴,翻開柴把來還會發現里面的柴被水浸濕了或者裹著塊大石頭。后來,各地辦磚瓦窯,下山的柴草越來越少,那時雖然“封山育林”,甚至采取拗斷砍柴人的扁擔、沒收柴繩的處罰辦法來“禁止砍柴”,但山頭還是被砍得光禿禿的,連柴根也得掘起來。有的人家通過關系從酒廠里買來做酒后的渣滓叫“紅刺根”,推在公路邊曬干了來燒火。七十年代初在修水利時挖出“黑爛泥”,把它曬干敲成碎塊也可燒,生產隊里每戶分配了燒,也有一船船裝到城里賣給居民的。
大灶頭終竟在灰飛煙滅中“下了崗”,被一只只小小的煤球爐所取代。煤球后“進化”為煤餅,都憑票(卡)供應。其間煤油爐(又叫“經濟爐”)也風光了好些年。那時政治運動方興未艾,單位、工廠里一些“逍遙派”職工、技術人員閑得無聊便用鐵皮敲敲打打,自制煤油爐,芯子有六管、九管,最大的十二管,燒火油或柴油。現在這些可快成“文物”了吧。
八十年代燒液化氣,滿大街只見自行車后座掛個煤氣罐,讓人聯想到幼時公路邊看到汽車后背的大氣罐。我所在單位參加了某個液化氣站的集資建設,每位教職工每年能分到三四瓶“白市”煤氣。大家歡天喜地的。我的那輛海獅牌重磅自行車于是成了灌氣專車。朋友用鋼筋做個鉤頭,扣住氣罐掛在自行車載貨架側邊,側著車身飛馳到城西三碰橋外,又到校場山后,還到白沙路楊家村東邊的灌氣站。每隔一兩個月,老岳父都會給我來電話:“阿陸,煤氣瓶要換了。”
上海親戚家有管道煤氣,兩三戶人家合一間廚房,各有煤氣灶,免去了換罐充氣之勞。九十年代末,鄉下慈溪也有了,政府引進港資辦起了管道煤氣公司。前幾年東海氣田終于通到了慈溪,我家灶頭燃起純藍的火焰便來自遙遠的東海大陸架。
現在又有電飯煲、微波爐、電磁爐,太陽能灶也“飛入尋常百姓家”。久已沒有采樵為生的“柴客人”了,過去濯濯童山,如今柴草長得人都鉆不進去了。如此,青山常綠該有望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