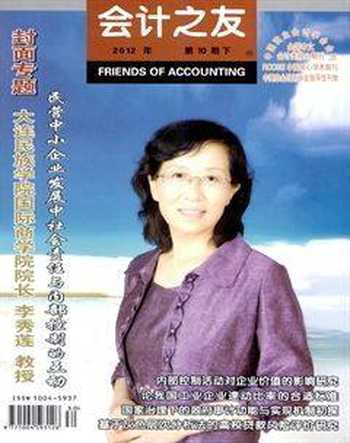持續經營審計決策動機:一個基于自我實現預言的解釋
朱朝暉 楊濱
【摘 要】 審計師根據審計證據作出審計判斷,不僅僅是一個認知過程,同樣也是一個動機問題。文章分析了審計師進行持續經營審計決策時的動機因素——審計師對持續經營不確定審計意見的自我實現預言效應的預期。這種動機使得審計人員并非中立的決策者,而是目標導向的,他們會更重視與其預期結果一致的審計證據,從而影響其對客戶公司持續經營能力的判斷。
【關鍵詞】 持續經營不確定性審計意見(GCO); 審計; 自我實現的預言
持續經營不確定性審計意見(going-concern opinion,以下簡稱GCO)是指由于被審計單位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導致注冊會計師對其持續經營假設產生重大疑慮,從而出具的一種非標準審計意見。具體包括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保留意見、無法表示意見和否定意見等類型。
企業持續經營能力是財務報告使用者進行合理決策、規避風險的重要依據。對上市公司持續經營能力進行判斷和評價是注冊會計師審計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內容。持續經營審計意見日益成為資本市場令人關注的一個重要現象。
一、持續經營不確定性審計意見:國內現狀
從1997年我國出現第一份對上市公司發表GCO審計意見的審計報告以來,GCO審計意見的審計報告在數量上呈上升趨勢:從準則出臺之前的零星發布,到1999年頒布《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17號——持續經營》后,GCO審計報告占非標準審計報告比例從百分之十幾逐漸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幾;2003年對準則的修訂導致這個比例直接躍升到50%左右;而《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 324 號——持續經營》正式頒布實施后,這個比例再次躍升到70%左右,個別年度甚至達到了80%。2011年,這個比例仍然保持在70%。根據中注協發布的上市公司2011年年報審計情況快報,截至2012年4月30日,證券資格會計師事務所共為2 362家上市公司出具了審計報告。其中,標準審計報告2 247份,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91份,帶其他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1份,保留意見審計報告19份,無法表示意見審計報告4份。在所有112份非標準報告①中,明確提及了持續經營不確定問題的有78份,占當年非標準意見的比例將近70%。
然而,另一組數據卻令人疑惑,2007年實施審計準則1324號以來,期間終止上市的公司為28家,其中2007年10家、2008年1家終止上市的沒有2007年以來的審計報告,剩余17家公司,除了ST本實(200041)因2005、2006年連續兩年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審計報告一直被停牌,2007、2008年又連續兩年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審計報告,并于2010年終止上市;ST東北高(600003)2007年被出具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并于2010年終止上市外,其余15家公司從2007年到其終止上市的2—4年內均收獲了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即使是ST東北高(600003),2008年的審計意見同樣是標準無保留的。我國的審計人員似乎并沒有在警告社會公眾關于上市公司經營風險上發揮應有的作用。是什么影響了審計人員對上市公司持續經營判斷的質量呢?
二、持續經營審計決策:認知與動機
審計準則要求審計人員客觀地、無偏地評價所有相關的證據。然而,大量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在處理信息和作出具體決策,尤其是在處理復雜的信息時,決策者往往無法達到完全理性的狀態。持續經營審計過程是一個需要在短時間內評價大量文件資料的多環節的信息處理和決策過程,因此,持續經營審計往往因為各種心理偏差,影響了審計人員如何看待和處理審計證據(Smith和Kida,1991)。
導致審計人員產生審計判斷偏差的心理效應,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然而這些研究關注的是審計人員客觀認知判斷過程中的有限理性,如錨定效應、時近效應、框架效應和肯定性傾向等;強調客觀因素,如證據的類別、證據的性質、證據的呈現方式等對審計人員判斷的影響;強調即使決策者知道他需要理性或者努力想做到理性,但由于理性認知的限制,他們無法達到理性的狀態(邢劍鋒,2011)。然而,影響審計人員出具最終審計報告的,不僅僅是一個認知問題,它同時也是一個動機問題。
事實上,在持續經營審計決策的不同階段,影響審計判斷質量的因素也不同(于艷,2010)。在審計過程中,審計人員首先需要識別客戶潛在的持續經營問題,這取決于審計人員的知識、經驗、技能、審計判斷模型及輔助工具、準則可操作性等因素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審計人員需要決定是否應為存在持續經營問題的客戶出具一份帶GCO的審計報告,研究者往往從淺層的經濟利益、審計風險角度加以分析,卻忽視了其深層的動機形成過程。對動機的分析,在審計研究中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Guiral,2011)。
三、持續經營審計決策動機:一個基于自我實現預言的解釋
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lling Prophecy)效應,也稱為羅森塔爾效應或皮格馬利翁效應。相傳塞浦路斯國王皮格馬利翁擅長雕刻,決定永不結婚的他雕刻了一座美麗的象牙少女像并愛上了這個雕像。皮格馬利翁把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熱情、全部的愛戀都賦予了這座雕像。他像對待自己的妻子一樣對待雕像,并最終感動了愛神,賜予雕像生命,與皮格馬利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人們借用這個故事說明人的期待效應。20世紀60年代末,哈佛社會心理學家R.Rosenthal(羅森塔爾)和L.Jacobson(雅各布森)對一所小學的學生進行了所謂的“預測未來發展”的測驗(實為智力測試),而后不考慮測試成績隨機地在各班抽取20%的學生,并故意告訴教師,這些學生在學業上很有發展潛力。8個月后,對全校學生的再次智力測試進行一次測驗,結果發現,那些所謂“具有發展潛力”學生的智力比其他學生有更大的發展。研究結果說明,教師對學生具有不同的心理預期,并且在無意識中把自己的預期傳遞給了學生,而最終結果,學生的行為與教師對他們的預期一致。羅森塔爾把這種現象稱為“皮格馬利翁效應”。
在持續經營審計決策中,研究者早就證明,審計人員能夠識別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Kida,1980),所以審計人員是否決定披露GCO的原因可能超越了客戶財務狀況的因素,可能并非因為審計人員沒有能力識別客戶的持續經營問題,而是源于審計人員對發布GCO可能導致的經濟后果的預期。
在持續經營審計中,自我實現預言效應表現為審計人員發布GCO可能導致客戶企業終止業務的可能性增加。作為獨立于上市公司和利益相關者的“第三人”而作出的審計意見,上市公司審計報告的意見類型為企業各方面的利益相關者所高度重視,并能對他們的決策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上市公司破產之前被出具GCO審計意見,會被利益相關者視為審計人員向市場傳遞了公司財務困境方面的信息,財務報告使用者很可能對這個專業的意見作出反應,繼而調整自己的行為來表示對這個專業意見的認可,從而導致股價下降以及企業財務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并可能導致客戶公司破產或加速破產。也就是說,審計人員的公開懷疑,加速了公司的結束。而這種自我實現效應對于審計人員的效應是:如果這種GCO自我實現,審計人員的未來經濟租無法實現;或者,客戶意識到GCO意見的逼近,先行更換審計人員,從而避免可能的GCO和潛在的GCO自我實現效應(Tucker,et al.,2003);或者因為出具GCO而客戶并沒有發生經營失敗帶來的聲譽損失或被辭退損失(廖義剛,2012)(圖1)。
對于這種自我實現的效應,審計人員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有預期的(Mutchler,1984)。因此,基于對這種自我實現預言效應的預期,審計人員就可能產生對客戶持續經營狀態的先念偏好,使得審計人員有強烈的欲望去相信客戶將持續經營,從而不愿意將公司持續經營不確定這樣的預期傳達給社會公眾。這種方向性的目標偏好,會使得他們更傾向于通過參考其目標偏好來評價審計證據(Wilks,2002)。審計人員可能采取一定的證據加工(evidence-processing)策略。所有的證據都會以無偏的方式引起審計人員注意的假設,在這種情況下是無效的。審計人員可能將更多的權重分配到與其期望結果一致的證據上,而忽視或者輕視那些質疑客戶生存能力的反面證據的存在(Guiral,2011)。其最終結果是,審計人員在可能并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對持續經營假設作出無偏判斷的能力大打了折扣。
四、結論
審計人員的審計過程是一個信息的加工處理和決策過程,審計人員的行為特征不可避免對其產生重要影響。審計報告的錯誤,除了審計人員有意認可企業當局的會計造假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審計人員認知與決策中的心理偏差,這已經成為了行為審計的核心內容。
從心理學角度看,審計人員對審計證據的信息加工和態度(認知的過程),可能受到他們自我實現預言效應的期望驅動(動機/激勵因素)。對自我實現預言效應的預期,使得審計人員并非中立的決策者,而是目標導向的,他們會更重視與其預期結果一致的審計證據,從而影響其對客戶公司持續經營能力的判斷。
【主要參考文獻】
[1] Guiral, A., Ruiz,E. and Rodgers, W. To What Extent Are Auditors Attitudes toward the Evidence In?uenced by the Self-Fullling Prophecy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2011,30(1):173-190
[2] Kida,T. Aninvestigation into auditors continuityand related qualification judgment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18(2):506-523.
[3] Mutchler, J. Auditors perception of the going-concern opinion.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1984,3:17-30.
[4] Smith, J., and T. Kida. Heuristics and biases: Expertise and task realism in audit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1, 3: 472-489.
[5] Tucker, R. R., Matsumura, E. M., and. Subramanyam, K.R. Going-concern judgment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nd forecast accurac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03,22:401-432.
[6] Wilks, T. J. Predecisional distortion of evidence as a consequence of real-time audit review.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2,77(1): 51-71.
[7] 廖義剛.審計意見的決策有用性及其出具動因:研究框架與研究述評[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2,27(5):49-56.
[8] 邢劍鋒.心理因素對審計的影響[J].審計研究,2011(5):110-112.
[9] 于艷.持續經營審計判斷質量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兩階段持續經營審計決策過程[J].財會研究,2010(23):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