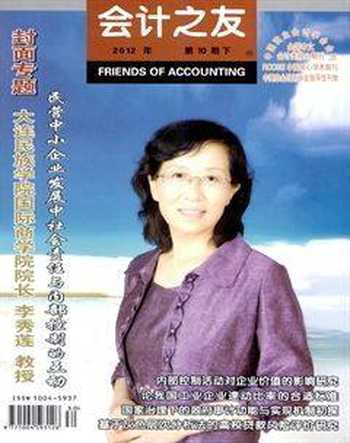ST公司高管薪酬激勵機制的現狀研究
龔大林
【摘 要】 目前,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共有百余家上市公司被特殊處理(ST),這在一定程度上威脅著投資者的利益,ST企業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板塊。基于此,文章試圖通過ST企業和撤銷ST企業的高管薪酬激勵現狀以及薪酬業績相關性的分析,揭示出ST與撤銷ST企業的薪酬激勵差異。研究發現,在撤銷ST的企業中,已經建立起良好的薪酬激勵制度,這也可能是其撤銷ST的重要原因之一。
【關鍵詞】 ST; 高管薪酬激勵; 經營業績
一、前言
1998年3月,中國證監會發布了《關于上市公司狀況異常期間的股票特別處理方式的通知》,由此ST企業應運而生。所謂ST企業,就是指交易所應對狀況異常的股票交易實行特別處理的上市公司。
長期經營不善將會大大地增加企業冠以“ST”帽子的風險,而如果公司“連續三年為虧損”,則會面臨停止上市的風險,這一舉措將ST企業推到了風口浪尖之上。而究其深層次的原因,是企業激勵機制的缺陷所導致,當企業尚未建立健全的激勵機制時,高管層就會背離股東最大化的目標,侵害企業的利益,產生委托代理成本。據統計,大多數的ST企業根本未建立高管薪酬的激勵機制或是激勵機制尚不健全,因此對于如何建立健全薪酬激勵制度,避免“戴帽”,關系到上市企業自身的健康發展和證券市場的有序運行。
在我國有關ST板塊的研究多集中在投資者保護、財務風險預警、盈余管理、公司治理環境、內部控制、股價波動等方面,而對于ST企業的薪酬激勵現狀卻鮮有研究,但是,良好的薪酬契約應該有助于緩解經理人自利行為引發的代理問題(Jensen and Meckling,1976;Smith and Watts,1992),是企業提高業績的有效途徑,因此研究ST公司時不考慮薪酬激勵情況不甚合理;大量探討高管薪酬激勵機制的文獻,考察的樣本既有上市公司全樣本,也有針對某一行業或具有某一相同特征的子樣本,但在這種情況下是需要將ST、PT等行為異常的樣本剔除的。
本文將研究高管薪酬激勵機制的視角集中在ST企業上,旨在通過對ST企業高管薪酬激勵機制的現狀進行分析和研究,試圖揭示符合上市公司發展規律的合理薪酬激勵機制,為豐富公司治理的理論體系增添新的內容和知識,并為現存尚未摘帽的ST企業的不合理薪酬激勵機制的校正提供較為直接的證據。
二、ST企業高管薪酬激勵現狀分析
(一)樣本來源與選取
本文選取2009—2011年的ST企業作為研究樣本,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和巨潮資訊網,同時剔除數據披露不完整的樣本,共計得到有效樣本435個。在具體分析過程中,將在這一期間撤銷了ST的樣本單獨列為一組,與2011年仍保持ST的樣本做對比分析。
(二)基本情況分析
筆者統計了ST企業的戴帽原因,主要分為以下幾類:234個樣本連續兩個年度虧損;108個樣本每股凈資產小于面值;45個樣本連續兩個年度虧損并且每股凈資產小于其面值;36個樣本被出具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9個樣本被出具拒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3個樣本由于欠款未正常收回,財務狀況異常。
(三)高管薪酬水平分析
將撤銷ST的樣本單獨列為一組,與保持ST的樣本進行高管薪酬水平的對比分析,高管薪酬用高管前三名薪酬總額表示,ST表示2011年仍保持ST的樣本,NST表示2011年撤銷ST的樣本,具體分析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NST的高管薪酬均值要略高于ST,ST樣本高管薪酬均值為65.6萬元,而NST的高管薪酬均值為78.8萬元。ST的樣本標準差為145.7126,NST的樣本標準差為133.1674,波動性都較大。從極小值和極大值看,ST的極小值為11.89萬元,極大值為196.00萬元,NST的極小值為13.5萬元,極大值為230.7萬元。從表1中可以看出ST和NST的公司高管薪酬均值和中值數的Wilcoxon/Mann-Whitney統計量在1%的水平下都顯著,說明它們兩兩之間存在明顯差異。
(四)高管薪酬激勵狀況分析
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高管薪酬激勵機制的建立:是否設立薪酬委員會、是否設立年薪制以及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兩職兼任。之所以將兩職合一加入到薪酬激勵機制中,是因為對高管的激勵和監督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當激勵更為有效或相對容易時,股東傾向于激勵高管,而監督更易行時,股東則更傾向于監督高管。兩職合一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映出企業公司治理的松散程度以及薪酬激勵機制的有效性。
從表2可以看出,撤銷ST的樣本其高管薪酬激勵機制更為完善。在兩職合一方面,ST的樣本仍然有67個樣本處于兩職合一的狀態,而撤銷ST的樣本中,僅有7個樣本仍然為兩職合一;在設立薪酬委員會方面,ST的樣本有276個設立了薪酬委員會,撤銷ST的樣本有81個設立了薪酬委員會;在設立年薪制方面,ST的樣本有311個設立了年薪制,撤銷ST的樣本全部實行了年薪制;在高管的股權激勵方面二者都沒有建立股權激勵制度。
(五)高管薪酬差距分析
Jensen和Murphy(1990)認為衡量高管薪酬激勵強度的標準不是絕對報酬額,而是取決于相對報酬,由此衍生出錦標賽理論。借鑒該思想,我們分析高管團隊內部的薪酬差距是否存在差異。
從表3可以看出,ST的樣本薪酬差距的均值為15.67萬元,標準差為35.89,極大值為32.1萬元,極小值為3.69萬元。而撤銷ST的樣本,薪酬差距較大,均值為20.89萬元,標準差為21.8,極大值為39.2萬元,極小值為5.67萬元。這一結果支持錦標賽理論。從表3可以看出ST和NST的公司高管團隊內部薪酬差距均值和中值數的Wilcoxon/Mann-Whitney統計量在1%的水平下都顯著,說明它們之間也是存在明顯差異的。
三、ST企業高管薪酬激勵合理性分析
高管薪酬激勵的目的在于解決委托代理沖突,減少委托代理成本。為此,設立良好的薪酬契約應是基于與業績掛鉤的基礎之上的。據此可以推測,上市公司ST后,可以通過建立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勵制度來激勵高管改良業績。筆者先考察高管薪酬絕對水平的治理效應,建立薪酬與業績的回歸模型,考慮到高管薪酬水平與公司規模、負債比率、行業等有一定的相關關系(Jesen等,1990;魏剛等,2000;杜興強等,2009),將公司規模、負債比率、行業作為控制變量,建立如下 模型:
LnP=a1+a2×Roa+b1×Size
+b2×Lev+b3×Ind(1)
上式中,LnP表示高管薪酬的對數值;Roa為總資產報酬率,反映企業會計業績值;Size為企業的規模,用總資產的對數值表示;Lev表示負債比率,用資產負債率表示;Ind為行業虛擬變量,將ST組和NST組的樣本分別回歸,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從業績對高管薪酬的回歸可以看出,在ST組中,高管薪酬水平與Roa在統計上并不具有相關關系,這證明在被交易所ST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并沒有發揮應有的治理效應,而在撤銷ST的樣本中,Roa的系數為4.175,并且在10%的統計水平下顯著,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明,股東傾向以薪酬激勵的方式激勵高管努力工作,提升公司業績,所以高管薪酬的制定與業績掛鉤,并發揮了良好的治理效應。
近年來,不少學者研究了薪酬差距對企業業績的影響,由于對結果的不同意見衍生了行為理論和錦標賽理論,行為理論認為薪酬差距的擴大,會使成員感到不公平,從而影響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不利于企業業績的提升。錦標賽理論則認為加大薪酬差距,是對能力最高者的獎勵,因而可以激勵高管更好地為企業工作,并鼓勵內部的監督和競爭。基于以上兩種觀點,驗證ST樣本和撤銷ST的樣本中,高管薪酬差距與業績的相關關系,筆者建立與模型(1)相同的回歸模型,并將因變量替換為薪酬差距。
Ln△P=a1+a2×Roa+b1×Size+b2×Lev+b3×Ind
(2)
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從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ST組中,Roa的系數為2.525,但是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在撤銷ST組中,Roa的系數為4.020,并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這一結果支持了錦標賽理論,合理的薪酬差距發揮了治理效應,激勵了高管提升企業的業績。
四、結論
本文從高管薪酬激勵的視角,分析ST上市企業高管薪酬激勵的現狀,并探究了ST企業撤銷ST處理的深層次原因,即是否關聯于高管激勵的有效性。本文基于高管薪酬是股東激勵高管的重要內容,企業經營業績將會直接反映到高管的薪酬水平(或是薪酬差距水平)。在面臨停止上市這樣的危急時刻,股東會傾向于更為有效地激勵高管提升企業業績。本文關于薪酬現狀和薪酬業績有以下結論:
通過對ST樣本和撤銷ST樣本的對比分析發現,ST樣本的薪酬水平與薪酬差距水平比撤銷ST樣本低,同時撤銷ST樣本的薪酬激勵機制也較ST樣本更為完善。在對薪酬和業績的回歸中,筆者得出撤銷ST的樣本其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差距水平與業績掛鉤,并且薪酬差距能更好地體現出與經營業績的相關性,而ST的樣本其薪酬水平和差距水平與業績并不具有相關性。因此,本文認為,上市公司撤銷ST的原因之一在于建立了良好的薪酬激勵制度,降低了企業的代理成本,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了ST上市公司改善經營績效的啟示。
【參考文獻】
[1] Murphy, K.J., 1998. Executive Compensation.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 Jensen, M.J., Meckling, W.H.,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305-360.
[3] 楊剛,王磊,由雯.我國上市公司高管激勵型薪酬模式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1(11).
[4] 杜興強,王麗華.高層管理當局薪酬與上市公司業績的相關性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7(1).
[5] 林浚清,黃祖輝,孫永祥.高管團隊內薪酬差異、公司績效和治理結構[J].經濟研究,2003(4):31-40.
[6] 魏剛.高級管理層激勵與上市公司經營績效[J].經濟研究,2000(3).
[7] 李增泉.激勵機制與企業績效——一項基于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會計研究,2000(1).
[8] 寧向東,張海文.關于上市公司“特別處理”作用的研究[J].會計研究,2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