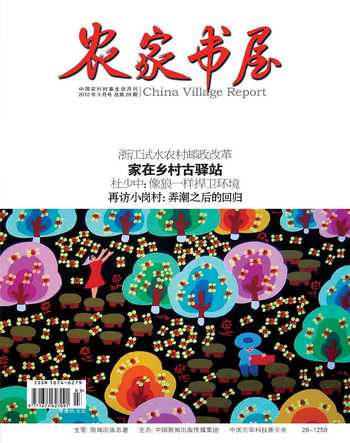圓桌
丁啟陣:兒時的家園無跡可尋
丁啟陣
知名學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交流學院(原中文系)副教授。
從前社會封閉經濟落后,鄉村面貌幾百年一成不變,人人夢想著有朝一日發生巨變。但是,當巨變真正發生的時候,又發現巨變并不是當初想象的那么美好,一些美好的東西隨著巨變一去不復返了。
村里的房子大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早已不在話下,彩電冰箱空調洗衣機微波爐,都是尋常之物。可以說,住的方面,不少家庭趕上并超過了普通城市居民的水平。行的方面,穿村而過的公路,也從沙石路變成了水泥路、柏油路。趕集、進城,由基本靠走,一變而為自行車、蹦蹦車,再變而為公交車、私家轎車。
日常生活四件事,衣食住行,衣食上的變化有目共睹,無需我贅言。
誰能說,農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富裕、越來越好呢?
但是,發生如上巨變的同時,也發生了另一方面的許多變化。我兒時的文體樂園,環繞整個村子,各有數十畝面積的柏樹林、栗樹林、毛竹林,蕩然無存;村子南邊上百畝的桑園,桑園間我兒時的戲水、垂釣樂園——一個長方形,一個正方形,兩個常年碧波蕩漾的清池——一去不復返了;我兒時觀魚、戲水的穿村水流,不再汩汩流淌,不再清澈見底,不再水草悠悠,不再有成群結隊的魚蝦蟹鱉。三十多年前,主婦們清晨到那里舀水煮飯,飯熟之時,常常可以看到,雪白的飯粒之間點綴著許多金黃色的小蝦米!……那個我生活過十七年,環境優美、趣味無窮的農村,幾乎無跡可尋了。
柏樺:用詩歌挽留鄉村
柏樺
著名詩人,現為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教授。
我高中畢業是1975年,當年上山下鄉,我在農村生活了兩年半,直到1978年春考上大學。三十多年了,我至今沒回去過,有機會很想回去看看。我的知青朋友有的回去過,說當地農民還記得我,還說山溝溝里出了個大詩人。他們很可愛。
那是個大茶場,有廣袤的森林,加上我們三十幾個知青住的地方是個“知青點”,沒有孤獨感。更關鍵的是,我并不是每天必須勞動。因為我讀書的習慣根深蒂固,無論什么,說出來的道理似乎就“見解不凡”,贏得了農民的尊重。他們用最大的善意對待我,我至今感銘在心。舉個例子,每個知青都要評工分,挑50公斤走10公里的壯勞力,一天才8個工分,我體力差,勉強評4個工分。很多女知青都比我強,大家不說什么。我向田園學習并常常醉臥森林,可以說,這是我一生中最最快樂的時光。
我有不少作品涉及這段生活,比如《高山與流水》《決裂與扎根》等。一次,為了見一個朋友,我走了一百里路。如今,我反復憶起那次長途遠行的情景。拂曉時分,鄉村生活的美仿佛是頭一次向我打開:竹林、溪流、房舍、炊煙,慷慨的寧靜似從未遇見,而我終于抵達!
葛紅兵:我是一個農民
葛紅兵
作家,批評家,上海大學中文系副主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
我覺得童年的意義,要在一生中經過反復發掘才能知道。在我這個層面上對童年的理解是這樣的,它有幾項財富,第一項就是它給了我關于大自然的認識。比如說跟動物的“交往”,包括小鳥、貓、狗,還有馬、牛、羊等等,與一系列這樣一些小生靈的“交往”,讓我感知到了生命的最初含義。
還有就是跟植物的“交往”。那個時候我在鄉下,對麥子產生了極深的感情,那是養育我們的東西,同時它也是美麗的景色,是生靈。我從來就是把這些東西當作生命來看待的,它養育了我的同時也是我此后寫作的一個非常重要動機,就是說把自己更加鍥入、融合到大自然中去。農村生活是非常難得的人生體驗,它可以激發一個人內心最為純真的情感和思緒,從而更加認真地對待生命。
近年來我不斷地宣稱我是一個農民,不要叫我知識分子。即使我是一個教授,我還是要像一個農民那樣說話。我希望我的語言像勞動號子一樣在大地上回響,那么有力量;我希望我自己在社會上的形象就像農民光著膀子,在大地上勞動一樣,他們不害怕自己的皮膚暴露在陽光里,不害怕流汗,是那種非常本然的情感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