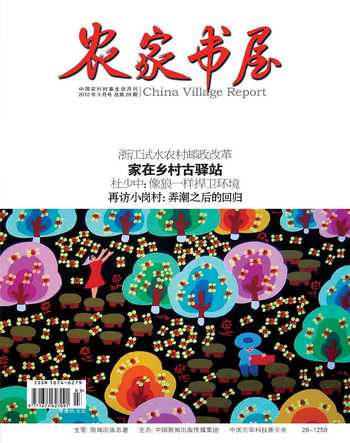再訪小崗村:弄潮之后的回歸
徐馳



一輛略顯陳舊的中巴車緩緩地停在一個三岔路口邊上,賣票的大媽指著右邊一條嶄新的馬路告訴我們,往前再走8公里就是小崗村了。
8公里的路程并不短,尤其是在寒風凜冽的早春農村。這條路是幾年前新修的,沿路兩旁凈是一大片綿延開去的田地,偶爾才有幾戶農家,更別指望在路上能搭到車了。許久才有一輛農用三輪車路過,我們以最原始的方式到達了小崗村。
小崗村的確很小,一條友誼大道貫穿全村,上百戶人家就坐落在大道兩旁,依次排開,房子是在08年統一新翻的,大部分都是兩層樓房,漆著白色的外墻。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小崗村又很大,自從2008年附近幾個村子合并之后,小崗村下轄23個村民小組,擁有849戶、3823人,耕地面積高達 8713畝,人均耕地2.28畝。
與普通的北方農村無異,小崗村家家戶戶都養著狗,掛著玉米、臘肉,街上也見不到太多人,整個村子都稍顯冷清。倒是入口處由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親自題詞的牌坊“鳳陽縣小崗村”,顯示它不一般的過去與滄桑,正如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在《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曾總結的,小崗村“江山依舊,舊貌猶存”。
戛然而止的“魔法”
關正銀家的三層小樓在村里很顯眼,一棟嶄新的樓房,刷著黃色的外墻,掩映在一片白色房子之間。這是村里為數不多的三層樓之一。
房子是在2008年翻新的。一樓關正銀夫妻倆住,用的大部分還是他們當年結婚時的家具;二樓則是完全不一樣的景象,電視電腦客廳沙發一應俱全,大兒子去年剛剛結婚,這是他的婚房;三樓目前還不住人,小兒子當兵去了,這是為他準備的。整個房子干凈,整潔,如同這一家五口人平淡安穩的生活。
關正銀的父親關友勝就是著名的大包干帶頭人之一。作為“大包干”的第二代,他人生中最榮耀的時刻莫過于曾經接待了來訪的胡錦濤總書記,那張他和總書記的巨幅合影至今還擺在他們家床頭柜的顯著位置。
當年村里十八個漢子簽生死契分田到戶的時候,關正銀才十多歲,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直到有一天,他跟著母親下田種地,一輛政府的車子剛好路過,看到田里只有一對娘倆在干活,就下車質問:隊里的其他人呢?母親支支吾吾答不上來,關正銀這才知道,這么做是要殺頭的。
“但是當時真的沒辦法,不這么干就得餓死。”關正銀說,他從小就不允許自己兒子浪費糧食,“你們可沒吃過那種苦啊。”
后來“大包干”做成了,這個曾經的“三保村”就再也沒餓過肚子,還破天荒的有了余糧。1980年,家里賣了幾頭母豬,湊了點錢,把原本高粱稈子圍成的茅草屋翻新成了幾間小土屋。1990年,關正銀結了婚,父親又為他單獨蓋了間平房。
雖然才43歲,但關正銀的兩鬢早早的出現了一絲白發。幾十年來,他曾在大包干紀念館當過廚師,也在養豬場殺過豬,06年的時候還曾和來小崗村創業的大學生合作搞過大棚種植雙孢菇,最多的時候他有三十幾個大棚,一年收入13萬,眼看快要搞成了,卻遇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產品價格從最高時的5塊一斤跳水至幾毛錢一斤。大學生走了,他家的10多畝地也種回了黑豆,只是去年黑豆的價格也不景氣,只賣到5塊錢一斤,還不到前年的一半。
這幾年村子里實行招商引資,好多農戶的土地都以1.2萬/畝的價格被征用了,這才有了點積蓄。只是關正銀家的田比較遠,一直沒被征用到。他索性開了一個自來水廠,每個月都有一千塊的固定收入,大兒子在村里的GLG工廠當保安,月收入也有兩千多,再加上種田的收入,一家人過得也還不算緊巴。剛過完年,現在還處于農閑時期,關正銀每天的事情就是到各家各戶抄抄水表,然后在家里看看電視。
雖然小崗村曾是中國改革的明星村,但從上世紀90年初,大包干的“魔法”似乎就戛然而止,從那時候開始,整個村子似乎就再沒多大變化。“08年翻新屋的時候還是村支書牽頭的,每戶人家補償一到兩萬,不然估計還是土房子。”關正銀說。
近十年來,小崗村也漸漸形成了父母在家種地、子女外出打工的經濟模式。直到近幾年才漸漸有了變化,許多工廠拔地而起,前來旅游的人也漸漸多了起來。
“如果你們晚幾個月再來,這兒更美,游客也更多。”說這話的時候,蔣華榮系了條圍裙,正蹲在自家院子里擇菜,她今年正好三十出頭,染著黃色的頭發,面容姣好,是這家“金昌食府”的老板娘。今天的生意并不好,只是零零碎碎來了五桌客人。
準確地說,蔣華榮并不算土生土長的小崗人,她是河南人,十年前嫁到了這里。她與丈夫結識于廣州的一家工廠,夫妻倆在那個工廠打工近十年,三年前才回到村子,開了這家飯店。
“村子里前前后后一共有四家飯店,都是這兩年才開出來的。不過,我們家的生意應該最好。”蔣華榮毫不掩飾對自己飯店的贊譽,如今這是他們夫妻倆唯一的經濟來源。尤其是在這幾年,來考察的、旅游的人一大撥,村支書通常都會把客人統一分配到各家飯店,這令他們很滿意。為了提高服務質量,夫妻倆還拿出所有積蓄買了一輛車,丈夫每天的任務就是到鎮上買菜,然后接送客人;而她則作為飯店的收銀、幫廚兼服務員,遇到特別忙的時候,村里的親戚也會過來幫忙。
“這可比在廣州打工強多了,”蔣華榮說,“出去那么多年,也不見得掙到幾塊錢。我看到今年好多村里人都回來了,打算做點小生意。”
42歲的嚴家芳就是回歸者之一,她很早就出去打工,這些年幾乎走遍了大江南北。今年年初,她回到村子,騰出自己家的一間房子,開了一家超市。超市就叫“紅手印”,一個具有時代烙印的名字。據她說,當年十八戶簽契約的時候就是在他們家按的紅手印。
近年來小崗村的變化,嚴家芳是實實在在看在眼里的,“光是工廠就多了好幾家,村子里的人氣也旺了。”她琢磨著開家超市,生意應該差不了。
更重要的是,女兒馬上就快上高中了,她要回家親自帶孩子。嚴家芳有些自責,她的大兒子以前讀書很好,就是因為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沒人管他,成績才一落千丈。如今兒子也只好到在寧波打工,連過年都沒回來。所以,這個女兒非她自己帶不可。
對大多數小崗人來說,他們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小崗村為什么發展不上去?還不是我們讀書不夠多!”學校門口的一位村民這樣說道。
早在二十年前,村里就辦了小學,幾乎所有的小崗人都是這里畢業的。2008年村子合并后,又增添了兩所幼兒園。去年村里還建成了一所中學,今年9月份就打算招生授課了。
說起這些,那位村民一臉希望,他們之中大多數沒有文化,但他們知道有文化意味著什么。上一輩的小崗人寧愿自己苦一點,也不愿下一代再走自己的老路子了,教育才是小崗村的根本出路。
曾經的時代弄潮兒
天色漸暗,接近下午四點的時候,路上連農用三輪車都很少出入,家家戶戶都開始準備晚飯,小崗村再次恢復了寂靜。
臨走前,我們在路邊偶遇了嚴金昌老人,當年帶頭“大包干”的十八人之一。
老人穿著一條黑色西褲和墨色棉襖,上衣穿得一絲不茍,帶著一頂棉帽,面頰刮得干干凈凈,整個人整潔利索,尤其是臉龐紅潤而又有點發黑的膚色,那是多年日曬和勞作的證明。他會在舉手投足間不經意地流露出某種莊嚴感,看得出,他代表著整個小崗村。
事實的確如此。今天是小崗村村支書丁俊的任滿之日,作為代表,嚴金昌與其他健在的十一位帶頭人集體把他送回了合肥,剛剛才回到村里。
嚴金昌的外表比他實際年齡年輕得多,他反應迅速,說話清楚,也沒有太多老年斑和白頭發,一點也不像一位72歲的老人。尤其是當他講起三十四年前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時,已經可以平靜得宛如在講述別人的故事。
1978年11月24日,晚飯過后,在沒有電燈更沒有路燈的小崗村,就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了。忽然,一陣此起彼伏的狗吠聲響起,小崗生產隊的十八條漢子,先后出了門。他們迎著凜冽的西北風,袖著雙手,縮著腦袋,陸陸續續向最西邊的嚴立華家摸去。
不一會兒工夫,冰冷破敗的茅草屋里,就聚滿了人氣,搖曳不定的煤油燈的光亮,把蹲在地上或坐在床上的一堆人影,夸張地映照在凸凹不平的土墻上。經過短暫商議,小崗村的十八戶決定冒著生命危險,分田到戶,并立下字據,按下手印。
“如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十八歲。”當年的契約上這樣寫道。
當然,嚴金昌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個日子后來會變得那樣重要。他單是記得那一年連老天爺都幫他們,“花生大豐收,漫山遍野都是;田里的芋頭有氣球那么大,我種了一輩子田都沒見過那么多糧食。”嚴金昌緩緩地說道,“那年,最差的農戶收入也在250元左右。”小崗村的“大包干”一時傳遍了大江南北。正是這個小崗生產隊的包產到戶,轟然撬動了中國,并引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變革。
如今,三十四年過去了,當年那些漢子也早已遲暮。就在今年,國家把他們每月的補貼從500元增加至800元,讓他們安享晚年。
現在的嚴金昌早已不下田了,每天吃過早飯,他都會在村子里轉轉,找相熟的人分根煙,然后隨便聊聊;假如天氣夠好,他也會在院子里找人打打小麻將;或者,他還會經常去村委會坐坐,與干部們談論一下小崗村的未來發展……
老人的生活正在逐漸走向平淡,而他腳下的小崗村才剛剛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