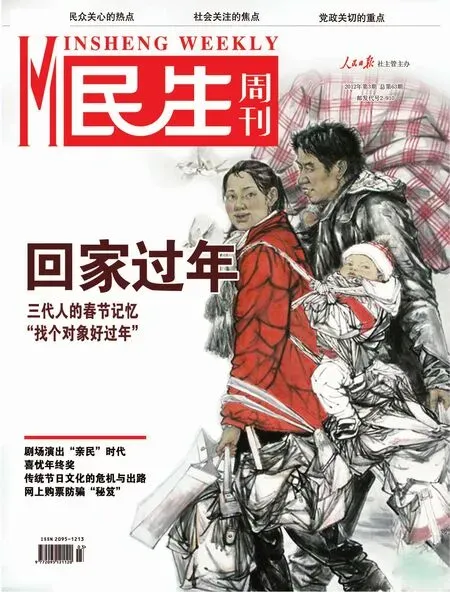傳統節日文化的危機與出路
湯嘉琛
見縫插針式的商業炒作與節日營銷,裹挾著五花八門的“洋節”文化呼嘯而來。諸如圣誕節、情人節、感恩節、母親節等異域節慶,正在成為中國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所推崇的新潮生活方式。
盡管很多人對這些“洋節”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傳統一知半解,但伴隨“洋節”一同襲來的感觀新體驗和文化新沖擊,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國民眾對節慶文化的理解。
毋庸贅言的是,那些在中國備受追捧的“洋節”,無論節日形式還是文化意蘊,都或多或少有所“改良”。最典型的例子是圣誕節的蘋果。它已逐漸成為中國版圣誕節的必備元素,但這顯然不是承襲西方社會的悠久傳統——僅僅因為漢語中“蘋果”與“平安”之間的語義關聯——當然,這個有些牽強的新節日傳統與商家的炒作密切相關。
“洋節”與中國傳統節日的沖突,集中表現在圣誕節與春節的文化沖撞之上。從時間上來看,圣誕節是公歷紀年的尾聲,而春節是農歷紀年承上啟下的節點,二者離得很近;從文化傳統來說,雖然圣誕節有宗教文化元素,但它和春節都強調家庭團圓,節日氛圍也都以喜慶、歡樂為主。然而,在很多中國年輕人看來,圣誕節是“新文化”、“新時尚”的代名詞,而春節則是“舊文化”“舊風俗”的代表。
當一種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形成某種對抗時,不少人都產生了幾分文化入侵的危機感,甚至還有幾分文化占領的屈辱感。正因如此,當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七節”的文化氛圍越來越淡,很多人往往不是反思我們的傳統節日出現了什么問題,而是將傳統節日“失傳”的危機歸咎于“洋節”的入侵。基于這種邏輯,近些年,有人號召抵制圣誕節等西方節日,也有民俗學者呼吁通過申遺來擴大傳統節日的影響力。
這種保護傳統文化的危機意識固然值得贊賞,但一項社會風俗能否歷經累世得以傳承,顯然與是否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并無直接關聯。早在幾年前,端午節和羌年(羌族的節日)就已經成功申遺,但這并沒有止住它們式微的勢頭——即便在屈原故里,被視為端午節標志性活動的劃龍舟,都已經更接近于表演,而非能夠讓大眾廣泛參與的風俗。
龍舟遭遇的尷尬,基本可以視作諸多傳統節日風俗共同面臨的通病。當一種風俗不能調動普通民眾的參與意識與熱情,就很容易讓人覺得它與自己“無關”,進而導致這種風俗失去文化傳承的社會基礎。我們時常在關于春節的新聞中聽到諸如“熱情的鑼鼓敲起來,歡樂的秧歌扭起來”之類的描述,畫面雖然很符合節日喜慶的氣氛,但那些終究是“表演”而不是“生活”。試問,有多少人春節期間會在自己家里敲鑼打鼓和扭秧歌呢?
不能激活民眾的參與意識,僅僅只是導致傳統節日文化式微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在于,無論是春節還是端午節、中秋節,我們的傳統節日過于強調“吃”這一元素,而忽略了更為重要的“文化”元素,這必然會在現代社會遭遇傳承困境。
在物質生活尚不豐富的時候,缺衣少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常態,而逢年過節則是能夠吃飽飯、穿新衣的“大日子”,因此無論老人小孩都期盼著過節。
然而,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很多家庭已經基本告別衣食住行層面的短缺需求,平常時日就能享受到以往在過節時才能享受的好生活,他們對節日文化必然會有更高的美學和精神層次的需求。問題恰恰在于,我們的傳統節日在演變過程中,并沒有滿足這種需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迎合了這部分需求的“洋節”,必然會被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所接受。
因此,要破解傳統節日所面臨的文化危機,出路既不在于通過“申遺”這種方式來尋求庇護,也不在于阻斷民眾對“洋節”文化的認可。真正行之有效的思路,是盡快實現傳統節日文化自身的轉型,在移風易俗中重新激活傳統節日的文化魅力。只有當傳統節日能夠更多地滿足工作的現實需要、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它們才會被更好地傳承下去,進而免于“消失”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