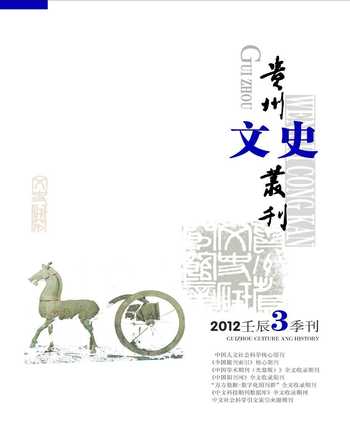致良知與“君子人格”的培養
黃江玲 陽紅
內容摘要:儒家提倡“君子之風”,也就是“君子人格”,它具有多種特質,而“內圣外王”的完美人格是最高理想。“致良知”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基本功夫。古今中外,對人格類型作了不同分類。王陽明倡導良知之學,認為人人心中具有良知本體。無論地位高低、職業殊異,只要立志、努力,都可以成為一個有德性人格的人。這正是“致良知”的巨大魅力所在,也是“君子人格”的巨大魅力所在。
關鍵詞:致良知 君子人格 境界論
中圖分類號:G1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8705(2012)03-53-58
儒家提倡“君子之風”,也就是“君子人格”,它具有多種特質,而以“仁、義、禮、智、信”為基本。而“內圣外王”的完美人格是最高理想。“致良知”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基本功夫。古今中外,對人格類型作了不同分類,儒家則提出境界之說,把君子人格略分為學人境界、賢人境界、圣人境界、萬物一體境界。在學人與賢人之間,還有“狂狷”境界。庶民百姓即愚夫愚婦雖然尚未達到“君子人格”境界,但他們個個都具有良知,無論地位高低、職業殊異,只要立志、努力,都可以做一個圓滿德性的人,成為一個有德性人格的人。一個人,只要“純乎天理而無欲”,就是君子。因此“人人可以為堯舜”。甚至惡人也可以轉化為善人。這正是“致良知”的巨大魅力所在,也是“君子人格”的巨大魅力所在。
儒家重視自我修養,儒家的為己之學,身心修養之學,要求從自己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自覺自愿地遵守儒家的工夫修習的原則。
“為己”不是為了獲取自己的利益,而是修養自己、充實自己,成就高尚的德操,成就自己的人格素養。當代著名儒學家杜維明認為“為己之學”是一個不斷擴展的多重關系的圓周中的自我發展、自我修養之學,“為己”,不是為了師長,也不是為了家庭,甚至也不是為了簡單的社會要求,而是為了發展個體人格,發展自己人格內在的資源。[1]
推原儒家典籍,對“為己”、“為人”有明晰的闡釋,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荀子對孔子的話作了明確的解釋,如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荀子·勸學》)荀子所闡釋的“為己之學”即是“身心之學”、“君子之學”;“為人之學”是“口耳之學”、“小人之學”。
君子之學,造就有道德的君子,塑造君子人格。小人之學,只能造就只顧私利的禽獸般的小人。中國的先哲們把“君子——小人”二分式的人格類型說,視為儒家所倡導的人格類型說。
從人格心理學和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考察,凡具備和諧精神的典型人格,便是孔子等圣人所提倡的君子人格。儒家提倡“和為貴”的思想,并以其為指導,去處理天人、人我、身心和主客間的關系,因此,君子人格具有共生取向、和諧發展的獨立人格。
“君子”一詞有多重含義。《論語》一書中“君子”一詞出現107次,主要是指“有才德的人”,只有一次指“在高位的人”。“小人”也有幾種含義,主要是指“無德者”或“見聞淺薄的人”。
孔子首倡“君子——小人”二分式的人格類型說,其后經歷代學者不斷充實和完善,對中國人的做人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延續至今,人們常以“君子之風”相矜尚。
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于“君子”的標準有多種提法,主要有十四個:仁、義、禮、智、信、忠、恕、誠、勇、中庸、文質彬彬、尚和、謙虛和自強。[2]凡具有以上素質者即為君子;反之,不具備以上素質者即為小人。恰如《淮南子·泰族訓》所說:“圣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君子”與“小人”,涇渭分明。
“君子人格”的十四種特質,只是表面的特質;深一層探析,可提煉出五種根本性特質,即“仁、義、禮、智、信”五種“常德”。
1.仁
“仁”是君子首先應具備的心理素質。孔子提出“仁、智、勇”三“達德”的命題。他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因為君子具有愛人的美德,泛愛眾人,故無所憂心;君子有知識,富智慧,故能不惑;君子為人剛毅果敢,故無所畏懼。而“愛人”是仁的核心。一個人若能以愛心待人,也就在行仁了。仁的另一個重要內涵是“孝悌”,這是倫理道德中最根本的品德。對父母長輩要行孝道,對兄弟、姐妹要有悌道,推而及于鄉鄰眾民,取得“泛愛眾以親仁”的社會效果,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
與君子相反,小人所愛的只是與他關系密切的人,只顧自己私利,不愿成人之美,常干那些損人利己的事,即“成人之惡”,諉過于人;甚而攻訐誣陷,落井下石,無所不用其極。
2.義
“義”是儒家崇尚的道德品質,常與“利”對舉。《論語·里仁》中,孔子主張“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并非絕對排斥“利”,但必須依正道而取之,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里仁》中孔子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只有依正道而取得的富貴,才可以享受,這就是“義”;不依正道,憑非法手段而獲得者,就是不義,應該丟棄。墨家“尚義”,與儒家之義有共通之處。
3.禮
“禮”是君子立身的根基,是待人接物應具備的基本禮儀,體現于日常的修養與實踐之中。孔子要求君子必須“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3],要用禮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孔子說:“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4]依禮而行,就不會干出離經叛道的言語行為來。
4、智
孔子把“智”作為“三達德”之一,要求君子努力學習修為,力求具有高超的智慧與能力。他曾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5]知識、智慧和能力,要靠平日長期的精心學習和積累,虛心求教于人。孔子嚴格要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而正焉,可謂學也已。”[6]君子有豐富的知識,才能正確認識自己和周圍諸多事物,正確處理個人與環境的關系,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
5、信
“信”即“誠信”,待人以誠,言面有信,言行一致。但信必須服從“義”這一最高原則。只對正義的事業講信,不能盲目對小人非義之言行講信用。孟子在《離婁下》中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如果犧牲“義”而守“信”,必將對社會造成危害。其他如誠、忠恕、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質彬彬、謙虛、自強等素質,均可包容于五種根本素質之中。
君子人格僅是儒家人格修養的一般性要求,而士子們追求的則是“內圣外王”的完美人格,即“人皆可以為堯舜”。儒家“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是仁、義、禮、智、勇、藝的完美統一。《論語·憲問》記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生平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據《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載,魯國大夫臧孫紇(仲武)很聰明,因不容于權臣,逃到齊國,但預見齊莊公有被殺的危險,便設法推卻掉莊公給他的田產,后來齊莊公被殺,他沒有受到牽連。而孟公綽清心寡欲;魯國勇士卞莊子勇敢無畏;冉求多才多藝,加以禮樂的文藝,六者具備,即成理想的人格典范。
漢代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論”。認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為雛,繭待繅以涫湯而后能為絲,性待漸于教訓而后能為善。”也就是說:先天性善的圣人,無須修為就自然具有理想人格。先天性惡、教也不善的斗筲之人永遠性惡,再教育也難為善。只有先天有善有惡的中民之性才有可能通過教育而為善。韓愈也贊同性三品說。朱熹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也支持董氏見解。
他們所提的理想人格的標準太高,一般人很難達到。但士子們依然將之作為畢生的理想去“修身”,去追求。
王陽明提出“致良知”的心學主張,對“成圣”的標準作了簡明的界說。他認為:“心之良知是謂圣。圣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眛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茍能致之,即與圣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圣愚之所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良知之外無學矣。”[7]也就是說,圣人同凡人都同具有“良知”,只要經過修養而致此良知,凡人也可成為圣人,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
這一論點,填平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圣凡”隔離的鴻溝,破除了“圣人”至高無上、永不可攀的成見。在“良知”同具的條件下,圣凡一致,透發出人人平等的光輝思想。給士子們成圣成賢的理想人格追求,點燃了希望的明燈。而成圣的標準只須一個:如能致得良知齊全純粹,也就是圣人。唯圣人之學也就是致良知。
然而,在致良知的工夫層次上,圣人、賢人及凡人仍然是有差別的。圣人致良知的工夫是自然天成,達到本體明凈,純然精熟,通脫透明的境界。而賢人在致良知的工夫上尚未精通、純粹,須勉力而為之。而一般凡愚之人,用功應更為深切,除去私欲障蔽,恢復本然良知,也可以躋攀圣人之境。
以往的學者,把圣人視為無所不知的全知全能者,先知先覺者。王陽明對此偏頗之見有所匡正。有弟子問陽明:“圣人應變無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陽明回答:“如何講求得許多?圣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己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講都是如此,是與圣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示天下,皆圣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而待于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后世,亦圣人之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有待于孔子?是知圣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個明的工夫。”[8]圣人之所以能應變無窮,只是心如明鏡,隨感而應,無物不照,并非預先講求應變之方。圣人的智慧和才能,是因為他的心不為私欲所掩蔽,對客觀事物觀察細致、公正準確,使自身良知所具有的智慧和潛能充分發揮,故而令人有預知的感覺。
圣人的才力有高下,而“此心純乎天地,而無人欲之雜”則是共同的。世間凡人,由于個人稟賦不同,才智有差異,有的聰慧絕頂,才智超群;有的領悟力稍弱,才智一般,只要他們積極修養,使其心純乎天理而不雜人欲,也同樣可成為圣人。凡人也可能成為圣人的命題,是對董仲舒等人性“性三品論”的徹底顛覆。“性三品論”中認定“斗筲之性”是永遠改變不了的,性惡者永遠不能從善。王陽明則認為不論什么人,不管才能的大小,不論地位的高下、身份的貴賤,職業的優劣,只要存心為圣,就有可能成為有德性人格的人。良知是天賦的,圣人、凡人的人格標準是一律的。這正是“天賦人權”的宣言,人格平等的贊歌,是陽明思想中的閃光點。
“良知”作為心之本體,是光明透亮的,無知而無不知,無照而無不照,有而未嘗有,無而未嘗無。但良知由于私欲的阻礙和障蔽,使其本體未能充分發育流行,因而必須通過“致”的工夫以恢復本體良知,使其完善地發揮其知善知惡的功能,以便實實在在地做存善去惡的工夫,這就是致良知。
致良知的實踐,正是知行合一的表征。王陽明說:“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于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后之可言也。”[9]可見,“知行合一”的工夫,就是“致良知”的工夫。“知”即是“良知”,致知即致良知。“致”就是實踐、實行。“致良知”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基本功夫。
王陽明認為“致良知”包括許多具體的修養功夫。
首先要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去體驗致良知的修養歷程,不計功利,不計成敗,從而集得真義,養得正氣。集義工夫是一種道德意識的培養過程,它能培養出至正至剛的浩然之氣。修養者全身心充盈著浩然之氣,自然精神飽滿,無餒無慚,勇猛無畏,充滿活潑的朝氣。正如陽明所說:“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并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正氣。”[10]又說:“須是勇。用功也,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11]
其次是要注意省察克治,即是在無事時自我省視,將留在心中的諸多私欲惡念一一搜尋出來,加以掃除廓清,永不復發,克治惡念時,要像貓捉老鼠那樣專心致志,剛有一絲私欲萌發,就毫不留情地將之清除掉,從而達到天理純全境地,培養完善的人格。
第三,致良知要靠實際行動,不能脫離日常生活的諸多事項,要在社會生活、家庭生活、個人生活的實踐中“致良知”。因此,必須在事上加以磨煉,在社會事務中進行致良知的道德修養和道德實踐的工夫之學。社會事務是紛繁復雜的,上至人民社稷、錢谷甲兵,簿書訟獄,舉業,憂患,下至搬柴運水、坐起詠歌,都是實學的內容。人們須在此類事務中進行磨煉,致其良知,才能遇事不慌,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才能完成經世濟民的政治目標。
第四,要立志。立志是人生發展的趨向和動力。方向和目標明確,意志堅定,決心勇毅,才能激發出無盡的力量,百折不撓地邁向終極目標。古往今來的大教育家、大宗教家、大政治家,無一不強調立志。王陽明為傳播推廣其心學思想,反復向門生講述“立志”,把它作為其精神修養、道德修養,也就是塑造君子人格的基本方法。古人的“志”,指心之所之,心之所向,也就是志向,就是確定自己人生奮斗的終極目標。王陽明的立志說,表明立志必是立圣人之志,也就是以成就圣人為人生的最終目標。《教條示龍場諸生》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憩時,而百無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則圣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飄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12]由此可知,志不立則人生失去目標,任其漂蕩,無所止泊。只要志向明確,就可以成圣成賢。
古代儒家以“君子----小人”來區分人格類型。《黃帝內經》依據陰陽五行,分為金形之人、木形之人、水形之人、火形之人和土形之人五大類,進而細化為25種類型。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實際是25種人格類型,而每一類型的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都不一樣。《尚書·皋陶謨》中提出“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三國時魏人劉劭著《人物志》,受“九德”的影響,他依據人的性格、習染、才具等因素,把人格分為十二種類型。
西方心理學家對人格心理作了長期而精深的研究。瑞士偉大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榮格建立了性格類型理論;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布里格女士及其女兒伊沙貝爾·布里格·梅耶,在榮格理論的基礎上,總結出“梅耶—布里格性格分析法模型”,俗稱“16種人格”,影響頗大。中國當代心理學家裴鈺的《16型人格》一書,把布里格“16型人格”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理論與歷史人物性格特質相融通,對16型人格作了詳細闡述。
現代心理學的“人格”,是人的氣質、性格和才情的綜合表征,顯現出人物的內質美與外形美相融合的精神風采。“人格”是外來詞,本意是面具。中國古籍中沒有“人格”一詞,王陽明等的著作未直接提及“人格”,但“人品”、“品格”、“品骨”等詞的含義與“人格”相近;也有以“氣象”來描述某某人的精神風貌,也就是人格風采。有些學者標舉“境界”一詞,來表述個人精神修養和道德修養所達到的層次,近似于人格類型。
什么是境界?陳來先生作了這樣的界定:“精神境界是指一個人世界觀的整體水平和狀態。這里說的世界觀不是對外部自然物質世界的認識,而是指對整個宇宙、社會、人生及自我的意義的理解與態度。境界是標志人的精神完善性的范疇,是包含人的道德水平在內的對宇宙人生全部理解水平的范疇。”[13]陽明心學的境界論,當以“心即理”為出發點,堅持知行合一、本體工夫合一的向度來闡發。葉遠厚先生指出:“所謂境界就是修養和工夫狀態中對終極價值本體的體驗與覺解的水平,精神受用的程度。”[14]依此界說,陽明心學把境界分為學人境界、賢人境界、圣人境界和萬物一體境界。達到上述境界,都屬“君子人格”范疇。流俗之士未入境界,但具有人品,也就有人格風貌。
從工夫境界區分,圣人的工夫為生知安行,賢人為學知利行,學人的工夫是困知勉行。圣人達到盡性、知性、知天的境界;賢人則尚隔一層,只能事天、存心、養性,因其心尚有未盡,性還未保全,必須堅持修為,以防倒退。王陽明對學人境界作了這樣的論述:“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15]而學人更次一等,于天命尚未知聞,正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因此,必須堅持省察克治,時時處處做那存天理、滅人欲的工夫,竟求賢人境界。
王陽明大力標舉狂者境界,是介于學人與賢人之間的境界。他自認為自我修養只達到狂人境界,而與鄉愿對立,力欲除之。他曾說:“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16]
他自許為狂者,就是要克服鄉愿習氣。鄉愿者,是戴著“君子”人格面具的小人,具有雙重人格,表面道貌岸然,實則與小人同流合污。陽明對此深惡痛絕。他說:“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無忤于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破壞而庶可與裁。”[17]鄉愿者兩面討好,其心不善。狂狷者超拔流俗,乃堅守圣人之道的豪杰之士,振起世道衰微的頹風,寄希望于狂狷者。
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萬物一體。王陽明萬物一體的思想,是仁心推廣的極致境界,是內圣外王的合一境界,也是其終極的價值關懷。陽明重“親民”之行,陳來先生指出:“陽明萬物同體思想的重點在‘博施濟眾‘仁民愛物的親民之一面。”[18]確是一語中的。簡要論之:明明德為內圣之功,而親民則外王之業。明德以親民為事為用;親民以明明德為體為本。由此而構建九族親睦,天下協合的至善境界。
王陽明吸取孔孟以來諸儒學大師有關萬物一體思想的精華,把個體精神境界的提升與社會理想融而為一,從而成為陽明心學思想最有魅力、最有影響力,也最具前瞻性的理論卓識。
論及個人修身與國家天下的關系時,陽明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天下平。”[19]
與佛教之學比較,佛學只在個人的生死解脫、涅槃寂靜;未能關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顯出自私的特質,只是小道。陽明心學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物的共存共有關系,追求世界的和諧與穩定,達到天人合一的至善至美境界。這對我們當下處理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地球保護問題、世界和平問題,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陽明先生自我追求和達到的只是“狂狷”境界,這是他自謙之說,事實上,他的立身行事,修養與追求,堪稱“君子人格”典范。他把“君子人格”定為“內圣”,即內心的德性,認為一個人“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就是君子。如果加以擴充,施之于民和社會、自然界,就能達到“內圣外王”的圣人境界、天人合一境界。王陽明52歲自我反省,認為一個君子只信良知,辨清真是真非,不必掩藏回護,既不怕得罪他人,也不怕忤逆權貴,只要照此良知做去,便是行君子之道,可攀賢人、圣人之境,追求理想人格。
至于“小人”,一般儒者都視之為禽獸,沒有人性,只知損人利己、奸詐巧偽,難以救藥。王陽明倡導良知之學,認為人人心中具有良知本體。即使是盜賊,心中也有一絲良知未滅,有改惡從善的可能。
人性之善,也就是良知。陽明認為良知者,“心之本性”,人人具有,無間賢愚。只要堅持為善去惡的修養工夫,惡人也可轉化為善人,小人自然可變為君子。這正是“致良知”學說光耀千秋的閃光點。
王陽明畢生堅持精神修養和道德修養的實踐,立下圣人之志,從日常言行中“集義實修”、“省察克治”、“事上磨煉”,最終成就“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境界。他的人格魅力,熠熠生輝,令當世及后人景仰。其所創行的“致良知”學說,經歷時代風雨的洗濯,更加堅實豐厚,不僅影響中國,而且傳播世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說:“陽明心學追溯孟子并承接象山自得之趣,針對釋老的出世法和當時功利薰心的舉業頹風,為了突出‘吾儒家法(身心性命之學),揭櫫補偏救弊的基本工夫(‘拔本塞源),提出了‘知行合一、‘存天理,去人欲、‘致良知、‘事上磨煉等以修齊治平為終極關懷的哲學和人學,至今仍有光輝燦爛的人生價值。”[20]
可以說,“致良知”學說,為健全人格的發展和修為,指出了切實可行的明確路徑和方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廣的哲學智慧。
參考文獻:
1.杜維明,《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換的自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2.轉引自汪鳳炎、鄭紅《中國文化心理學(第3版),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P409
3.楊伯峻注:《論語譯注(第2版)》,北京:中華書局1980,P81
4.同上書,P166
5.同上書,P63,P64.
6.同上書,P9
7.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P280
8.同上書,P12
9.同上書,P49
10.同上書,P107
11.同上書,P94
12.同上書,P974
13.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P8
14.葉遠厚《身心修養之道——王陽明心學的受用與詮釋》,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P245
15.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P43-44
16.同上書,P116
17.同上書,P1287-1288
18.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P259
19.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P251
20.見《王陽明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貴州教育出版社,1997,P27
Abstract:The Confucian advocates “The gentleman's personality”, and “internal saints and external kings”is the perfect personality. “The extension of innate knowledge” can make people own ideal personality. The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People classifie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ersonality. Wang Yangming advocated the Theory of Innate Knowledge, said that everyone had a conscience ontology in his mind. Whatever social status was high or low, poor or rich, he could be a virtue of personality as long as he make efforts. That is the charm of “The extension of innate knowledge”, and also the charm of “The gentleman personality”.
Keywords:Innate knowledge;The gentleman personality;Realm of theory
責任編輯 何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