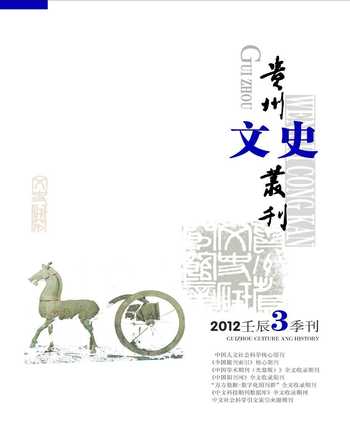1911年丁文江的貴州印象
楊建忠
內容摘要:丁文江1911年游歷貴州,在游記《我的第一次內行旅行》中記錄了他的貴州之旅。貴州獨特的氣候、地貌、交通、經濟、民族風俗給他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并影響了他以后的研究工作。他對百年之前貴州的記述和研究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關鍵詞:丁文江 貴州 旅行 印象
中圖分類號:K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2)03-120-123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蘇泰興人,出身仕紳家庭,早年負笈日本,后來在吳稚暉影響下到英國留學。歸國后歷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長、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北京大學地質調查所所長、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在他并不漫長的一生中,他主持多項地質考察和調查,其足跡遍及西南、華中和華北,特別跋山涉水多次深入川滇黔進行大規模的地質和礦產考察并開展古生物研究,是公認的中國現代地質學之父。他又是“科玄論戰”主將,否定張君勱“科學對人生哲學無所作為”的觀點,狂人傅斯年譽之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1]胡適稱他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2]。1932年,他根據自己1911年游歷云南、貴州及湖南的所見所聞所思寫成《我第一次的內地旅行》發表于《獨立評論》第5號,其中的《“地無三里平”——雍正以前的地圖、新舊驛道》、《人無三分銀——貴州人吃鹽的方法》、《貴州的土著民族》、《一千五百里的水路——從鎮遠到常德》等篇記錄了丁文江的貴州之旅,[3]為我們留下了100年之前的丁文江所見所聞的貴州。
1911年(宣統三年)5月10日,在英國留學七年后,揣著格拉斯哥大學動物學和地質學雙科學士的丁文江從歐洲歸國。他放棄常走的簡便的直達上海的海路,中途在越南的勞開下船,開始了第一次內地旅行,也是作為地質學家的丁文江進行的第一次科學考察。他乘坐剛通車的滇越鐵路列車到昆明,逗留了兩個多星期。5月29日,丁文江脫下西裝,換成長袍馬褂,戴上黑紗瓜皮帽,裝了假辮,留了小胡子,時任云南高等學堂監督葉浩吾派了兩名徒手護兵護送,雇了9個“麻鄉約信轎行”的腳伕挑了儀器書籍,浩浩蕩蕩從昆明出發。[2]經過馬龍、沾益、白水、平彝(今富源),6月初到貴州境內。
丁文江親身領教了“天無三日晴”的貴州天氣,知道此言不虛,他在貴州的一個月零七天的旅行,就下了十五天的雨,也延遲了他的行程。特別重要的是,領略了缺乏實踐精神的中國地理科學的落后和荒謬。本著科學家的研究精神和敏感,丁文江從平彝起一路“自己用指南針步測草圖,并用氣壓表測量高度”。按他手中持有武昌輿地學會1903年(光緒三十一年)出版的《中外輿地全圖》指示,從平彝到貴陽,要過亦資孔、普安、盤江、永寧、關嶺、黃果樹。不想這條黔滇驛道于雍正七年(1729年)已由云貴總督鄂爾泰奏請改建,改從劉官屯、楊松、上寨、毛口渡、郎岱、坡貢到安莊,以避開關嶺鐵索橋。他發現這條新的驛道在《中外輿地全圖》和商務印書館新出的中國地圖中都標示錯誤,起因在于這些地圖的底本居然是17世紀天主教傳教士為康熙皇帝所繪制的地圖,這些地圖不僅沒有地形標識,缺乏標注偏遠地區的地理位置,而且對黔滇驛道的改變也沒有再現。“一條貫兩省的驛道,在圖上錯誤了二百多年,沒有人發見。足見我們這二百多年地理學的退步”。這與滿清時代中國仕人士大夫們都忙于皓首窮經,在考據和辨偽中浪費時日卻不肯“出去走走”看天下變化,缺乏實證意識有關。為修正此類錯誤,提高地圖的準確性和實用性,丁文江與翁文灝、曾世英合纂的《中國分省新圖》和《中華民國新地圖》先后于1933年和1934年由上海申報館出版。《中國分省新圖》的出版具有劃時代意義,50年代建國初期的中印邊界談判,中國政府就是以此圖為在領土談判中的依據,而《中華民國新地圖》卻是以后新出的各版中國地圖的藍本。[4]
他深入了解到“地無三里平”,交通不便是貴州的常態。一路上,他堅持科學精神,滿懷著對地質和礦產的深切關注,他沿黔滇徙步旅行,穿越偏遠的深山峽谷,進行繪圖和地質考察工作,開辟學術疆域。[5]通過實測,他得出劉官屯的海拔高度是1624米,黃果樹1008米,貴陽1095米,整個貴州從西到東地勢是逐級降低的,中間有許多500米至1000米深的峽谷,處處都有丘陵起伏,地形多樣,“中國舊地圖硬要把這復雜的丘陵峽谷畫成了長蛇式的山脈,無怪它一無是處了。”從劉官屯到黃果樹,黔滇新驛道長153.2公里,與舊驛道(長118.5公里)相比,反而“遠了將近六十里路,”“新路也極其不平”,改修新道的原因是貴州西部山高谷深,陡坡絕壁,河流縱橫,交通障礙眾多。與舊驛道相比,新“驛道的路好走”,“雖然要遠到六十里,還是值得繞越;鄂爾泰把驛道改到毛口河,郎岱,還是不錯的”。云南雖是高原,便山間尚有大量的平地“壩子”。進入貴州境內,“每日所見的,不是光禿禿的石頭山,沒有水,沒有土,沒有樹,沒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峽谷,兩岸一上一下,都是幾百尺到三千尺”。平地很少,只有峽谷的支谷(如北口,炒米鋪、鐵場)或石山的落水塘(如安順、清平、黃平、施秉)才見到極少的村落,而城市往往在比較淺而寬的峽谷里(如貴陽)。因多山,峽深,“除去靠湖南邊境,有幾條河,能勉強通小民船之外,一切的的運輸不是人背,就是馬馱”,“通省沒有車輪子的影子”。
對水運交通和城鎮的考察有專業精神。6月29日,丁文江到達鎮遠,由于旅費不足,只得在鎮遠過了六天閑逛時光,等一位曾任云南普洱知府的告老回鄉的一位同鄉老進士,好搭他的包船回籍。在鎮遠,他考察了北岸的縣城和南岸的衛城,瀏覽了黔東名勝青龍洞,描繪和測量了祝圣橋,“長九十公尺,寬七公尺,高出水面十幾公尺。橋上有五個大孔,橋中間有一個十幾公尺高的寶塔,是貴州很少見的建筑。”他細察了沅江水運交通,鎮遠海拔507米,洪江180米,從鎮遠到湖南常德因落差大,流水急,恰逢當時大水一千五百里水路八天就到了,若是上水逆行,所需時間則在三倍以上,至少要走24天。
經過長年戰亂,貴州人口銳減,生產凋敝,經濟落后。據丁文江觀察,他從亦資孔到鎮遠千里貴州行經過的十二州縣中,僅有貴陽和安順人口過萬。郎岱(今六枝郎岱)、鎮寧、安平(今平壩)、清鎮、龍里、貴定、清平(今爐山)、黃平、施秉、鎮遠人口較少,其中貴州東部商業重鎮鎮遠號稱有四千戶,實際不足二千;號稱州縣的黃平、清平人口還不到一千,沿途經過的鎮市村落沒有超過一百戶的。當然,丁文江僅靠路邊走馬觀花所見下斷言說“路邊的居民一共不到十六萬人,若是除去貴陽,安順兩個大城,其余的不過四萬人”可能是錯誤的,但從中可看出晚清貴州的經濟境況。人口少,山間可墾植的田地極其有限,農業生產效率低下,人民收入微薄,省政府收入有限,“貴州全省的田賦不到一百萬兩,不過抵上江南的一個大縣”。
清末的貴州,原設屯堡的地方,由于人口比較集中,地理位置和交通比較便利,逐漸發展成了鄉村集市,并規定物品交易的固定日子(趕場日)。場名一般按十二生肖命名,如龍場、馬場、牛場、雞場、狗場、羊場、猴場等,用干支計算趕場日,形成固定場期,以免鄰近的地方沖突。丁文江到黃果樹的當天恰逢趕場,了解到一些鄉村的集市貿易規則和交易情形。人民普遍貧困,集市貿易落后,肉類只有在趕場天供應,“趕緊叫人去賣(應為買,筆者注)肉,因為不趕場子,當然不能宰豬的”。
鴉片是貴州對外貿易的主要物品。[6]19世紀末20世紀初,貴州是全國四大鴉片產區之一,尤以丁文江所過的黔西北產量最多。隨著鴉片產量激增,鴉片貿易在貴州相當繁盛,較大的城鎮都是鴉片的重要集散地,而安順則是貴州首屈一指的最繁忙的鴉片貿易市場,四川、兩湖、兩廣的鴉片商紛至沓來,規模很大。“在當日貴州生活狀況之下,除了鴉片之外,農產物已經絕對不能外運”。清末,由于政府推行禁煙制度特別嚴厲,人們賴以維持穿衣吃鹽的鴉片種植受到影響,無物交換,人民生活困苦,前來“趕場子”的少數民族群眾都是光腳或穿草鞋,“沒有鴉片出口,食鹽棉花都發生了問題。所以‘人無三分銀的話,在我第一次到貴州的時候,尤其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昂貴的食鹽給丁文江以永久不忘的印象。貴州對外貿易的大宗,是食鹽的輸入。貴州本地不產鹽,全靠川鹽、滇鹽、淮鹽、粵鹽等輸入供應。食鹽經過長途運輸及多道流通環節,價格高昂,“斗米斤鹽”使鹽成為生活奢侈品,吃鹽也成為一件奢侈的事。他在《貴州人吃鹽的方法》中說:
到了貴州境內,就只看見辣子,少看見鹽粑(四川來的成塊的鹽叫做鹽粑)。大路邊的飯鋪子,桌上陳列的是,白米飯,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里面都沒有一顆一粒的鹽屑,另外有一只碗里面放一塊很小的鹽粑,吃飯的人,吃得淡了,倒幾滴水在這碗里,然后把這幾滴鹽水倒在飯菜里,得一點咸味。我從兩頭河到楊松的時候,在半路上“打尖”。一個夫子喊道,“老板娘!拿點水來放在鹽碗里”。一個五十多歲老婦人走了出來,慢慢的說道“鹽碗里放不得水的!放了水化得太快了。你們嫌淡,拿起來放在嘴里呷呷就好了”。果然那個夫子照她的話把那塊鹽拿起來呷了一呷。不到一刻工夫,我眼看見這一塊鹽在九個夫子的口里各進出了一次!
蹇念益[7](字季常,貴州遵義人,曾留學日本,主持松坡圖書館總務,與丁同為共學社、《改造》雜志成員,是著名作家蹇先艾的叔父)也曾給丁文江講過一個貴州人的吃鹽故事:
有一家人,父子三個一桌吃飯。父親將一塊鹽高高的掛在桌子當中。對他的兩個兒子說道:“你們覺得淡的時候,吃三口飯,看一看鹽,就可以過癮了,不必吃鹽。”等了一會,他的大兒子叫道:“父親!弟弟吃一口,就看一看鹽!”“你聽他去罷。他不懂得事。等他咸死!“
在貴州,通過與姿態各異的土著民族的接觸,引起了丁文江的人類學研究興趣,他調查民族分布,區分了各土著民族的差異,進行了簡單的體質人類學測量。這為他1914年到云南蒙自、個舊、武定及四川會理研究蜀黔滇少數民族進行民族文獻資料收集、人體測量和民族調查的作了準備。1929年他第三次到貴州大定(今大方)收集到石刻漢文與倮倮文對照的《千歲衢碑記》拓本并請當地人羅文筆用三年多時間翻譯倮倮文經典《爨文叢刻》中的八篇(《獻酒經》、《解冤經》(上下)、《天路指明》、《權神經》、《夷人做道場用經》、《玄通大書》、《武定羅婺夷占吉兇書》),對了解倮倮人歷史和民俗,特別是以后凌純聲、馬學良等認定爨人(彝族)在中國邊疆民族發展史中的地位產生了重要影響。[8]
貴州境內世居少數民族十多個,各民族內部支系眾多,分布不均,文化多樣。雍正鄂爾泰治貴州,推行“改土歸流”,重點是治理少數民族地區。“剿撫苗蠻”、“打通苗疆”尤其是對黔東諸苗寨用兵擾亂了苗族的長期聚居地,大量苗民被近西遷。同時,官府對各少數民族的長期欺壓、奴役和繁重的徭役激化了民族矛盾,乾嘉年間黔東苗民包利紅銀起義、石柳鄧吳八月起義被鎮壓數萬苗民被屠殺,苗寨被焚毀,幸存的苗人只得向西尋找新的棲息地。[6]從平彝到郎岱的七天中,丁文江只看見十幾個漢族村落。一直到坡貢至黃果樹新舊驛道向會合的路上見到了大量的苗族,這些苗族就是從黔東西遷的苗民后裔。據他一路上對苗族分布的觀察,“苗家的老巢在貴州的東部和湖南的西部。從貴陽向西,雖然一直到云南的西南,四川的東南,都有苗族的蹤跡,似乎都是近代的移民”。在黃果樹,丁文江遇見了不同的苗族分支,一是穿青色長襖,著青色短裙,束青色裹腿,皮膚較黑,盤頭的青苗;另一是裝束相似但衣飾顏色為紅白二色的花苗。他在黃果樹見到的青苗與其后他在黃平等地所見的青苗是同一支系,那里的苗民都是從黃平附近西遷的。只是由于長期遷徙,西遷苗民更加窮困,“衣服都是舊的,而且很不干凈”,用棉布或粗麻制作,沒有扣子,只得用一根帶子將敞開的衣服束在腰間;“腳底下都是光腳,不穿草鞋”。而黃平等地的苗民似乎更為富足,“衣服比較的整齊,而且往往帶上許多銀的首飾:鐲子環子之外還有一種八兩到十兩的大銀圈,帶在頸項上”。在鄉場上,他還見到了穿藍底白花大袖短襖、百褶長裙,頭戴涼帽,穿草鞋的仲家子(布依族)。布依族身高1.53米左右,較苗族高,膚色長得很白,行動活潑,給丁文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各民族間存在著族群邊界或隔閡。在商品交易的鄉場,少數民族與其他民族進行物品交換時都用漢語,對民族的人則操本民族語言。各民族的地域分布有比較明顯的界線:
從昆明到貴陽的大路,又是仲家和猓猓(彝族)的分界線。大路以南是仲家的勢力——東連到廣西的獞人(壯族),西連到云南的擺夷,都是一種。大路以北是猓猓的勢力。
參考文獻:
[1]雷啟立編.丁文江印象[M].學林出版社,1997.
[2]胡適著.丁文江傳[M].東方出版社,2009.
[3]丁文江著,陳子善編訂.游記兩種[M].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文中引文未標注部分均出自本書
[4][美]費俠莉著,丁子霖等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M].新星出版社,2006.
[5][美]郭穎頤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6]貴州通史編委會編.貴州通史簡編[M].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
[7]許紀霖等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歐陽哲生編.丁文江先生學行錄[M].中華書局,2008.
The Impression of Ding Wen-jiangs about Guizhou in 1911
Yang Jian-zhong
(Kaili University, KaiLi 556011; School of Education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Ding Wen-jiang traveled Guizhou in 1911. In his travel note "my first trip in the hinterland" records of his trip in Guizhou. The unique climate, topography, transportation, economic, ethnic customs of Guizhou's left him a very deep impression. The impression affected his later work. His account and research on Guizhou before the centuries give us a valuable asset.
Keywords:Ding Wen-jiang;Guizhou;Trip;Impression
責任編輯 何 萍